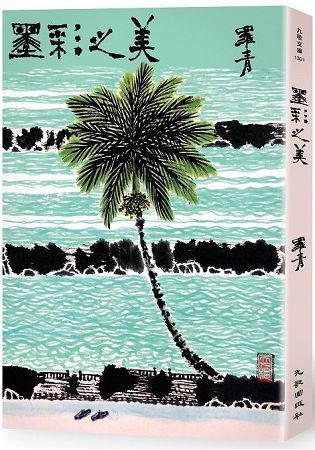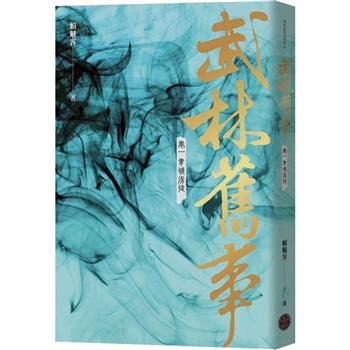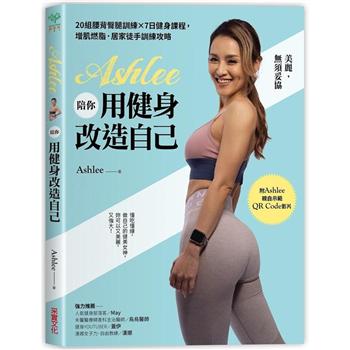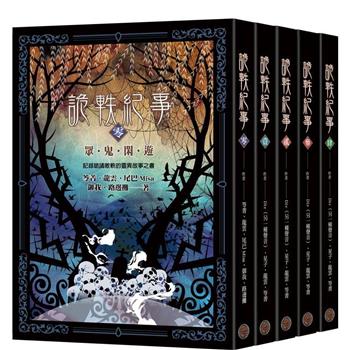以〈吃西瓜的六種方法〉聞名的詩人羅青,不只寫詩也畫畫,從小在墨彩名家溥心畲、任博悟習門下習畫,四處看畫展,他以詩人的靈魂、文人的筆墨,建構出他個人獨特的水墨畫,因此獲獎無數,被楚戈先生贊為「新文人畫的起點」。
在《墨彩之美》他以自身對墨彩畫的研究與創作經驗,為「墨彩畫」正名,從三大方面:繪畫美學、古典傳統畫流變、近代繪畫的傳承與發揚,切入墨彩畫的發展歷史、繪畫內涵與特質。從「彩墨畫」到王維提倡「水墨畫」,無須彩色,運用不同墨法呈現「濃、淡、乾、濕、燥」五色,形成文人畫的傳統,搭配賞析〈女史箴圖卷〉、〈雪中芭蕉〉、〈清明上河圖卷〉等畫作。旁及唐、宋、元、明、清及民國以來的重要畫家,王維、徐兢、石濤、王原祈、齊白石等,綜論、賞析、重估,不只提供繪畫相關知識,瞭解墨彩的歷史淵源,還有中國獨特的扇面繪畫藝術和歷史。篇篇新詮古典繪畫美學,連接當代社會,配合獨創的美學原則,具體而微的說明「墨彩畫」的最新發展,並討論二十世中國藝術史的編寫之道,改寫千年來的墨彩畫史及美學史,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墨彩之美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80 |
繪畫欣賞 |
$ 316 |
藝術設計 |
$ 316 |
美術 |
$ 316 |
國畫欣賞 |
$ 316 |
Arts & Photography |
$ 352 |
中文書 |
$ 352 |
繪畫 |
$ 360 |
國畫欣賞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墨彩之美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羅青
本名羅青哲,湖南省湘潭縣人,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生於青島。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曾任輔仁大學、政治大學英語系副教授,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所、翻研所、美術系所教授,中國語言文化中心主任。明道大學藝術中心主任、英語系主任。一九九三年獲傅爾布萊德國際交換教授獎。
一九七四年獲頒第一屆中國現代詩獎,國內外獲獎無數,被翻譯成英、法、德、義、瑞典等十三種語言。畫作亦獲獎多次,並獲大英博物館、德國柏林東方美術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美術館、美國聖路易美術館、中國美術館、遼寧省美術館、深圳畫院美術館、臺灣美術館等國內外公私立美術館收藏。曾出版詩集、詩畫集、畫集、論文集、畫論集五十餘種。
羅青
本名羅青哲,湖南省湘潭縣人,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生於青島。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曾任輔仁大學、政治大學英語系副教授,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所、翻研所、美術系所教授,中國語言文化中心主任。明道大學藝術中心主任、英語系主任。一九九三年獲傅爾布萊德國際交換教授獎。
一九七四年獲頒第一屆中國現代詩獎,國內外獲獎無數,被翻譯成英、法、德、義、瑞典等十三種語言。畫作亦獲獎多次,並獲大英博物館、德國柏林東方美術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美術館、美國聖路易美術館、中國美術館、遼寧省美術館、深圳畫院美術館、臺灣美術館等國內外公私立美術館收藏。曾出版詩集、詩畫集、畫集、論文集、畫論集五十餘種。
目錄
〔自序〕
「墨彩畫」的再生
上卷 概論篇
中國墨彩美學初探
漫談中國藝術的特色
論文人水墨畫
扇搖風生詩畫香---扇畫簡史
中卷 古典篇
雪中芭蕉寓意多──論王維的畫藝
被藝術史遺忘的繪畫大師──北宋詩書畫三絕的徐兢
清明上河圖新解
詩中有畫畫中詩──論玉澗的《山市晴巒圖》
清奇古怪通鬼神──論陳洪綬的畫
一呼前後九百年──談石濤的一開冊頁
扇搖風生詩畫香──扇畫簡史
下卷近代篇
漫談民國「三石」的書畫藝術
第一位名揚世界的中國墨彩畫家
雕刻中的石像──蘇立文《二十世紀中國藝術》讀後〉
「墨彩畫」的再生
上卷 概論篇
中國墨彩美學初探
漫談中國藝術的特色
論文人水墨畫
扇搖風生詩畫香---扇畫簡史
中卷 古典篇
雪中芭蕉寓意多──論王維的畫藝
被藝術史遺忘的繪畫大師──北宋詩書畫三絕的徐兢
清明上河圖新解
詩中有畫畫中詩──論玉澗的《山市晴巒圖》
清奇古怪通鬼神──論陳洪綬的畫
一呼前後九百年──談石濤的一開冊頁
扇搖風生詩畫香──扇畫簡史
下卷近代篇
漫談民國「三石」的書畫藝術
第一位名揚世界的中國墨彩畫家
雕刻中的石像──蘇立文《二十世紀中國藝術》讀後〉
序
序
「墨彩畫」的再生
要想與西方藝術市場抗衡對話的第一步,便是對自己民族的美術遺產做精深的研究及發揚;把過去的藝術成就與二十一世紀的生活及思想聯繫起來,這樣方能吸引別人來觀摩學習。中國藝術的特色之一,便是墨彩繪畫,成就輝煌,足以傲視世界,領袖羣倫。因此對墨彩藝術及美學的深入研究,便成了藝術工作者應該努力的重點之一。
中國繪畫從彩陶開始,一直是彩墨並行,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壁畫及帛畫盛行,遂有「繪事後素」的美學典範出現,強調繪者在施以彩、墨繪畫之前,必須將牆壁粉刷平整成為「素壁」,帛布整治妥當成為「素帛」。這也就是說,必先把準備在其上繪畫的各種不同材料,清理素淨,才能在其上勾勒草稿,然後施以墨色及彩色。這種最後以施用彩色來完成作品的藝術,可稱之為「彩墨畫」,從戰國到盛唐,獨霸藝壇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到了公元八世紀,詩畫家王維(699-759)出現,著意於畫筆下,追求佛家簡淨空寂之美,於是在〈山水訣〉一文中大膽提出:
夫畫道之中,水墨為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工,或咫尺
之圖,寫百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底。
認為依靠單色「水墨」的豐富層次變化及靈動的筆法技巧,無須彩色,便可在一張小畫裡,以近乎「造化」的功夫,表達四季之不同,開啟了「水墨美學」的新典範。此一「水墨」風氣,發展了近三百年,在北宋初期,到達了頂峰,當時的繪畫名家如荊浩、關仝、李成、范寬、董源、巨然、郭熙、許道寧、燕文貴…等,無一不是以水墨畫為主,成就其藝術的獨特面貌。
而這段期間,墨條與配合發墨的紙張,經過不斷的研發,有了很大的改進。如南唐李廷珪的松煙墨,精良無比,就是一例;而南唐歙縣的「澄心堂紙」,製造尤佳,最為名家愛用,與廷珪墨、龍尾硯、諸葛筆並稱四寶。此外,蘇州的「金栗山藏經紙」,湖北的「鄂州蒲圻紙」…等,亦名氣響亮。名墨配上佳紙,把水墨的特色發揮到了極致,樹立了新的美學品味與典範。
到了宋徽宗(1082-1135)即位,在翰林院中創立「畫學」(1104),吸收了水墨畫所發展出來的精華,以墨色的運用為主,重新讓彩色回到繪畫之中,變「彩墨」、「水墨」的傳統為「墨彩」新猷,開創了影響廣大的「墨彩畫」時代,傳承變化發揚至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成為農業時代美學與品味的代表,並繼續向工業社會及後工業社會挺進。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迄至一九七〇年代,一百三十年間,傳統農業社會遭到西方工業社會的巨大挑戰,帶來了深遠的美術變革,「現代主義」(Modernism)風潮,隨工業社會而起,所向披靡。許多現代主義畫家,因為美學理論的不足與匱乏,倉促重新啟用「水墨畫」一詞,藉以代表東方精神,期望從「形式技巧」上與油彩畫所代表的現代主義理論接軌,完全忽略了「墨彩畫」基本美學的重新詮釋、再開發與創造,喪失了自家藝術的立足點,成了西方現代主義的附庸與註解。等而下之者的作品,則成了機械形式與新奇技巧的大量複製,淪為可以批發代工的工藝美術品。
從一九八〇年代至今,近四十年間,因個人電腦及手機在海峽兩岸的大量出現,有關後工業社會與「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的思想,勃然而興,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去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與多元化(Pluralism)的風潮,刺激了藝術家對「墨彩畫」根源的反省,大家開始分頭在美學上探討「墨彩畫」的過去、現在與可預見的未來。
本書的上卷「概論篇」,就是在這個前提下寫成的。其中〈中國墨彩美學初探〉、〈漫談中國藝術的特色〉、〈論文人水墨畫〉三篇通論文章,重新回顧了「墨彩畫」的內涵與形式特質,希望找到其與當代社會的連接點。
接下來中卷「古典篇」,以〈雪中芭蕉寓意多──說王維的畫藝〉、〈被藝術史遺忘的繪畫大師──徐兢〉、〈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新解〉、〈詩中有畫畫中詩¬──論玉澗的畫〉、〈清奇古怪通鬼神──論陳洪綬〉、〈一呼前後九百年──說石濤畫〉、〈墨中有色熟後生──論王原祈〉、〈扇搖風生詩畫香──扇畫簡史〉八篇文章,分別選擇唐、宋、元、明、清的重要畫家,深入賞析,做為了解古典繪畫史的鑰匙。
下卷「近代篇」,以〈漫談民國「三石」的書畫藝術〉、〈第一位名揚世界的中國墨彩畫家---齊白石〉、〈雕刻中的石像---蘇立文《二十世紀中國藝術》讀後〉三篇文章,討論民國以來的重要畫家,配合上述通論所揭櫫的美學原則,具體而微的說明「墨彩畫」的最新發展,並討論二十世,中國藝術史的編寫之道,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墨彩畫」的再生
要想與西方藝術市場抗衡對話的第一步,便是對自己民族的美術遺產做精深的研究及發揚;把過去的藝術成就與二十一世紀的生活及思想聯繫起來,這樣方能吸引別人來觀摩學習。中國藝術的特色之一,便是墨彩繪畫,成就輝煌,足以傲視世界,領袖羣倫。因此對墨彩藝術及美學的深入研究,便成了藝術工作者應該努力的重點之一。
中國繪畫從彩陶開始,一直是彩墨並行,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壁畫及帛畫盛行,遂有「繪事後素」的美學典範出現,強調繪者在施以彩、墨繪畫之前,必須將牆壁粉刷平整成為「素壁」,帛布整治妥當成為「素帛」。這也就是說,必先把準備在其上繪畫的各種不同材料,清理素淨,才能在其上勾勒草稿,然後施以墨色及彩色。這種最後以施用彩色來完成作品的藝術,可稱之為「彩墨畫」,從戰國到盛唐,獨霸藝壇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到了公元八世紀,詩畫家王維(699-759)出現,著意於畫筆下,追求佛家簡淨空寂之美,於是在〈山水訣〉一文中大膽提出:
夫畫道之中,水墨為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工,或咫尺
之圖,寫百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底。
認為依靠單色「水墨」的豐富層次變化及靈動的筆法技巧,無須彩色,便可在一張小畫裡,以近乎「造化」的功夫,表達四季之不同,開啟了「水墨美學」的新典範。此一「水墨」風氣,發展了近三百年,在北宋初期,到達了頂峰,當時的繪畫名家如荊浩、關仝、李成、范寬、董源、巨然、郭熙、許道寧、燕文貴…等,無一不是以水墨畫為主,成就其藝術的獨特面貌。
而這段期間,墨條與配合發墨的紙張,經過不斷的研發,有了很大的改進。如南唐李廷珪的松煙墨,精良無比,就是一例;而南唐歙縣的「澄心堂紙」,製造尤佳,最為名家愛用,與廷珪墨、龍尾硯、諸葛筆並稱四寶。此外,蘇州的「金栗山藏經紙」,湖北的「鄂州蒲圻紙」…等,亦名氣響亮。名墨配上佳紙,把水墨的特色發揮到了極致,樹立了新的美學品味與典範。
到了宋徽宗(1082-1135)即位,在翰林院中創立「畫學」(1104),吸收了水墨畫所發展出來的精華,以墨色的運用為主,重新讓彩色回到繪畫之中,變「彩墨」、「水墨」的傳統為「墨彩」新猷,開創了影響廣大的「墨彩畫」時代,傳承變化發揚至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成為農業時代美學與品味的代表,並繼續向工業社會及後工業社會挺進。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迄至一九七〇年代,一百三十年間,傳統農業社會遭到西方工業社會的巨大挑戰,帶來了深遠的美術變革,「現代主義」(Modernism)風潮,隨工業社會而起,所向披靡。許多現代主義畫家,因為美學理論的不足與匱乏,倉促重新啟用「水墨畫」一詞,藉以代表東方精神,期望從「形式技巧」上與油彩畫所代表的現代主義理論接軌,完全忽略了「墨彩畫」基本美學的重新詮釋、再開發與創造,喪失了自家藝術的立足點,成了西方現代主義的附庸與註解。等而下之者的作品,則成了機械形式與新奇技巧的大量複製,淪為可以批發代工的工藝美術品。
從一九八〇年代至今,近四十年間,因個人電腦及手機在海峽兩岸的大量出現,有關後工業社會與「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的思想,勃然而興,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去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與多元化(Pluralism)的風潮,刺激了藝術家對「墨彩畫」根源的反省,大家開始分頭在美學上探討「墨彩畫」的過去、現在與可預見的未來。
本書的上卷「概論篇」,就是在這個前提下寫成的。其中〈中國墨彩美學初探〉、〈漫談中國藝術的特色〉、〈論文人水墨畫〉三篇通論文章,重新回顧了「墨彩畫」的內涵與形式特質,希望找到其與當代社會的連接點。
接下來中卷「古典篇」,以〈雪中芭蕉寓意多──說王維的畫藝〉、〈被藝術史遺忘的繪畫大師──徐兢〉、〈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新解〉、〈詩中有畫畫中詩¬──論玉澗的畫〉、〈清奇古怪通鬼神──論陳洪綬〉、〈一呼前後九百年──說石濤畫〉、〈墨中有色熟後生──論王原祈〉、〈扇搖風生詩畫香──扇畫簡史〉八篇文章,分別選擇唐、宋、元、明、清的重要畫家,深入賞析,做為了解古典繪畫史的鑰匙。
下卷「近代篇」,以〈漫談民國「三石」的書畫藝術〉、〈第一位名揚世界的中國墨彩畫家---齊白石〉、〈雕刻中的石像---蘇立文《二十世紀中國藝術》讀後〉三篇文章,討論民國以來的重要畫家,配合上述通論所揭櫫的美學原則,具體而微的說明「墨彩畫」的最新發展,並討論二十世,中國藝術史的編寫之道,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