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名稱:狀元地
近代綠島的話語權,一直由外人所構建──「監獄」、「白色恐怖」、「觀光勝地」、「海底溫泉」,不是刻板的政治意向,就是浪漫多情的島國遐想。綠島真實的歷史、常民生活都被遮蔽在那些強烈而清晰的外來符號之下,無人來為之詮釋。
綠島不只是昔日白色恐怖記憶所在、今日的觀光勝地。誰能想像這個貧瘠的火成岩島嶼,淡水稀缺,歷史中竟曾有稻米種植,就種在名為「狀元地」的兩塊梯田。梯田的命名,飽含了過往幾代人胼手胝足下,樸素的期望。本書以《狀元地》命名,由綠島人作家李基興與兒子李家棟合著,榮獲國藝會出版補助。循著父親李基興的童年足跡,還原那個還有蓊鬱熱帶雨林的阿眉山,迷信、神靈與洪荒並行的墾殖歷史。綠島人的四季生活、飛魚季、釣煙仔、牽馬鰮、蓋鹿寮、鑿古井等,在詩意的筆下,拼貼出一幅幅早年風情畫,替那個已快被所有人遺忘的民國五〇年代綠島斷代,填補台灣地方文學中,關於綠島的空白拼圖。
本書特色
★填補台灣地方文學中缺漏的綠島的拼圖。
★精采的文字搭配珍貴的綠島照片和古地圖,讓人更加了解綠島這片土地。
王萬象、馬翊航 專文導讀
夏曼•藍波安、廖鴻基 接地氣推薦
作者簡介|
李家棟
李家棟,一九八四年生,畢業於台東大學台語教師所,現任教於寶桑國中。寫散文也寫詩,半個綠島人,但不愛吃魚。曾獲後山文學獎、台中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相信自己的出生,對綠島而言確然是有意義的。
李基興
綠島大湖(現朝日溫泉一帶)人,國小退休校長。退休後開始藉寫作,挖掘自己童年的回憶及往事,想用文字記錄民國五十年代,那個已經湮沒在時間及白色恐怖之後,不為人知的綠島風貌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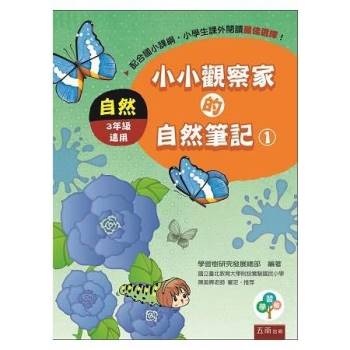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