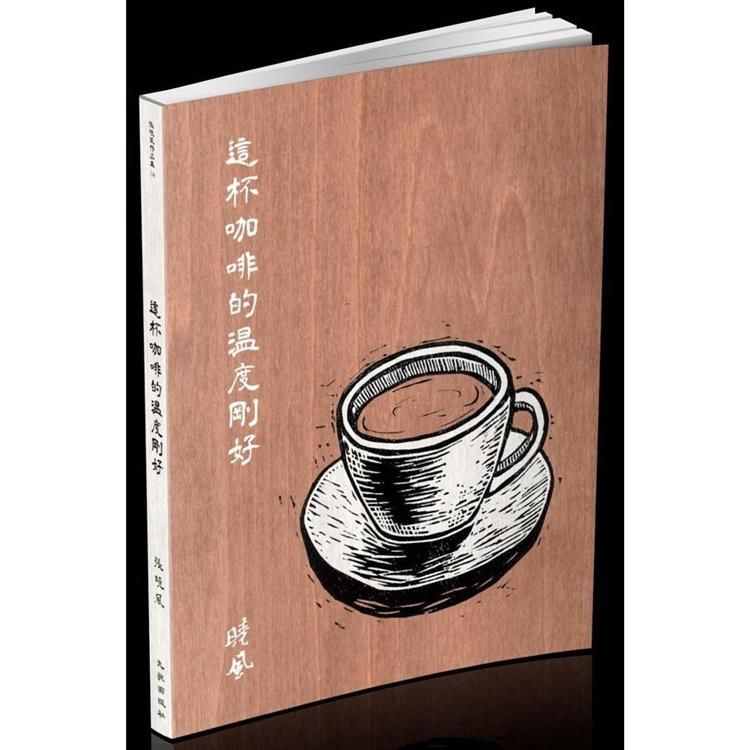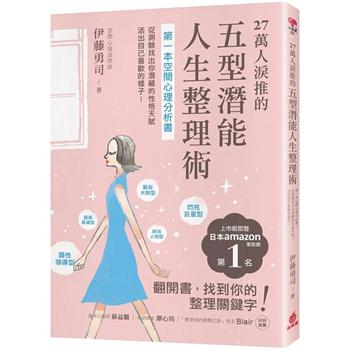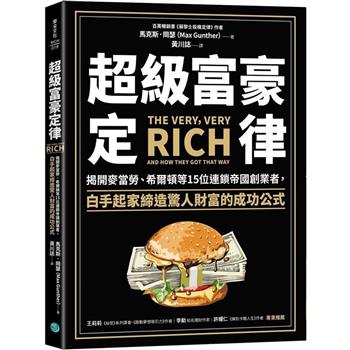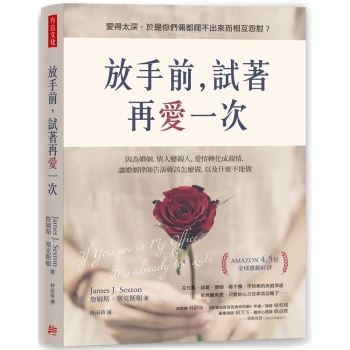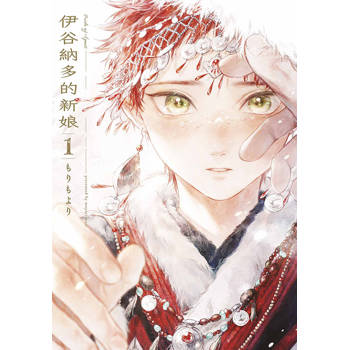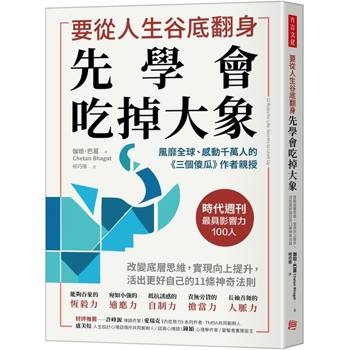圖書名稱: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
在生命的本體之前,「文學」能說的話無非也像童言,像夢話,破碎而不週全。但那半句童言細聽之下或者也隱藏幾許玄機吧? 文學,仍是可加期待的。一本書,仍有它出航的必要。
──張曉風
張曉風以情入理,在有限的字數裡,出入古今,仰視宇宙之大;從泛政治、眾聲喧嘩的都會中尋找悠閒生活之美。文字洗鍊,內容深刻精博,突破窠臼,值得細品珍藏。
在她筆下一位落榜的考生張繼,在離開京城的夜晚,寫下傳頌千年的〈楓橋夜泊〉,成就了〈不朽的失眠〉;寫父親的勤儉愛物,用鋁壺盛水曬太陽成為〈我家獨製的太陽水〉來洗澡;她也妙寫想要〈成聖的女子〉不需要成為修女,只要走入婚姻就能成為聖人。
不論是惱人的塞車、鄰居廚房肉焦事件,或是耳熟的歌曲、一杯溫度剛好的咖啡,這些我們常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日常,透過張曉風的筆,重新感受生活,品嘗出另外一番風味來,重新體會生命的點滴。
所以詩人瘂弦說:「讀張曉風不但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隨她穿過古中國文學的宗廟殿堂,更會發現宮中有宮,室內有室,千門萬戶,雍雍穆穆,而原型在焉。」
作者簡介|
張曉風
原籍江蘇省銅山縣(徐州),筆名曉風、桑科、可叵,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教東吳大學、香港浸會學院、陽明大學。曾獲中山文藝散文獎、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學獎等,並於一九七六年獲選十大傑出女青年。著有《地毯的那一端》、《步下紅毯之後》、《從你美麗的流域》、《玉想》、《送你一個字》、《花樹下,我還可以再站一會兒》,另有童書《祖母的寶盒》、《看戲》,評述和小說、詩作等。三度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及《問題小說》、《小說教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