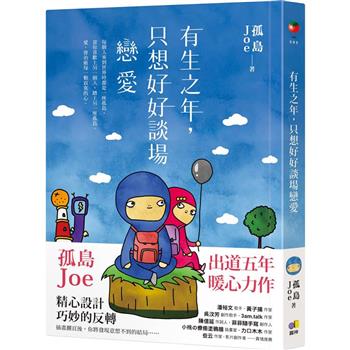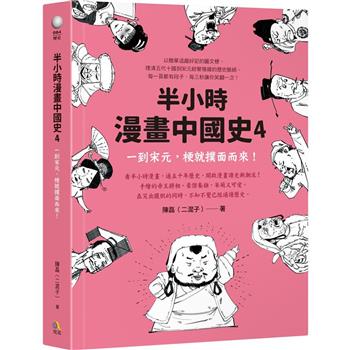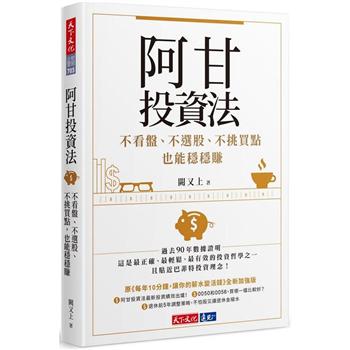圖書名稱:逆:叛之三部曲二部曲
林剪雲「叛之三部曲」首部曲《忤》從唐山過台灣到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屏東萬丹富商家族興衰為背景。二部曲《逆》則接續二二八事件後,移民再次大量湧入台灣。描繪社會底層人民面臨生存的難題,從自我認同的省籍問題,到壓抑自由思想的白色恐怖,內心的不滿、不安,像火種逐漸燃起違逆的風潮,進而引爆美麗島事件。
一九八九年莎拉颱風襲台前夕,林素淨搭車南下屏東,尋找當年從她生命中突然消失的B。穿插回憶,在現實與過去之間來回,如同南下列車窗外一幕幕快速後退的風景:慘澹的童年生活、青澀早夭的戀情、黨外活動的震撼、自我認同定位的游移……。
父親林柏仲自福建移民來台,落腳屏東萬丹,林素淨是家中最小的女兒,備受父親疼愛,卻也被生母凌虐。她常被一些街坊鄰居大人小孩嘲笑是「外省豬仔」「阿山仔查某囝」,但外省同學卻說,從福建來的怎麼是外省人呢?而努力向上的林素淨發現周遭不斷有人主動「不見了」,如後來的鋼琴家李沐心、國中導師周雅仙、李慶瑜老師的先生……被動「不見了」更多,如酒家哥哥敏郎、國中公民老師、憲兵隊劉國忠、書攤老闆胡江圖……半主動半被動「不見了」的邱生存……。
作者以小說手法描繪一九五七─一九八九年三十年間,死亡與失蹤如影隨形的台灣社會,面對自然災害的無情、政權的高壓管理,底層人民噤聲壓抑,仍舊勇敢扎根,展現草根的韌性。全書台語和華語交錯,對白生動,真實呈現語言的混雜與變遷,人物栩栩如生,藉由主角的成長故事,訴說台灣人共同的悲歡離合。
本書特色
★小說家吳錦發、高師大國文系副教授唐毓麗、成大台灣文學系副教授廖淑芳、詩人、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李敏勇、活水來冊房主人黃震南、小說家宋澤萊聯合推薦
★以二二八事件後到美麗島事件之間三十年台灣社會氛圍,透過主角林素淨的經歷,呈現心路歷程的變化,社會變遷,以小說真實呈現大時代的悲歡離合。
作者簡介|
林剪雲
過往:以人身肉體碰撞愛恨悲喜,累累傷痕堆砌為現在的我
現況:企圖以大河小說形式建構當代人書寫當代史
嗜好:玩文字、賞電影
專長:小說、戲劇
最愛的詩句: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
代表作品:《暗夜裡的女人》、《恆春女兒紅》、大河小說叛之三部曲首部曲《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