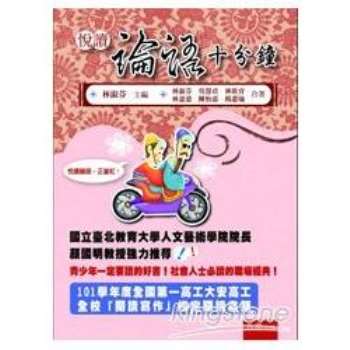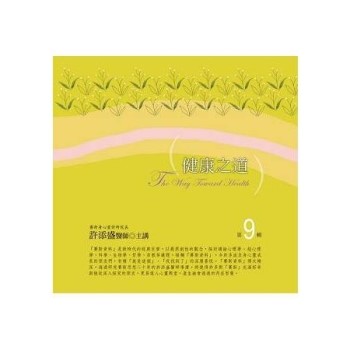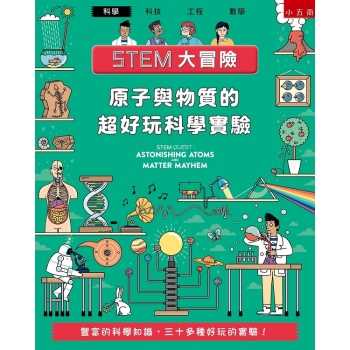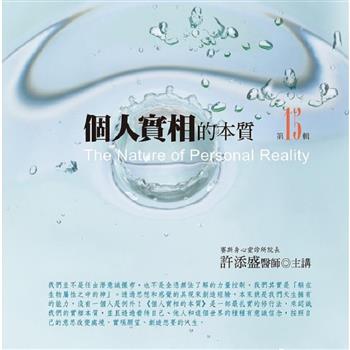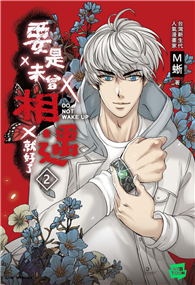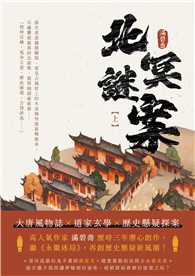自序
小眾運輸,大城紀事
公車是城市交代細節的工具。
學生時,有次從亞庇飛往山打根。飛機降落山打根後,我問工作人員何處等公車,他說沒有。這和我從網路聽來的消息是違背的。我苦找站牌卻徒勞,眼看私用車、飯店小巴陸續接走乘客,人群漸少,問了幾位華人,他們沒搭過。後來問了一位馬來人,他說必須走出機場,右手邊有間學校,對面就有公車到市區。
循著指示前去,確實有間學校,對面有座疑似候車站的建物,但沒人候車。趨近,亦無任何號碼、路線等公車牌示,就是一個簡單的遮篷。我心想:真的有公車會經過嗎?多久會來?
愈想心愈慌。然後,竟下起雨來。正當撐傘想著攔計程車時,一台銀色van開來對我按喇叭。
緊接著車停,門開,司機說了一段我聽不懂的馬來話。
這是公車嗎?我感到困惑。
「To Sandakan?」我問。司機點頭。我趕緊跳上車,此時是私用車、計程車、公車都不重要了,能到市區就好。
上車後,我問司機費用,他說二令吉。Bingo,我知道,這是公車,只有公車才是這個價。
看一下車內,無華人面孔,應多為馬來人。車子駛過一段路後,轉進某條上坡徑,繞入一個社區,只要候車亭有人,即使無招手攔車,司機也靠近鳴喇叭,開門,說了一段馬來話,然後關門離去。荒疏的黃土邊、避雨的大樹下,沒有站牌,卻有人上車。有人像是司機的親朋,坐上車就聊起來;有人從車外遞來瓜果給乘客,順便交代一些事;甚至,車在某個工廠外突然停了下來,接著對街來了三位乘客,衣髮濕透而上車。
似乎有原則,又似乎無原則。消失的站牌,可妥協的路線,既公且私。車子在社區晃了一會,接著又回到主幹道上。
仔細觀察,這是一台改裝成公車的van。共三排座位,加上副駕駛座,約可坐十位乘客。車門被改裝,可自行開關;而下車鈴就在天花板上。車錢,下車給。
大約四十分鐘後,車抵山打根總站。乘客隨即四散,我立在車站,感到恍如一場夢,搭公車成了旅行中的實驗。
但事後當我離開山打根,記憶裡最濃烈的是這段四十分鐘的車程,勝於西必洛雨林的人猿或市區骨董般的魏亞貴大酒店。
謎樣的站牌、漂浮的時刻表、陌生的文法,搭公車成了一種解碼。
何時投幣、何時按鈴、單邊設站、延駛班次……,太多太多的潛規則在每一條路線噤聲。公車似有一種秩序,是乘客默許的,他們知道車會停在哪、幾點來,即使沒有站牌、動態APP仍未發明。
小城如此,大城亦是。日後當我旅行曼谷、馬尼拉或仰光,陷在車煙瘴氣中,苦尋不著站牌,看著當地人嫻熟地等公車、攔公車、上公車,彷彿有套內建的公車系統,家務事般的,是不向觀光客表露的。
在馬尼拉,公車除了大巴,就是吉普尼(jeepney)。這是由二戰時美軍留下的吉普車改裝來的。車輛繁多,捷運站外鳴聲擾嚷,攬客聲嘶力竭。吉普尼車身裝飾豔麗,乘客屈膝蹲低登車,擠坐兩條長凳上。沒有明確站牌,車陣中就能上車。藉乘客遞錢給司機,若找錢,再遞回。但車資我總搞不懂,坐過八‧五披索,也坐過11披索。敲敲天花板,車子就為你停下。在那個時空裡,司機與乘客帶著微笑給我指引,揭露了法則,我認識了一座不是傳言裡,那勒贖、槍響與搶劫的馬尼拉。
旅行時,我大概會把一些時間留給公車,雖知耗時卻有其樂趣。有時就是單純坐車,人進人出,讓公車交代這地的日常──一城的漆色、衣裝、食肆、小販、廣告、綠化。車內車外,公車載著無飾的風景,東西南北,內環外環,大巴小巴,走過邊邊角角,撿拾旁枝末葉,還原土地形廓。
有次我從印尼泗水搭車往Probolinggo。中途休息時,前門一連上來七、八位小販,揹腰包,有人徒手抓了好幾瓶飲料,有人手掛零食串,彼此商品同質性極高。一眨眼,他們又從後門下車了。不久車啟動,上來一位婦人,她從提袋中掏出喇叭與麥克風,調一下音量,接著開始唱歌,嗓音略粗帶點砂礫感。唱畢,端出打賞箱,一步晃一步,逐排向乘客躬身微笑。半小時後,我突然想到:人呢?往車後看,婦人已不見,司機已無聲地讓她在公路邊下車,車流中繼續她的人生。
旅行在東亞,常覺得城市的性情會感染公車。
搭上九龍彌敦道上的雙層巴士,車與車,甚至與行人、店家擦身來去,貼得緊密。巴士往直的發展,招牌往橫的發展,那是世界上稠密的極致。香港絕對不會有山打根的性情,車開車關車走,沒有囉嗦,都是俐落,都是效率。
從渋谷搭往池袋的公車,會發現東京不擅於公車路網。班距稍長,路線稍少。或許厭惡停頓,沉迷於快特、特急、急行等速率追求,這城更多的細節在地鐵裡。但我對東京公車最深的印象,是過於禮貌的西裝司機。上車一聲請與謝謝,下車也是,從外在到內裡,這城都講究。
相對於東京,首爾的公車顯得綿密也廉價。一張T-money卡,公車轉公車,半小時內免費。這城的公車醒得特早,狂歡一晚,凌晨四點多,迷濛坐上跨越漢江的頭班公車,車內已有信徒,前往汝矣島上的教會晨禱。
公車路線或許多從城市主幹開始,映證一條條群眾的移動軌跡、生活共徑,那是上班、求學、買菜、就醫、信仰的故事。
有時在高雄搭公車,全車連司機共三人,我會想:這「小眾」運輸,也能交代一座城的日常嗎?
但無妨,至少它能負載。載過我的求學日常,帶我領略高雄。用十二元來載。
第一次遇見十二元是小五那年。那還是一個冷氣公車剛萌芽的年代,有次我攔到一輛冷氣公車,二十八路,上車投了半票六元,司機說:「你長這麼大,要投十二元。」
那時,公車票價只論身高,不論年齡(現改為十二歲以下享半票)。所以在十一歲那年,我就得開始買全票。身長似乎在某些時候,也會帶來一些劣勢。
到楠梓、到左營、到小港、到鳳山,那時全市公車一律一段票,上車投幣──普通車十元,冷氣車十二元。穿遊城市毋須有分段點、緩衝區、段號證的概念。只是十元公車日漸凋零,高一時搭過幾班,之後就在城裡消失了。
高中是我搭公車的尖峰。那是個紙卡月票的年代,我辦過幾次。貼張大頭照,學生票三百元一張,共六十格,普通車剪一格,冷氣車剪兩格。在悠遊卡與一卡通嗶嗶來去的今日,紙卡顯得原始,卻有一種溫度。
大學時開始騎車,但因兼了小港、前鎮的家教,路程稍遠,於是在火車站轉搭12路、69路、機場幹線等公車,生活版圖也延伸至所謂的「南高雄」。
畢業後一年,二○○八年,高雄進入捷運時代。那年十月,我離開高雄至外地工作,一晃就是十二年。十二年,縣市合併了,輕軌出現了,港區建物一座比一座前衛;再一段時間,那些鐵道之上的陸橋、之下的地下道都消失了,火車潛入地底;有些百貨商場熄燈了,有些新降臨;那年幼整街牛排館的夜市、同學追星的商圈,舊愛之地已鬆動,還留存幾分呢?生活在這城,新的來得太快,念舊似乎不宜太多,那會悲傷,得學著放手。
如今雖不像學生時頻密搭公車,但每當回高雄,出站總會轉一班公車,感應票卡,扣下熟悉的十二元,彷如一種通關密碼。而公車路線變得更多更長更遠,兩段、三段票公車也出現了。後來取消分段,改里程制,超過八公里算第二段,並推出「一日兩段吃到飽」等方案。無論優惠多繽紛,基礎起始單位仍是十二元。
或許因為我搭的這條線乘客不多,我常觀察到,不少人即使從後門下車,也會回頭向司機道聲謝謝。上車一次,下車一次,我知道,這是高雄。公車其實也交代了這城的細節──不涼薄,可能又多那麼一點溫厚與感激。
《十二元的高雄》發想於公車,實則寫母城:高雄。是的,高雄是名副其實的母城,母系親族生於此,長於此,也老於此。這本書構想早,但正式提案是二○一二年,全書收錄二○○六至二○二○年間作品。期間常常事忙就擱著,慢吞吞的寫作進度,一度一年僅寫一篇。有時不免這麼想:會不會成書時,公車票價就不再十二元了?
謝謝九歌出版社的陳姐、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的美秀姐,願意等待,願意寬容;這本書有多篇文章曾在副刊發表,謝謝這些默默第一手閱讀也予回饋的編輯;謝謝寫作路上,一直支持與陪伴的好友妮民;更謝謝高雄這塊土地與其上的人們,是這些流轉的故事,厚實了這本書。
二○二○年歲末,成書之際,高雄持續脫胎,許多文中地景與敘述又得更新調整。但也唯有這樣的時間跨度,才知道城市的速度,才知道十二元的不易,縱使日後調漲,十二元已成一種指認,一種連結,對應生命中曾經的交通往復,我城的微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