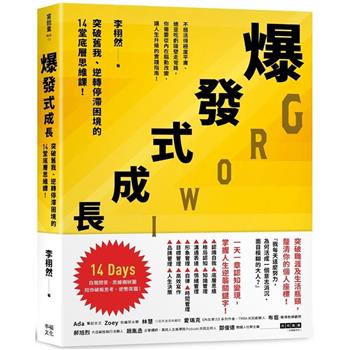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你是盛放煙火,而我是星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10 |
散文 |
$ 237 |
現代散文 |
$ 237 |
文學作品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時時生滅的微物隱喻,每一次與所愛的生發與相遇,都扣擊靈魂深處,成為顫動的回聲。
繼《借你看看我的貓》後,張馨潔再度以纖柔善感的文字,輕輕撥動自身與萬物相繫的細弦。透過珍重而誠摯的敘說,還原由她眼目所見,心靈與萬物共振的世界。
全書分為二輯:「你在,煙火盛放」寫交會與愛情,錯雜著執迷與失落的探尋,時空流轉下難以追企及繪測的事物。當關係的結局已然明瞭,每次的相遇是否皆為流逝,以不可見的速度凋亡?回視相愛的日子,企圖以語言描繪定義〈不曾發生卻確實存在的一天〉,卻發現觀測的對象早已在光陰中跨步向前,每個落空的指涉都是追趕不及的殘影。也曾窮盡〈最遠的路徑〉,在探索幽暗地宮的傷與被傷中,識得己身真名;或與〈坐在遊覽車最後一排的人〉,在方醒的清晨相視而笑。模糊的記憶與各異的詮釋不構成述說的困擾,因往事無可核鑑,存疑或深信亦無法更動分毫;所有故事在發生的當下,我們已永遠的失去了它。
「我在,星空如常」則寫自我與生活中隨起的雜想,透過作者眼光看待日常器物,探究各種關於身體的、情緒的、閱讀的心念,今昔串聯並且彼此暗示。〈持存〉凝佇時光鐫刻自我的飾物,祈願文字同樣貼身不須取下;摩挲製陶家載滿心意的作品,〈敬畏生活如同敬畏神祇〉;嗜甜者撕下邊緣烘烤酥脆的肉桂捲,配上糖漬核桃,讓食慾與記憶在胃底泛漣漪。陌異的他者在踏實又連續性的行動中被賦予意義,同時,作者亦不避諱深入自我的疆域,感受路途中的顛躓與苦澀。試探著同貓兒間關係的距離,也沉浸〈四弦的獨奏〉,在拉奏大提琴中,感受主與客的喧雜交談。最終明白寫作者〈信仰時間〉而非文字,看見生命在時光裡流洩的軌跡,相信事事終有各自的歸屬與流向。
張馨潔聚攏微末小事,撿拾煙火與星空的碎片,在轉瞬與恆常間思辨愛情與自我,織就斑斕絢爛的夜空。
周芬伶、崔舜華 專文導讀
徐珮芬(詩人)、張瑞芬(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陳繁齊(作家)、蔡俊傑(作家)、謝子凡(作家) 燦爛推薦
作者簡介|
張馨潔
伴養2.5隻貓,愛動物勝於愛人。曾獲全球華文星雲獎散文首獎,首部散文《借你看看我的貓》入圍2020年臺灣文學金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