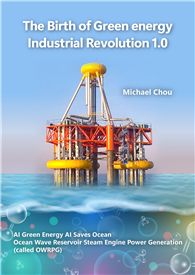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 繼《花樹下,我還可以再站一會兒》之後暌違五年最新散文集。
張曉風的散文,典雅耐讀,她出入古今、典籍、山水,日常事、平凡人,一草一木,在她筆下均自成風光。因此詩人瘂弦說:「讀張曉風不但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隨她穿過古中國文學的宗廟殿堂,更會發現宮中有宮,室內有室,千門萬戶,雍雍穆穆,而原型在焉。」
繼《送你一個字》、《花樹下,我還可以在站一會兒》之後的最新散文集。搭乘英國火車〈在D車廂〉她遙想《自己的房間》與吳爾芙,以及《坎特伯里故事》中的巴斯婦人和作者喬叟,宛如一場寧靜的英國文學之旅。因一篇四十年前紀念老友的文章,與老友親人千里相會,在感傷中又彷彿昨日再現。談〈楊絳與法塔〉,一個「護錢鍾書之才」一個「顧賓拉登之命」,她們勇於站在男人之前,顛覆一般站在男人背後的女人。她以不可思議的角度出手,把古人拉到眼前,看見在以地為紙學習認字寫字的歐陽修,透過大地這個「教室」翻轉命運,也聽見改變六祖慧能生命的瞬間,那熱人之耳、揪人之心的美妙吟誦聲。
她〈回想〉長年的筆耕,卻是一部私密的文學戀愛史。雖從寫小說教小說開始,進而創作戲劇、詩、兒童故事,但最常寫的是散文。〈談到寫作,最重要的是──〉,到底是先天的天分還是後天的努力重要?信手捻來,談及粵語、文字學、《花間集》等,以精簡的白話文轉譯古人話語,深入淺出且令人會心。
她致力提倡愛地球,將環保落實在生活之中,甚至還發願有朝做地球球長。搬至新居為了減少用電,種起橘子樹來抵抗西曬的烈日,居然也節約夏日的冷氣電力。在她筆下任何大小事都可逸趣橫生,浮想聯翩,周末一人在家享受毛豆莢的〈浪子大餐〉;關懷動物,從失去母親照顧的小水獺、曾經美麗的梅花鹿、流落異鄉的雲豹以及日漸稀少的石虎,以民胞物與的情懷,期望喚醒人們公平對待,尊重其他生物的生存權。
錦繡文章天地來,全書展現曉風在抒情美文之外全方位的創作,持續精進,創意無限。
作者簡介:
張曉風
她覺得,她欠古典文學一份情
如果不好好研讀,並好好轉手佈施
那就太對不起歷代古人了
由於持恆了六十多年的精湛創作
她成為後輩作者風從的典範
因為眼光獨到,所以出版社很希望她來選書
(如本社的《小說教室》)──雖然她不常答應
因為作品深入淺出,她的文章常在兩岸
入選教科書
曾經擁有特別的權力,可以大聲嚴責部長級的人物
但她不希罕那份權力
她最引以為榮的,卻是遠赴泰北山區
走過黃泥路,去探視苟延殘喘的二戰老兵
她的資料,網上可查的有一堆
但她的深意俠情只能在翻書聲中隱隱聽到
章節試閱
一篇四十年前的文章
二○一五年十一月,台北市,細雨霏霏,我去赴宴。是一場既喜悅又悲傷的午宴。
邀宴的主人是黃教授,她退休前曾是東吳大學經濟系的主任,邀宴的理由是想讓我跟她遠從天津來台的姪孫見面。說得更正確一點,是她去世四十年的亡夫的姪孫。
說是「姪孫」輩,其實年紀也只差五歲。至於「黃教授」,也是「官方說法」,我們其實是一九五八年一同進入大學的同學,後來,一起做了助教,並且住在同一間寢室裡,所以一直叫她「小寶」。如今,見了面,也照樣喊她「小寶」。這一喊已經喊了五十七年,以後,只要活著,想必也會照這個喊法喊下去。
宴席設在紅豆食府,是一家好餐廳,菜做得素雅家常而又美味,遠方的客人叫杜競武,他是我老友杜奎英的大哥杜荀若的孫子,老友逝世已四十年,他前來拜望杜奎英的妻子黃教授。他叫黃教授為叔祖母,我好像也順便升了格。至於他要求見我一面,是因為──照他說──讀了我寫他三老爺(杜公)那篇〈半局〉,深為其中活靈活現的描述感動。
「活靈活現?哈!」我笑起來,「你見過你三老爺嗎?你哪一年生的呀?就算見過,你能記得嗎?」
他也笑起來。
「理論上見過,」他說,「我一九四六出生,那時候三老爺住我們家,他一定見過我,我卻不記得他……他的行事風格嘛,其實我都是聽家裡人說的……。」
也許DNA是有道理的,他說話的聲口和神采也和當年杜公有那麼一分神似。但也許是少年時候因有台灣背景,受過許多痛苦折磨,也許是因為他比當年的杜公年紀大,他看來比較約斂自制,沒有杜公那種飛揚跋扈。但已足以令我在席間悄然一思故人一神傷了。
印尼有個島,島民有個奇怪的風俗,那就是在人死後幾年,又把死人從地底下一再刨出來,打扮一番,盛裝遊街。他們不覺如此做唐突了死者,只覺得應該讓大家能有機會,具體地再一次看見朝思暮想的那人。
我在報上看見圖片,心裡雖然不以為然,天哪!那要多花多少錢呀?世界如此貧薄,資源如此不夠用,厚葬怎麼說都該算一項罪惡。我怎麼知道那是厚葬呢?因為推算起來屍身要保持得那麼完整,而且又要維護得如此栩栩如生,一定是錢堆出來的。但是,看見圖片上那死者整齊的衣服、宛然的面目,以及陪行寡婦的哀戚和眉目間的不捨,仍不禁大為動容──雖然我與那人素昧平生。啊!人類是多麼想、多麼想挽回那些遠行的故人啊!我們是多麼想再見一眼那些精彩的朋友啊!
我此刻坐在雅緻的餐廳裡,跟五十多年前的老友的姪孫見面,彼此為的不就是想靠著反覆的陳述來重睹逝者的音容嗎?
曾經,身處兩岸的我們隔著那麼黛藍那麼憂愁的海峽、那麼綿延的山和那麼起伏的丘陵,以及那麼複雜的仇恨──然而,他輾轉看到了我的文字書寫,他覺得這其間有一份起死者於地下,生亡魂於眼前的魅力。我的一篇悼念,居然能令「生不能親其謦欬,死不及睹其遺容」的那位隔海姪孫,要從遠方前來向我致一聲謝。我一生所得到的稿費加版稅加獎章和獎金,都不及那老姪孫的俯首垂眉的一聲深謝啊!
兩天後,他回去了,山長水遠,也不知哪一天才會再見面。人跟人,大概隨時都在告別,而事跟事,也隨時都在變化──政局會變,恩仇會變,財富的走向會變,人心的向背會變。而這其間,我們跟歲月告別,跟伴侶告別,甚至跟自己曾經擁有過的體力和智力告別……
然而,我不知道「書寫」這件事竟可以如此恆久,雖然「壞壁無由見舊題」,如果兵燹之餘,所有圖書館都燒成灰燼,則一切的書寫只好還原為灰塵(啊!原來人類肉身的「塵歸塵,土歸土」的悲哀法則,也可能出現在文學或藝術品上)。但在此之前,這篇文章,它至少已活了三十九年半,讓遠方復遠方的族人,可以在青壯之年及時了解一段精彩的家人史,呼吸到故舊庭園中蘭桂的芬芳。
後記:一九七五年,八月,四十年前,我的朋友杜奎英謝世,我當時人在美國,不及送他最後一程。隔年我寫了一篇〈半局〉悼念他,刊於《中華日報》。不意近四十年之後,有一位朋友跨海而來,向我殷殷致謝。
楊絳和法塔
楊絳走了,在二○一六年五月。
她是嵩壽的才女,相較於同年年初去世,亦逾百歲遐齡的張充和(沈從文的小姨子)和她那種高華古典絕美的風格,楊絳顯然更親民、更幽默、更貼近大眾,而我哀悼她,其實別有傷懷處。跟她曾受過的政治迫害無關,那個迫害,應是凡在四○年代選擇留身在中國大陸的文人都極難避免的一劫。所以,既是個普遍現象,也就不談它吧!
可是,法塔又是誰呢?這個,也且等一等再說吧!
話說,晚年的時候,楊絳說了一句話,她說她對錢鍾書最大的貢獻,就是保全了他的「天真」和「孩子氣」。她甚至說,這兩種特質,曾是錢鍾書的老爸當年最提心吊膽的,他深怕錢鍾書會因而自誤,一輩子要吃大虧。
但楊絳不擔心,她選擇讓自己一輩子成為一個為錢鍾書擋子彈的人,錢鍾書因而可以「天真到死」、「孩子氣到死」。
做妻子,尤其是做才子的妻子,若不能「捨此身」以「取義」,則那位才子丈夫其實早就變成「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凡夫俗子了。
唉,這就讓我想起法塔,法塔的父親把十七歲的法塔當作禮物送給了賓拉登為妻,她的年齡當年只有賓拉登的三分之一,而且,她只是五分之一的妻子,他們共同生活了十年,她為賓拉登生了三個孩子。
二○一○年五月,美國海豹部隊攻入賓拉登密窟的那一夜,法塔勇敢地站在賓拉登身前,對狙擊手說:
「射我!」
狙擊手不想打她──因為她不夠斤兩──他們朝她的腿上射了一槍,意思是說:
「滾開,你的命,誰要呀?別來攪和了!我們忙翻了!」
法塔中槍倒地,肉盾沒有了,賓拉登遭兩槍斃命,一在腦,一在胸。
法塔護主無功,但一片赤膽忠肝卻是真的。賓拉登九一一雙子星大樓一案可以弄死二千九百七十三人,傷殘四千四百人──但他臨死之際卻竟有年輕美女願意為他殉身,也算豔福不淺。
不過,如果要說殉身,我想,做妻子的大概可以分成「文殉身」和「武殉身」。法塔是「武殉身」,楊絳是「文殉身」。「被武殉身」的丈夫十個大概有七個會心懷感謝,但「被文殉身」的丈夫十個大概只有一個會感恩,其他四個則視為理所當然,另外五個則渾渾然一無所知,他也未必生來就是忘恩負義之輩,只是他完全沒弄清楚妻子曾為他做了些什麼。
一般家庭,難免會有一兩個小孩,而如果做丈夫的又「立志」或「不小心」加入了「小孩國」,那,做老婆的就只好權當自己是「多生了一個『壞小孩』的媽媽」──噢,不對,應該是「多生了一個『壞老孩』的寡婦」。說她是寡婦,那是因為她已經沒有丈夫了,她的丈夫已經把自己列籍為孩子國的一員去了。
某位丈夫,是個詩人,五十多歲的時候,他的妻子出境幾天,事前冰箱裡當然為他準備了存糧。但他不知怎的忽然想喝稀飯。在他想,稀飯,有何難哉,詩都能寫的手,難不成不會煮稀飯?但,當然了,術業有專攻,他想,還是先來請教一些專家朋友吧!但不知為何,也許專家級的人都不屑教這種幼稚的把戲,那一天,詩人問了半天似乎不得要領。只是這一問倒暴露了一項祕密,詩人大概是不怎麼進廚房的。
此事已過了三十年,詩人後來有沒有學會「烹粥大術」,我不得而知。但根據我自己身為人妻的體會,家裡既然現放著勇於「赴湯蹈火」的「廚房人」,身為男士,誰又會笨到自己去下廚呢?──當然啦,現在流行「新好男人」,不過,卻有價無市,極端缺貨,一般不容易嫁到。相對於「新好男人」,大部分的女人嫁到的是「舊中男人」,也就是「舊式的」、「不怎麼好也不怎麼太壞的中等男人」。至於嫁到「陳腐壞男人」的也有,那就要自求多福了。
另有一位教授,他有天回家,對妻子和女兒說:
「哎,我們辦公室來了一個同事,他每天穿的衣服都是熨過的呀!」
他的妻子和女兒面面相覷,瞪大眼睛表情奇怪──卻都不說話,他發現不對,才問:
「怎麼啦?」
他的女兒說:
「你,你都不知道三十年來你的掛在衣櫥裡的衣服,件件也都是熨過的嗎?」
當然,家庭熨的衣服不像洗衣店熨得那麼那麼褲縫畢挺,但至少也是平平整整的。只是,三十年來他一直以為衣服本來就是那樣的乖乖順順服服貼貼,自己把自己吊進衣櫥裡去的。
要維持錢鍾書的「天真」和「孩子氣」要付什麼代價?楊絳沒細說,但其過程想必慘烈,足夠消磨壯志、扼殺才氣。
當然,或者有人會嫌我多事,人家夫妻恩愛,礙著你什麼啦?法塔和楊絳,都是自動為丈夫擋子彈的人,你替她們煩什麼呀?唉,法塔我不管,但楊絳卻是個才女,讓才女在亂世中「護寶」而行走江湖,那真須有「俠女的身手」和「犀牛皮般的耐磨度」。但,六十年下來,才女楊絳能讓自己依舊青鋒紫電冰雪聰明嗎?我若是楊絳的老母,可能會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說:
「唉,女兒呀!你個笨女兒呀!從小,人人不是都誇你聰明嗎?但你那『擋生活之子彈』的生涯,算哪一門子嘛?你也是我千辛萬苦培養出來的才女啊!雖說是為了『偉大的愛情』──但,他不是也愛你嗎?他又為你犧牲了什麼呢?」
也不是什麼大悲大痛,只是一點蝕骨腐心的酸惻,隱隱的,為才女楊絳。
不過,我也不要把話說得太過頭,錢鍾書其實並不算太壞的丈夫,他因留英,擅長用「立普頓紅茶」泡出好奶茶。(英國的畜牧業發達,他們的全脂牛奶真是好喝!)回國後沒有立普頓,他們試著用三合一配方,以湖紅、滇紅和祁紅三者互搭,就此一項絕技,也就足以傳為千古美談了。何況,留學期間,他還曾把自己打理好的早餐托盤呈獻給躺在床上尚未起身的楊絳。這個小動作,讓楊絳一輩子記得──一直記到一百歲。
可是他也常做些煩人的小壞事,例如打翻墨水瓶(楊絳要想辦法洗桌巾),弄壞台燈(楊絳要負責修理),所以,善後者永遠都是楊絳──咦?想不到她居然還會修電器呢!
不過,以上文中所舉的例子,還只是「正常社會」中的「瑣務之折磨」,至於楊絳身處「千古非常社會」,其間種種詭譎險惡的局面,一個女人要如何去對付,真不敢想像!文革之可怕,楊絳沒提,她為錢鍾書擋了多少禍,她也不細說,她僅僅只說了一句:
「文革以後,我就再也不怕鬼了!」
呀,隔著四十年,隔著大海,讀她晚年的這句話,想到曾經有一批成千上萬殘狠恐怖勝過惡鬼邪魔的「人」,仍不勝觳觫──那時候,身為錢鍾書的妻子,楊絳也許開著個「護才」的「楊絳鏢局」呢!
一篇四十年前的文章
二○一五年十一月,台北市,細雨霏霏,我去赴宴。是一場既喜悅又悲傷的午宴。
邀宴的主人是黃教授,她退休前曾是東吳大學經濟系的主任,邀宴的理由是想讓我跟她遠從天津來台的姪孫見面。說得更正確一點,是她去世四十年的亡夫的姪孫。
說是「姪孫」輩,其實年紀也只差五歲。至於「黃教授」,也是「官方說法」,我們其實是一九五八年一同進入大學的同學,後來,一起做了助教,並且住在同一間寢室裡,所以一直叫她「小寶」。如今,見了面,也照樣喊她「小寶」。這一喊已經喊了五十七年,以後,只要活著,想必也會照...
作者序
曾經,有個春天,有座春山 代序
他去拜訪朋友,朋友住在深山裡。他到的時候才發現,原來訪客不止他──跟他一起殷勤來訪的,還有春天。
於是,跟春天一起,他們推開柴扉,朋友站在院中一棵梨花樹下等著他們。
那棵樹本來已經開了幾朵小白花,但等春天剛一進門,那樹彷彿忽然醒了似的。他當下恍惚聽到似有若無的轟然一聲,接著整棵樹就爆出白紛紛的晶瑩剔透的花瓣,來不及地,一朵擠在另一朵的身旁,一層疊著一層地,綻開起來,樣子純潔認真到有點傻氣,像一營服從命令的小兵。
(來客的名字叫許渾,其實,「渾」字是個好字眼,不過為了不打擾閱讀,此事留待文後再來說它吧!他是晚唐人(七八八~八六○),但對我來說,他是我的房客,住在我家的書櫃裡,他的戶籍地址是「《全唐詩》五百二十八卷六○三六~六一四三頁(大陸中華書局版)」,他的隔壁房客一邊是「杜牧」,另一邊是「李商隱」。)
「時間還早,」山居主人崔處士(處士是古代對有才學卻隱居不仕之人的尊稱)說,「我們先出去走走,回來吃午餐剛好。」
「呀,太好了!」許渾放下褡褳,「我剛才一路就想著,這次要怎麼多看它幾眼山景,官場久了,眼睛都會翳霧掉!」
「不過,我帶你去,不是為了讓你去『看』什麼……」
「那,是去『聽』什麼嗎?」許渾自作聰明地問道。
「也不是,別亂猜,跟我走,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於是喝下一甌茶,他們便朝門外走去。
那一年春天其實並不特別,山中潮濕而微潤,山裡有樹、有花、有草、有鳥。小鳥本不希罕,但看到春天,牠們就一個個都爭著唱了起來,而且有時還是對唱、合唱。當然還有大小石頭,石頭也不希罕,但此刻的石頭都包著柔柔膩膩的青苔,像絨氈,並且發出幽微的綠色瑩光……
至於那條由崔處士領頭帶著走的山徑,沿途什麼也沒有,因為是闢出來留給人走路用的,主人甚至刻意修剪了幾根樹枝,免得擋路──但在這鬱鬱山林中的曲折小徑裡,如果你低頭仔細往地下看,你會發現,其實在柔軟的黃泥地上倒有些奇特的圖案──獸留下蹄痕,鳥留下爪印,蛇留下蹭跡,猴子留下果皮,小飛蟲留下屍體……
「等下一個路口,向右上方爬點坡,」崔處士說,「那條路不容易發現,因為沒人走,兩邊長滿了草,只有住在這座山裡的人才知道這條路。」
「如果沒人走,幹麼開出這條路來?」
「是我開的,」崔處士說,「我喜歡有這條路。」
看到許渾不解,崔處士只好又解釋一下:
「我種了些橘子,要去橘子園,開條叉路比較近,路,其實愈小愈好,走的人也愈少愈好。」
「怎麼這麼說呢?大路不是比仄徑好嗎?」
「因為人多了,就擠掉了萬物,你在通衢大道上看過蝴蝶飛嗎?你在長安鬧街上見過小鹿散步嗎?這個世界,人太霸道了,把什麼地盤都佔盡了。但這裡是山,也該為那些獸類、鳥類、蟲類、魚類留點老根底作活路吧!我開闢了橘子園,其實也有點對不起住在山裡的這些朋友,所以我不施肥,不除蟲也不剪枝,橘子結得又小又酸,我都任牠們去吃。我有空會常來果園看看,就是看看,看牠們居然也喜歡橘子,我很高興,但橘子不甜,我只拿它做橘醬、做酒,等會午餐你就可以吃到了……」
「哦──這──這──」二人正邊走邊說,許渾忽然神色一變,並且整個人都癡楞住了。
「天哪!」憋了半天,他終於叫喊出來,「這是什麼氣味呀?是花嗎?不對,不是花……沒有什麼花會香到這麼濃!」
崔處士含笑不語,只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氣。
良久。
「你見多識廣,我猜,你已經知道這是什麼氣味了。」
「我現在想起你剛才的話來了,我此刻懂了,你說要帶我出來走走,我以為你要讓我在春山中大開『眼界』,或者『耳界』──但原來不是,你要我的皮膚感知到溫暖而又涼颯微潤的風的觸摸,而且,讓我的鼻腔也感受那不知怎麼形容的香氣……」
「其實,說得出或說不出『是什麼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聞到了,你真真實實聞到了!而且,你已深深體悟並且深深喜悅了!於是你渾渾然變成這香氛的一部份,香在你裡,你在香裡。」
「好,我告訴你,我其實已經知道這是什麼香了,只是,因為跟我從前聞的氣味大不相同,所以把我搞糊塗了,但我知道──它是麝香。」
「你說對了,大唐朝的長安城或任何大城裡都不缺麝香。你做官,見過大場面,麝香,當然聞過。但在大城裡這東西只在三個地方出現,一個是皇帝和後宮的寢處,一個是聲色場所,還有一個,是講究的善於擺派頭的大家閨秀的深閨裡。那種麝香,都是人工再製作過的,用的時候要加熱薰蒸,那氣味如果讓母麝聞了,牠一定掉頭而去,並且說:『搞什麼鬼把戲呀,一股子怪味!』」
「我總算聞到真的麝香了!但,奇怪的是並沒見到麝呢!」
「牠如果在,你也看不到,牠才不願意讓人看到牠呢!牠只要讓母麝知道牠在哪裡就好了!」
「那麼,你知不知道,那隻麝,現在,是不是就在附近──不然,怎麼這麼香?每根草都香,每吸一口氣都香!」
「哈,哈,這些年你不是迷禪宗嗎?香很神祕,跟宗教一樣,你看不見它,卻又知道它就在那裡。你抓不到它,卻知道那是真真實實的,比你手裡拿著的那根竹杖還要真實。反正,說不清──而且,你待會回去,你自己也滿身麝香呢!至於麝在哪裡?你也就別管了。」
許渾一時渾噩起來,嘴裡顛顛倒倒不知念叨些什麼,然後,他不知不覺吟出一句:
「麝過春山啊──草自香。」
是的,大地有山,人很少陽光很多樹很多的山,山裡有公麝和母麝,牠們都是弱小的賤物,不像孔雀那麼漂亮,不像老虎那麼狠,甚至連一對可以打鬥或抵抗的鹿角都沒有。但公麝會放香,母麝會欣然答允那香味的呼喚。然後,小麝會出生,麝的生命會緜延(只要人類的貪婪沒讓牠們滅種)。新的春天來時,山林的荒煙蔓草中,仍然會騰越出被麝臍薰染過的令人萬般不捨的香氣(古人一般說「麝臍」,其實它的「香位置」在肚臍與陰囊之間的特別腺體)。
「哎呀!好詩句!」崔處士忍不住擊了一下掌,「我看,這野草身上有幸沾染到的香氣到冬天自會散淡消失。但,有你這句詩,一千年後的人還能恍惚聞到今天這春陽之中草莖之上的馥馥香氣,並且為之如癡如醉,你信不信?」
許渾笑而不答,他並沒有把握這句詩可以流傳多久,當然,也不是全然沒把握……但流傳不流傳關我何事?許渾想,我只要記住今日這一刻,我只要輕輕聞嗅,深深存貯,並在心靈底層留下這在陽光催促下的草莖上偶然凝聚的奇異芬芳。
一千年過去了,一千兩百年過去了,我坐在書桌前,深夜,隔著時空,遙遙感知那座我不知其名的春山。曾經,有個春天、有條小徑、有一帶百轉千迴的芳草劃下不可思議的軌跡,曾經有對公麝母麝留下牠們的愛情印記,那令人肅然凜然的生之悸動,那喚醒某些生命內心深處的神界芳香。
我,也是小草一莖吧?當巨大的美好經過,我甚願亦因而薰染到一縷馨香。
文後:
一、詩人許渾名字中的「渾」字是個後起字,也就是說更遠古的「甲骨文」、「鐘鼎文」中都沒有它。這兩種文字一般是官方在使用(廣義的官方包括宗教祭祀),所以多半是名詞或動詞性質的字,負責記載具體事件。但「渾」是形容詞(或副詞),因此,古文字中便不容易有它的一席之地了。
它第一次出現,是在許慎(東漢)的《說文解字》中(那時,有了九三五三漢字──其中有重疊的),「渾」字原始的解釋是「巨川大河之水流聲」。
我之所以嚕嚕嗦嗦來說此字,是因此字原義少人知。麻煩的是,一般人看到此字只想到「罵人的訾語」,如「渾蛋」或「你這渾人」。唉,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字呢!而如果你認定它就是「罵人字」,這就形成了「障」,有了這個「障」,你就看不到「渾」字之美了。
所以,我想要先「除障」。
二、其實,「渾」字所描述的是大自然的現象,自然現象無法定其美醜善惡。但在古老的字組詞彙中它是個好字,因為它的原義是指大水,特別是合流而為一的水,因衝擊而撞出的轟然巨響的那般聲勢。
下面且舉幾個跟「渾」有關的句子:
「財貨渾渾如泉湧。」(荀子‧富國)
「濤如渾金璞玉,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晉書‧山濤傳)
「上窺姚姒,渾渾無涯。」(韓愈‧進學解)
「其(指蘇洵、蘇軾、蘇轍三蘇之文章)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宋史‧蘇軾傳)
三、李渾的生年和卒年研究者分幾派意見,但所差不多,姑從(七八八~八六○)之說。他的籍貫也有不同說法,例如江蘇丹陽、河南洛陽、湖北安陸,我個人比較贊成「洛陽說」,其理由說來很可笑,因為洛陽在地理上比較偏西北,相對於中國東南方,是個「乾燥地區」。而李渾的詩作中非常愛寫「潮濕感覺」。這一點,讀者當然很快會發現,許渾於是居然得到一個奇怪的封號「許渾千首濕(詩)」,我想是和洛陽的乾爽(或乾燥)相較,「潮濕」是一種值得一寫再寫的新鮮經驗。
四、最後也提一下,許渾六代以前的先祖許圉師是武則天執政時的宰相。所以他算是個有根底、有家世的文人,雖然科舉方面一直不太如意。
五、為了作者,我又嚕嗦多寫了九百多字,原因可以話分兩頭,其一是人老了,常想「把話說得更明白一點」。當然,我的企圖也許會失敗,會遭人譏笑為「幹麼寫得如此『落落長』,煩不煩人呀!」其二是我對年輕一輩的耐心不太敢信任。他們中間肯主動去查書去追蹤資料的人不多。我不如乾脆做個「售後服務」,把包括原作者在內的故事細節多交代一下。
曾經,有個春天,有座春山 代序
他去拜訪朋友,朋友住在深山裡。他到的時候才發現,原來訪客不止他──跟他一起殷勤來訪的,還有春天。
於是,跟春天一起,他們推開柴扉,朋友站在院中一棵梨花樹下等著他們。
那棵樹本來已經開了幾朵小白花,但等春天剛一進門,那樹彷彿忽然醒了似的。他當下恍惚聽到似有若無的轟然一聲,接著整棵樹就爆出白紛紛的晶瑩剔透的花瓣,來不及地,一朵擠在另一朵的身旁,一層疊著一層地,綻開起來,樣子純潔認真到有點傻氣,像一營服從命令的小兵。
(來客的名字叫許渾,其實,「渾」字是個好字眼,...
目錄
代序:麝過春山草自香
輯一 在D車廂
在D車廂
一篇四十年前的文章
教室
故事兩則
楊絳和法塔
「你得給我盛餃子!」
「我們何不來談談各人的心願?」
日本故事中的風沙與皮箱
獨此一人
華人和民主之間,有點麻煩
「他人生病」和「自己生病」──兼懷饒宗頤先賢
忽然,他聽到朗朗的朗讀聲
金庸武俠,我的課子之書──悼金庸
「報告鴨子!」──寫在經國先生去世三十年之際
舞、舞雩和舞之子──贈楊桂娟教授
「給我一個西紅柿!」
唉,我的小妹子──寫給赤縣神州黃土地上荷鋤兼荷筆的女詩人,知名的,以及不知名的
輯二 請看我七眼,小蜥蜴
回想──我愛上一個傢伙
談到寫作,最重要的是──
我愛聽粵語
趨
一部美如古蕃錦的《花間集》──談千年前蜀中的「遠域文學」
垂直中國和朙
請看我七眼,小蜥蜴
「《選》學」和「被選學」
「欓」這個字
「哎呀!原來甲骨文是這麼美的!」
輯三 半粒米和山溪小蟹
同一個地球上的「球民」
如果我做了地球球長
幾乎沒有指紋的手指
愛恨「假公園」
前方有一棵樹,她說
收藏在我案頭美麗廢物
茶葉可喝,那,茶枝呢?
親愛的,請你聽我說兩個故事
半粒米和山溪小蟹
受邀的名單中,也有他
有事──沒事
浪子大餐
輯四 「人為萬物之靈」,真的嗎?
「人為萬物之靈」,真的嗎?
說到「麗」這個字的模特兒
唯一不值得珍惜的,是,牠的命
山羌的小確幸
麝‧麝香貓‧椰子狸‧咖啡
羊和美
另類詩人──珠光鳳蝶
「勿──勿──勿溜」啊!
那條通體瑩碧、清涼柔潤的緬甸翠玉
○熊?熊○?
長舌公‧長舌婦
除了為小水獺垂淚之外
你看過石虎嗎?
寫給雲新
台灣奇蹟
後記:捨不得不手寫漢字的人
代序:麝過春山草自香
輯一 在D車廂
在D車廂
一篇四十年前的文章
教室
故事兩則
楊絳和法塔
「你得給我盛餃子!」
「我們何不來談談各人的心願?」
日本故事中的風沙與皮箱
獨此一人
華人和民主之間,有點麻煩
「他人生病」和「自己生病」──兼懷饒宗頤先賢
忽然,他聽到朗朗的朗讀聲
金庸武俠,我的課子之書──悼金庸
「報告鴨子!」──寫在經國先生去世三十年之際
舞、舞雩和舞之子──贈楊桂娟教授
「給我一個西紅柿!」
唉,我的小妹子──寫給赤縣神州黃土地上荷鋤兼荷筆的女詩人,知名的,以及不知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