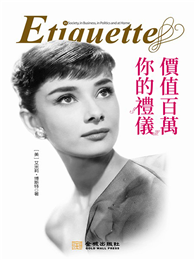★ 鍾怡雯暢銷經典散文,歷年得獎代表作
名家焦桐為文推薦
名家 瘂弦、陳義芝、陳萬益、柯慶明、李瑞騰、廖玉蕙、簡媜、王浩威、許悔之讚譽推薦
《垂釣睡眠》是鍾怡雯成名代表作之一,也是深受讀者歡迎,且獲獎無數的作品。她迴盪在台灣與馬來西亞,這二個緯度之間,以「想像之狐」和「擬貓之筆」,展現了散文的語言魅力,以及驚人的創造力。
她擁有金聖嘆所謂的才子獨具之慧眼靈心,能從極微處去觀照婆娑世界;靈眼明察,又能夠靈手捕捉,以詩的象喻生動地刻畫顯現。她寫周遭事物,不論是抽象的遺忘、具象的植物或是金魚,娓娓道出天地萬物皆有生命與情感。運用擬貓的筆法,描繪出〈髮誄〉中如貓般的糾纏主人的頭髮,或是〈可能的地圖〉中充滿貓性的陽光。另一方面,以豐沛的想像營構出赤道雨林和南洋時期的生活圖景,不但蘊含深厚的人文情感,更有對文化與歷史的關照。
鍾怡雯特為新版撰寫新序,並收錄鍾怡雯歷年創作品年表和個人得獎紀錄。
作者簡介:
鍾怡雯
一九六九年生於馬來西亞。元智大學中語系教授。著有散文集《河宴》、《垂釣睡眠》、《聽說》、《我和我豢養的宇宙》、《飄浮書房》、《野半島》、《陽光如此明媚》、《鍾怡雯精選集》、《麻雀樹》;論文集《莫言小說:「歷史」的重構》、《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靈魂的經緯度:馬華散文的雨林和心靈圖景》、《內斂的抒情:華文文學論評》、《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經典的誤讀與定位:華文文學專題研究》、《當代散文論I:雄辯風景》、《當代散文論II:后土繪測》、《永夏之雨:馬華散文史研究》、《翦影之秘:當代中國散文研究》;並主編《華文文學百年選》(16冊)、《馬華文學批評大系》(11冊)等多部選集。
章節試閱
垂釣睡眠 一定是誰下的咒語,拐跑了我從未出走的睡眠。鬧鐘的聲音被靜夜顯微數十倍,清清脆脆的鞭撻著我的聽覺。凌晨三點十分了,六點半得起床,我開始著急,精神反而更亢奮,五彩繽紛的意念不停的在腦海走馬燈。我不耐煩的把枕頭又掐又捏。陪伴我快五年的枕頭,以往都很盡責的把我送抵夢鄉,今晚它似乎不太對勁,柔軟度不夠?凹陷的弧度異常?它把那個叫睡眠的傢伙藏起來還是趕走了? 我耍起性子狠狠的擠壓它。枕頭依舊柔軟而豐滿,任搓任捶,雍容大度地容忍我的魯莽和欺凌。此時無數野遊的睡眠都該已帶著疲憊的身子各就其位,獨有我的不知落腳何處。它大概迷路了,或者誤入別人的夢土,在那裡生根發芽而不知歸途。靜夜的狗在巷子裡遠遠靜靜的此起彼落,那聲音隱藏著焦躁不安,夾雜幾許興奮,像遇見貓兒蓬毛挑釁,我突發奇想,牠們遇見我那蹺家的壞小孩了吧! 我便這樣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間中偶爾閃現淺薄的夢境,像一湖漣漪被一陣輕風吹開,慢慢的擴散開來。然而風過水無痕,睡意只讓我淺嘗即止,就像舐了一下糖果,還沒嘗出滋味就無端消失。然後,天亮了。鬧鐘催命似的鬼嚎。 我從此開始與失眠打起交道,一如以往與睡眠為伍。莫名所以的就突然失去了它,好像突然丟掉了重要零件的機器。事先沒有任何預兆,它又不是病,不痛不癢,嚴重了可以吃藥打針;既不是傷口,抹點軟膏耐心等一等,總有新皮長出完好如初的時候。它不知為何而來,從何處降。壓力、病變、環境太亮太吵、雜念太多,在醫學資料上,這些列舉為失眠的諸多可能性都被我否定了。然而不知緣起,就不知如何滅緣。可惜不清楚睡眠愛吃甚麼,否則就像釣魚那樣用餌誘它上鉤,再把它哄回意識的牢籠關起來。失眠讓我錯覺身體的重心改變,頭部加重,而腳下踩的卻是海綿。感覺也變得遲鈍,常常以血肉之軀去頂撞家具玻璃,以及一切有形之物。不過兩三天的時間,我的身體變成了小麥町││大大小小的瘀傷深情而脆弱,一碰就呼痛,一如我極度敏感的神經。那些傷痛是出走的睡眠留給我的紀念,同時提醒我它的重要性。它用這種磨人脾性損人體膚的方式給我「顏色」好看,多像情人樂此不疲的傷害。然而情人分手有因,而我則莫名的被遺棄了。 每當夜色翻轉進入最黑最濃的核心,燈光逐窗滅去,聲音也愈來愈單純、只剩嬰啼和狗吠的時候,我總能感受到萎縮的精神在夜色中發酵,情緒也逐漸高昂,於是感官便更敏銳起來。遠處細微的貓叫,在聽覺裡放大成高分貝的廝殺;機車的引擎特別容易發動不安的情緒;甚至遷怒風動的窗簾,它驚嚇了剛要蒞臨的膽小睡意。一隻該死的蚊子,發出絲毫沒有美感和品味的鼓翅聲,引爆我積累的敵意,於是乾脆起床追殺牠。蚊子被我的掌心夾成了肉餅,榨出無辜的鮮血。我對著那美麗的血色發呆,習慣性的又去瞄一瞄鬧鐘。失眠的人對時間總是特別在意,哎!三點半了!時間行走的聲音讓我反應過度,對分分秒秒無情的流失尤其小心眼。我想閱讀,然而書本也充滿睡意,每一粒文字都是蠕動的睡蟲,開啟我哈欠和淚腺的閘門。難怪我掀開被子,腳跟著地的剎那,恍惚聽見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在冷笑:「認輸了吧!」原來失眠並不意味著擁有多餘的時間,它要人安靜而專心的陪伴它,一如陪伴專橫的情人。 我趿上拖鞋,故意拖出叭噠叭噠的響聲,不是打地板的耳光,而是拍打暗夜的心臟。心有不甘的旋亮桌燈,溫暖的燈光下兩隻貓兒在桌底下的籃子裡相擁酣眠。多幸福啊!能夠這樣擁抱對方也擁抱睡眠。我不由十分羨慕此刻正安眠的眾生、腳下的貓兒、以及那個一碰枕頭就能接通夢境的「以前的我」。眼皮掛了十斤五花肉般快提不起來了,四天以來它們闔眼的時間不超過十二個小時,工作量確實太重了。黃色的桌燈令春夜分外安靜而溫暖。這樣的夜晚適宜窩在床上,和眾生同在睡海裡載浮載沉。 或許粗心的我弄丟了開啟睡門的鑰匙吧!又或者我突然失去了泅泳於深邃睡海的能力;還是我的夢囈干犯眾怒,被逐出夢鄉。總而言之,睡眠成了生活的主題,無時無刻都糾纏著我,因為失去它,日子像塌陷的蛋糕疲弱無力。此刻我是獵犬,而睡眠是兔子,牠不知去向,我則四處搜尋牠的氣味和蹤跡,於是不免草木皆兵,聲色俱疑。眾人皆睡我獨醒本就是痛苦,更何況睡意都已悉數凝聚在前額,它沉重得讓我的脖子無法負荷。當然那睡意極可能是假象,儘管如此,我仍乖乖的躺回床上。模糊中感到鈍重的意識不斷壓在身上,甜美的春夜吻遍我每一寸肌膚,然而我不肯定那是不是「睡覺」,因為心裡明白身心處在昏迷狀態,但同時又聽到隱隱的穿巷風聲遊走,不知是心動還是風動,或是二者皆非,只是被睡眠製造的假象矇騙了。那濃稠的睡意蒸發成絲絲縷縷從身上的孔竅游離,融入眾多沉睡者煮成的無邊濃湯裡。 就這樣意志模糊的過了六天,每天像拖個重殼的蝸牛在爬行。那天對鏡梳頭時,赫然發現一具近似吸血殭屍的慘白面容,立時恍然大悟,原來別人說我是熊貓只是善意的謊言。此時剛洗過的頭髮糾結成條,額上垂下的瀏海懸一排晶亮的水珠,面目只有「猙獰」二字可形容。頭髮嫌長了,短些是否較易入眠?太長太密或許睡意不易滲透,也不易把過多的睡意排放出去,所以這才失眠的吧! 到第七天,我暗忖這命定的數字或會賜我好眠,連上帝都只工作六天,第七天可憐的腦袋也該休息了。我聽到每一個細胞都在喊睏,便決定用誘餌把兔子引回來。那是四顆粉紅色、每顆直徑不超過零點五公分的夢幻之丸,散發著甜美的睡香,只要吃下一粒,即能享有美妙的好夢。 然而我有些猶豫,原是自然本能的睡眠竟然可以廉價購得。小小的一顆化學藥物變成高明的鎖匠,既然睡眠之鑰可以打造,以後是否連夢境也能夠一併複製,譬如想要回味初戀酸酸甜甜的滋味,就可以買一瓶青蘋果口味的夢幻之水;那瓶紅豔如火的液體可以讓夢飛到非洲大草原看日落;淡黃色的是月光下的約會;藍色的呢!是重回少年那段歲月,嘗嘗早已遺忘的憂鬱少年那種浪漫情懷吧! 我對那幾顆小小的東西注視良久。連自己的睡眠都要仰仗外力,那我還殘存多少自主,這樣活著憑的是甚麼?然而我極想念那隻柔順可愛的兔子,多想再度感受夢的花朵開放在黑夜的沃土。睡眠是個舒服的繭,躲進去可以暫時離開黏身的現實,在夢工場修復被現實利刃劃開的傷口。我疲弱的神經再也無法承受時間行走在暗夜的聲音。醒在暗夜如死刑犯坐困牢房,尤其月光令人發狂的恐慌。陽光升起時除了一絲涼淡淡的希望,伴隨而來是身心俱累的悲觀,彷彿刑期更近了,而我要努力撐起鈍重的腦袋,去和永無止盡的日子打仗。 我掀開窗簾,從沒看過那麼刺眼的陽光,狠狠刺痛我充血的眼睛,便刷的一聲又把簾子拉上。習慣了蒼白的月光和溫潤微涼的夜露,陽光顯得太直接明亮。黑夜來臨,我站在陽台眺望燈火滅盡的巷子,彷彿一粒洩氣的氣球,精神卻不正常的亢奮起來,如服食過興奮劑,甚至可以感覺到充血的眼球發光,像嗜血的獸。 我想起大二時那位仙風道骨的書法老師。上課第一節照例是講理論,第二節習作。正當同學把濃黑的注意力化作墨汁流淌到紙上,筆尖和宣紙作無聲的討論時,突然聽到老師低沉的聲音說:「唉!我足足失眠兩個星期了。」我訝然抬頭,還撇壞了一筆。老師厚重鏡片後的眼神閃現異光,那是一頭極度渴睡的獸。我正好和他四目相接,立刻深深為那燃燒著強烈睡慾的眼神所懾,那是被睡意醃漬浸透、形神都淪陷的空洞,或許是吸收了太多太多的夜氣,以致充滿陰冷的寒意。然而他上起課來仍是有條有理,風格流變講得井然有序,而我現在終於明白他不時用力敲打自己的腦部、揉太陽穴,一副巴不得戳出個洞來的狠勁,其實是一種極度無奈的沮喪。他是在叩一扇生理本能的門,那道門的鑰匙因為芸芸眾生各持一把,丟掉了借來別人的也無濟於事,便那麼自責的又敲又戳起來。 然則如今我終於能體會他的無奈了。可怕的是我從自己日趨空洞的眼神,看到當年那瞬間的一瞥復又出現。晝伏夜出的朋友對夜色這妖魅迷戀不已,而願此生永為夜的奴僕。他們該試一試永續不眠的夜色,一如被綁在高加索山上,日日夜夜被鷲鷹啄食內臟的普羅米修斯,承受不斷被撕裂且永無結局的痛苦。然而那是偷火種的代價和懲罰,若是為不知名的命運所詛咒,這永無止境的折難就成了不甘的怨懟而非救贖,如此,普羅米修斯的怨魂將會永生永世盤桓。 失眠就是不知緣由的懲罰。那四顆夢幻之丸足以終止它嗎?我聽上癮的人說它是嗎啡,讓人既愛又恨,明知傷身,卻又拒絕不了,因為無它不成眠。這樣聽來委實令人心寒,就像自家的鑰匙落入賊子手裡,每晚還要他來給自己開門。於是我便一直猶豫,害怕自己軟弱的意志一旦肯首,便墜入深淵永劫不復了。 睡眠的慾望化成氣味充斥整個房間,和經過一冬未晒的床墊、棉被濃稠地混合,在久閉的室內滯留不去,形成房間特有的氣息。我以為是自己因失眠而嗅覺失靈的緣故。一日朋友來訪,我關上房門後問:「你有沒有聞到睡眠的味道?」他露出不可思議、似被驚嚇的眼神,我才意識到自己言重了。 就像我沒有想到會失眠一樣,睡眠突然倦鳥知返。事先也沒有任何預示,我迴避鏡子許久了,一如忘了究竟有多少日子是與夜為伴,以免嚇著自己,也害怕一直叨念這一點也不稀罕的文明病,終將為人所唾棄。何況失眠不能稱為「病」吧!如此身旁的人會厭惡我一如睡眠突然離去。而朋友一旦離開就像逝去的時間永不回頭,他們不是身體的一部分,亦非血濃於水的親密關係,更不會像丟失的狗兒會認路回家。 那天清晨,自深沉香醇的夢海泅回現實,急忙把那四顆粉紅色的夢幻之丸埋入曇花的泥土裡。也許,它們會變成香噴噴的釣餌,有朝一日再度誘回迷路的睡眠;也可能長出嫩芽,抽葉綻放黑色的夜之花,像曇花一樣,以它短暫的美麗溫暖暗夜的心臟。
垂釣睡眠 一定是誰下的咒語,拐跑了我從未出走的睡眠。鬧鐘的聲音被靜夜顯微數十倍,清清脆脆的鞭撻著我的聽覺。凌晨三點十分了,六點半得起床,我開始著急,精神反而更亢奮,五彩繽紛的意念不停的在腦海走馬燈。我不耐煩的把枕頭又掐又捏。陪伴我快五年的枕頭,以往都很盡責的把我送抵夢鄉,今晚它似乎不太對勁,柔軟度不夠?凹陷的弧度異常?它把那個叫睡眠的傢伙藏起來還是趕走了? 我耍起性子狠狠的擠壓它。枕頭依舊柔軟而豐滿,任搓任捶,雍容大度地容忍我的魯莽和欺凌。此時無數野遊的睡眠都該已帶著疲憊的身子各就其位,獨有我的不...
推薦序
想像之狐,擬貓之筆 焦桐
──序鍾怡雯《垂釣睡眠》
一九九七年的台灣文壇,鍾怡雯無疑是備受矚目的散文選手,她不但同時勇奪難度相當高的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的散文首獎,也在這一年獲得華航旅行文學獎、梁實秋散文獎,和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
中國時報、聯合報文學獎之所以備受重視,跟社會體質、作品出版管道有關。缺乏知名度的年輕人想要在文壇露臉,委實困難重重,兩報副刊的版面又非常擁擠,一個新進作家想讓自己的名字經常出現於兩報副刊不容易。因此文學獎的得獎就是一條捷徑,是文藝青年一夕成名的捷徑。我曾在一篇論文裡指出:台灣這些文學獎的存在,尤其是影響力最廣泛深遠的兩報文學獎,具現為一種權力位階的生產,評審被世俗化為德高望重者,參賽者被世俗化為有待提攜的後進──只有獲獎者才能靠那名聲晉升位階,甚至轉而擔任評審,獲獎者的名聲不是孤立的榮譽或金錢利益,它通過媒體的權力操作,取得某一種合法性的位階。這種尊卑關係在每一次的文學獎活動中重複生產出來。換一個角度看,在徵文比賽中,得獎者對落選者而言也是有權力的;得獎者的權力表現為一種無意圖的影響(unintended influence),影響後來再參賽者的寫作手段。
長期以來因為有機會主辦、評審文學獎,我知道許多年輕人每年剛好寫了足敷徵文比賽的作品,卻鮮見其他作品發表,好像文學創作的目的只是得獎。這幾年,台灣重要的文學獎徵文,鍾怡雯幾乎無役不與、攻無不克,她的文學成績和聲名,早已不是等待提攜的「文壇新秀」。令人敬佩的,並非她囊括了多少散文獎項的成績,而是在參與這麼多文學賽事之餘,還能保持豐沛的創作力,持續發表,量與質俱佳。我知道她是一個用功讀書的寫手,參賽之於她,顯然希望能保持選手身分,那是一種勇於跟其他寫手同台競技的運動精神,一種保持高度創作警覺的自省能力。據我多年來對台灣文學生態的觀察,這樣認真思索、仔細創作的人才恐怕是值得嚴加保護的稀有種了。
《垂釣睡眠》是鍾怡雯的第二本散文集,收錄二十篇規模相當一致的作品,在藝術性較第一本散文集《河宴》有令人驚異的躍進。裡面多數篇章心思細膩,構思奇妙,通過神祕的想像,常超越現實邏輯,表現詭奇的設境,和一種驚悚之美,敘述來往於想像與現實之間,變化多端,如狐如鬼。〈髮誄〉裡的一頭長髮「耍起脾氣來是隻固執的鬼」,「老是要以那媲美狐狸尾巴的優雅線條,較暗夜更鬼魅的髮色,以及令禮教不安的儀態而沾沾自喜」;〈說話〉的敘述者在換水時,發現魚缸裡的水竟是魚魂和語屍,是金魚所「傾吐的心事,或許還浸泡著幾十尾魚兒的遺言和魂魄」。
也許是鍾怡雯在描述周遭的事物時慣用比擬(personification),她筆端的天地萬物皆有生命和情感,和敘述者互相感應、對話;她總是設定相愛相纏又相怨相斥的兩方,使得美麗與哀愁、親密與疏遠纏綿不休,抽象如〈忘記〉裡描述遺忘「是一種會繁殖的細菌,它逐漸吞噬了記憶的領域」;具象如〈說話〉裡陽台上「老是蠢蠢欲語」的植物;和魚缸裡死到剩下最後一條的金魚,不但會「吐悶氣」,還亟欲交談。敘述者似乎總是能夠洞悉它們的精神意志,經常和它們對話、抬槓、拌嘴,形成精神良伴;〈傷〉描寫手臂上的瘀傷,「像小妖一樣玩起變色的遊戲」,描寫左腳大拇指踢到石頭受創流血,「腳趾頭戴了一頂俏皮的豔紅小帽,傷口齜牙咧嘴對我笑,鮮血在快樂的唱著雄壯的進行曲」;〈垂釣睡眠〉描寫失眠,竟是睡眠離家出走,「迷路了,或者誤入別人的夢土」……等等。
更準確地說,鍾怡雯慣用的比擬是一種擬貓法──萬物多像是她豢養的寵物貓:身體柔軟,卻具有銳齒利爪;楚楚依人,卻難能完全馴服。我不知道她何以如此愛貓?貓的身影卻頻繁地出現於文本,在〈換季〉裡,午後的陽光很有「脾氣」,是一頭「性嗜傷人的暴獸」,當夏秋之交,「夏的爪牙翻天覆地不甘心地喧鬧」;〈鬼祟〉裡的襪子不但有著鬼鬼祟祟的脾氣,賊兮兮地,鼠性十足,是她家貓咪最喜愛的寵物;〈可能的地圖〉則處理一段溯源之旅,追尋祖父生活過的小村落,卻每天徒勞往返,敘述者每天早晨頂著朝陽出發,沐著夕照踏上歸途,連那陽光也是貓性十足,「像條大白舌頭,舐走希望,留下日益深厚的困惑和沮喪」;〈髮誄〉裡的頭髮更是有知覺、有獨立意志,貓一般,糾纏著主人。
貓的意象如此繁複地充滿文本。又如〈傷〉描寫一種令人神傷的眼神,「專門勾人的三魂六魄,也令人忘卻牠藏匿在優雅舉止中的爪子。總要等到牠無情的抽身離去,才赧然發現記憶裡血色飽滿,楚楚動人的爪痕」;〈癢〉以皮膚過敏為引,描寫早晨醒來臉頰出現兩條抓痕,「那痛楚亦十分懂事,好像是竭力忍著,不得已才痛一下,盡量避免我嫌棄它」,「那癢是過度寵溺的小孩,愈疼它便愈放肆」,因此,癢便有著貓一般的性格和脾氣,她說,「我多麼羨慕貓兒抓癢時那種瞇眼打呼,全然陶醉的幸福。一隻健康的貓從抓癢裡享受全然不假外求的幸福,那認真的表情彷彿在說:啊哈!我『抓』到這個『癢』了!」。此外,〈時間的焰舞〉裡敘述者燃燒收藏多年的信件,那剛點燃的火苗「小心翼翼舔了那張嫩黃的紙張,好像在試吃新鮮的乳酪」;〈禁忌與祕方〉述及迷信與知識開發的程度相關,人跡罕至的地方有較多的禁忌和民俗療法,資訊普及的城市則難得逮到禁忌與祕方「一兩隻畏畏縮縮的小爪牙」,諸如此類的例子俯拾皆是。
鍾怡雯擅長比喻,她的散文語言常見詩語言的豐富表情,如使用某一詞來表達多重的態度和情感的歧義性(ambiguity)。在〈換季〉裡,她描寫大自然的季候更迭,其中重疊著一段情感生活的失落變易,情感的變易中又重疊著身體、思想、觀念的轉換,因此夏天和秋天在本文裡遂形成語義重疊(multiple meaning)。
這種複義語言總是通過局部特寫來彰顯,尤其是由小觀大的功力,如〈徊盪,在兩個緯度之間〉描寫台北、吉隆坡兩個國際化中的都市,是聚焦在台北來表現的,而描寫台北其實是描寫師大路,師大路的面貌又通過味覺來彰顯──記憶裡馬來攤子的炸curry puff,比較了台北麵包店的咖哩角;記憶裡的馬來人情掌故,比較了台北街頭的人情掌故;青少年的生活經驗,比較了負笈台灣求學的生活經驗。多層次的描寫技術,表現繁複的情感,於是鄉愁的滋味,摻進了情感的滋味、土地認同的滋味。
貓的嗅覺自然是敏銳的,氣味,在擬貓高手鍾怡雯的散文藝術裡,就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驚情〉對一封情書的記憶竟然是氣味,「它笨笨傻傻的氣味,令人想起帶點油垢味的木料地板,肥滾滾的小黑狗沒命地搖尾示好,或是企鵝走路的滑稽」,她藉這種「笨笨的氣味」描繪追求女孩的青澀少年,展現特立獨行的敘述手段。
鍾怡雯擅長用氣味來挖掘記憶,用氣味思索,甚至營造狐鬼般奇詭的意境。這是一種文字嗅覺,也是貓性的延伸。〈茶樓〉處理氣味就十分精采,敘述者追憶童年時期的舊茶樓,從氣味出發,筆觸乾淨俐落,身手不俗──「茶樓的空氣總是瀰漫著一股特殊的味道,像曝晒過度的乾柴、龜裂的泥土。我一直以為那就是『老』的氣味,這種氣味和咖啡、麵包、砂糖混合得十分融洽,復與沙啞、粗俗乃至不入流的談話契合無間。」這自然是一種懷舊的氣味,只藉氣味,竟神準描繪茶樓的市井風光,和人情世故。此文描寫「老」非常傑出,敘述者童年在茶樓吃燒賣配菊普茶,那壺茶,「暗褐色的茶湯上浮著一朵飽蓄水分的黃花」,除了味覺的享受、養生的意義,更有著視覺的美感,「偶爾菊花一動,像老者混濁的眼神被記憶的靈光觸動乍現的一閃清光」,短短幾句,從容出入物與人之間,文字飽滿,寓意極為豐富,對全文所鋪陳和渲染光陰之推移、人事景物之變遷、心境之更改有畫龍點睛之妙。
〈漸漸死去的房間〉對人事的追憶和懷念,也通過氣味來實踐。敘述者藉家裡一個毒瘤般的房間,憑弔住在這房間裡的兩個人──自殺身亡的曾祖母,和滿姑婆。由於曾祖母長年臥病、排泄失禁,被家族隔離在一個陰黯、汙穢的房間,敘述者以氣味來經營這個房間的氛圍,那是一種生命腐朽的氣味,「混濁而龐大的氣味,像一大群低飛的昏鴉,盤踞在大宅那個幽暗、瘟神一般的角落。」鍾怡雯經營的這種氣味不僅表現於嗅覺,更高明的是表現於聽覺,如滿姑婆「低緩的嘆息總是無所不在:『她養了我這麼多年……』它與混濁的氣味攪拌之後,充塞大宅。」嗅覺攪拌聽覺,使得記憶中的氣味更加濃重,徘徊不去,這種手法,帶著聊齋般的狐鬼氛圍,正是鍾怡雯揉合想像之狐、現實之鬼的文字魅力。 這樣的文字魅力表現在描繪景物上,十分可觀,如〈茶樓〉藉著幼童的眼光,觀看早晨老人們聚集的茶樓風光,「無數分《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的上半身銜接一雙雙粗細不同顏色不一的腿」,這種狀物功力要配合靈敏細膩的觀察和想像,等閒不能至。鍾怡雯的想像,帶著記憶的景深,很是幽邃。
她在〈時間的焰舞〉自述少女時代作文,虛構了許多故事,「把自己置入想像的情節,不斷修飾和重塑,以分歧的面貌和不同的個性去參與虛構的遊戲,藉此遊離和逃避現實的無趣」;又如獲第十九屆聯合報散文首獎的作品〈給時間的戰帖〉也是一篇虛構性質濃厚的散文,她在得獎感言中說:「我不喜歡讓散文正面洩露真實的生命經歷」。虛構與否,其實很難檢證,散文雖然帶著較濃的非虛構特質,我們卻難以求證創作文本和現實文本的真實程度。文學是另一種真實。鍾怡雯如此歡喜以虛構的辦法經營散文藝術,曾再三表露這種創作取向,我猜想,虛構是她開展想像的敘述策略,企圖使想像的景深幽邃;此外,這個辦法顯然充滿叛逆的樂趣,對散文的非虛構特質進行地下革命,並逼使讀者的偷窺慾羽而歸。
從《河宴》到《垂釣睡眠》,鍾怡雯繼續致力於局部特寫、複義語言的開發,除了感性抒情的基調,更多了議論層次,如〈說話〉從敘述者和一尾金魚相對欲言,思索語言與情感之間的糾葛和依存,並略帶批判地反省創作倫理,基本上這篇文章旨在立論語言,語言的功能與困窘,寂寞,和沉默的美德;〈傷〉論述具體和抽象的傷痛,知感交融;〈癢〉喻發呆為抓癢,形容癢為生生不息的意念,從而展開議論。最明顯的例子莫非〈門〉,敘述者為了畢業論文,來到偏僻的深山村落,為避免受打擾,乃在借居的房舍裝置一扇門,然則「門違反了他們坦蕩蕩的生活習性」,「反而挑起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偷窺慾與好奇心」,敘述者從田野調查出發,聚焦在對「門」具象、抽象的思考,從裝門的經驗、文化差異、人際關係,到國家民族之開放改革與閉關自守之間展開辯證。
全書大致上維持低緩的基調,〈癢〉和〈驚情〉則呈現稍強的輕淡、流暢、幽默感。尤其〈驚情〉是應聯合文學製作情人節專輯而作,寫情書的故事,輕易就會纏綿悱惻或感傷浪漫,然則鍾怡雯卻逆向操作,渲染少女懷春的夢想如何被隔壁班男生的情書所摧毀,將可能形成的一齣愛情肥皂劇,巧妙扭轉成青春爆笑劇。這種效果是修辭策略的轉變,包括語言的輕淡感,和故事的輕淡感。《垂釣睡眠》分為兩卷,卷一大抵記述台北生活的感思和體悟,裡面頗有另創格局的佳構;卷二稍稍延續了《河宴》的精神面貌,營構赤道雨林和南洋時期的生活圖景,不同的是蘊含更深厚的人文情感,和對文化與歷史的關照。
想像之狐,擬貓之筆 焦桐
──序鍾怡雯《垂釣睡眠》
一九九七年的台灣文壇,鍾怡雯無疑是備受矚目的散文選手,她不但同時勇奪難度相當高的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的散文首獎,也在這一年獲得華航旅行文學獎、梁實秋散文獎,和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
中國時報、聯合報文學獎之所以備受重視,跟社會體質、作品出版管道有關。缺乏知名度的年輕人想要在文壇露臉,委實困難重重,兩報副刊的版面又非常擁擠,一個新進作家想讓自己的名字經常出現於兩報副刊不容易。因此文學獎的得獎就是一條捷徑,...
目錄
舊日終須記(新版代序)
想像之狐,擬貓之筆 焦桐
──序鍾怡雯《垂釣睡眠》
卷一 時間的焰舞
說話
垂釣睡眠
髮誄
癢
傷
鬼祟
換季
驚情
忘記
時間的焰舞
給時間的戰帖
卷二 可能的地圖
蟒林‧文明的爬行
茶樓
葉亞來
門
可能的地圖
漸漸死去的房間
神在
禁忌與祕方
徊盪,在兩個緯度之間
渴望(後記)
鍾怡雯創作年表
舊日終須記(新版代序)
想像之狐,擬貓之筆 焦桐
──序鍾怡雯《垂釣睡眠》
卷一 時間的焰舞
說話
垂釣睡眠
髮誄
癢
傷
鬼祟
換季
驚情
忘記
時間的焰舞
給時間的戰帖
卷二 可能的地圖
蟒林‧文明的爬行
茶樓
葉亞來
門
可能的地圖
漸漸死去的房間
神在
禁忌與祕方
徊盪,在兩個緯度之間
渴望(後記)
鍾怡雯創作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