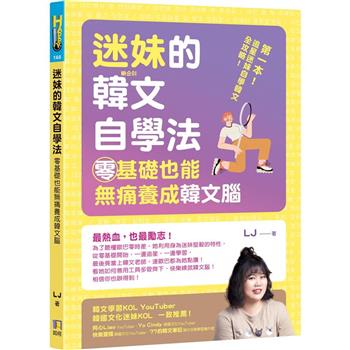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如此歲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80 |
詩 |
$ 316 |
華文現代詩 |
$ 316 |
文學作品 |
$ 352 |
中文書 |
$ 352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如此歲月
一代詩魔洛夫
天涯漂泊的代表作〈漂木〉
鎔鑄古今的〈唐詩解構〉
明心見性窺見禪趣的現代禪詩
充滿實驗精神與創造性趣味的〈隱題詩〉……
寫詩超過六十年,洛夫不斷錘煉詩的語言,進而營造無邊的遼闊意象,更由現實中翻轉出超現實的詩情,奠定了個人的特殊風格,詩壇美稱他為「詩魔」,影響一代又一代的新詩創作者。
本書收錄洛夫自選一九八八年至二○一二年間的一○四首菁華詩作,尤其晚近作品超脫現代而回歸質樸,語境更為純淨老練,多采的形式通古今上下,真摯的內容究天地人間。包括傳誦兩岸三地的史詩鉅作〈漂木〉、突破文字局限並造成模仿風潮的隱題詩、融古典於今日的〈唐詩解構〉,以及包裹濃濃父愛的親情詩作等等。書中呈現寬廣的詩世界,思想深邃、表現手法繁複多變。詩壇如此評稱:「從明朗到艱澀,又從艱澀返回明朗,洛夫在自我否定與肯定的追求中,表現出驚人的韌性。」
增訂新版收錄莫凡寫於洛夫逝世週年的〈念父親──詩魔洛夫〉,以詩歌形式道出追憶懷念與父子深情;陳芳明〈我的洛夫閱讀史〉,則以讀者角度細訴人生不同階段對於洛夫詩作的深刻領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