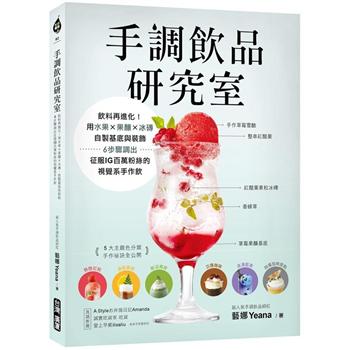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是我睡了他們,不是他們睡了我。」
李昂經典代表作《北港香爐人人插》指涉身體即政治,
敘寫身處男性凝視下的女性──於政治、國族、情慾與道德間的角力
探討女性主義不可或缺的台灣小說經典作,於一九九七年出版時,屢被政壇「對號入座」掀起波瀾議論,時隔二十五年後,女性權益備受討論與關注的今日,更顯批判力道──女人是否用自己的身體來換取權力?
「北港香爐」原為一句街談巷語,更為諷刺女性代表句,李昂挪用「人人插」意涵為小說篇名,小說集收錄〈戴貞操帶的魔鬼〉、〈空白的靈堂〉、〈北港香爐人人插〉和〈彩妝血祭〉四篇獨立並互文的小說名作,合則為長篇「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政治小說,以李昂於九○年代參與政治運動的經驗,透過政治遺孀、代夫出征的烈士之妻、色藝雙全的女民代、婦女運動倡議者、獨立建國運動之母等視角,描繪身處台灣黨外運動時期下被凝視的多重女性面貌,如何以身體顛覆以男性為權力中心的政治場域。
李昂以小說銳利地劃開男性凝視下的女性身體於國族、道德、情慾、權力下的擺盪,將身體即政治的連結具現為千絲萬縷的關係,透過《北港香爐人人插》交織多重話語的敘事策略,見證台灣的性、道德與政治論述的消長。
本書特色
★身體情慾與政治權力的糾纏──台灣文學經典《北港香爐人人插》出版25週年增訂紀念版
★特別收錄李昂新版自序、漫畫名家柳廣成跨界轉譯漫畫精選、〈彩妝血祭〉舞台劇劇照
★限量作者親筆簽名,值得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