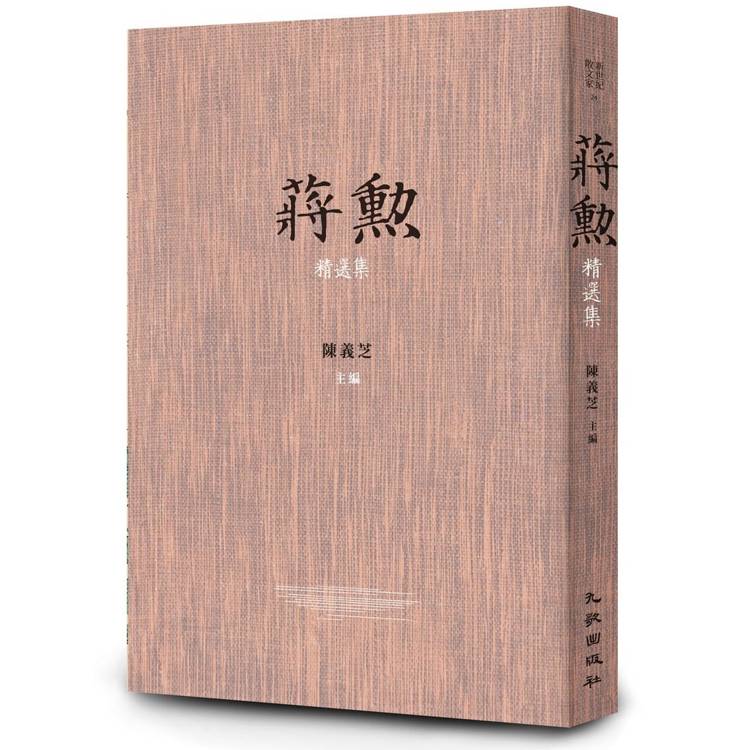推薦序
善述與喜捨 張曉風
善述是什麼意思 「善述」這兩個字,如果翻譯出來,就是「善於敘述」的意思,但善於敘述又是什麼意思呢?由於這是我統括蔣勳平生的字眼,所以有必要解釋一下。 善述,如果從文法觀念來看,算是個「述語」。有趣的是,句子中的主詞和受詞卻都省略了,為什麼省略呢?因為,好像沒有必要去說。因為,反正人人明白。 原來,善述,一般都指為人子者,善述其父,(當然,如果你要說成子女善述父母,也請便,但那並非古人的意思)《禮記.中庸篇》裡有: 父作之 子述之
的句子,換言之,在儒家思想體系中,所謂「善述」,指的便是孩子善於敘述親長。然而,兒子善於敘述父親又是什麼意思呢?簡單的說,那便是「孝」的意思。 所以,「善述」,就等於「孝」,為什麼?原來,最高級的孝道就是能好好把父親顯揚出來。 這種父子之倫當然也可以化為廣義的,像孔子,就頗以敘述往聖為他的職志,甚至不惜說出「述而不作」的話來。孔子平生最重要的事與其說是教育弟子,不如說是在一個詭異而充滿變數(其實不一定是壞,也不一定是衰世)的、令人迷惘不知所措的年代,把可以依循的典籍找出來,重新加以詮釋和建構;其中包括抽樑換柱,舊屋新裝,除蟲去蠹,鑿池掘井,總之,務將傾頹的大廈回陽,成為可以遊可以憩也可以居可以藏的地方。
美的導師 台北蔣勳,人道是:「蔣老師」。 二十世紀末,海峽兩岸不知怎麼吹起一股「稱師風」,到處聽到叫人老師之聲。海這邊還好,海那邊用得很浮濫,連師母師丈也一併變成了「老師」,好像禮多人不怪似的。台灣稱人老師其實多半是真的老師。蔣勳在五十歲那年號稱要送自己一項大禮,這禮是辭去他專任的教職,還自己以自由之身。奇怪的是,不當專業老師,他的施教範圍反而更大了。他的職業欄裡輕易可以寫出如下的工作:
畫 家 詩 人 散文家 小說家 影劇音樂舞蹈的評論家 電台節目主講人 演說家 美術之旅的解說人 美學學者
此外,還主掌「聯合文學」雜誌,且不時寫字送人,或唱歌怡人,或說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話娛人。 「台北蔣勳」基本上是一個善述者。善於把低眉垂睫的美喚醒,讓我們看見精燦灼人的明眸。善於把沉啞瘖滅的美喚醒,讓我們聽到恍如鶯啼翠柳的華麗歌聲。 就善述而言,蔣勳可謂是主流文化之美加上庶民文化之美的孝子,他慎重的敘述了這一對父母的行誼,讓世人為之斂容生敬──至於這位孝子會不會叛逆或出走,那又是另一件值得玩味的事了。
台北風流人物 而我說「台北蔣勳」,其心情一如說「草堂杜甫」或「蜀人張大千」。像蔣勳這種彷彿南朝的人物,彷彿從《世說新語》中走出來的精彩人物,絕對一眼便可辨識出來是台北的產物。雖然他的生平也和西安和福建和舟山群島有過一點關係,但他的主要成分還是「台北之子」。 像蔣勳這種人,我把他算作「第一代半的外省人」。凡自己以成年人身分來台的,我算他們是「第一代外省人」。第一代的外省人在此地所生的,我叫他「第二代外省人」。但當年被第一代外省父母或牽或抱帶著來的小孩,我在生物學上把他們作更精準的分類,叫做「第一代半外省人」(如白先勇)。這批人和「末半代日治人」(如黃春明)加起來成為文化上極重要的一個世代。 從巴黎留學回來的蔣勳,你當然可以算他是一個「地球民」。但事實上當他第一次重返西安街頭,不免萬分驚駭的發現「原來滿街上的人,說的都是我母親講的那種話呀!」而在台灣,在高山部落的夜宴裡,被原住民的小米酒灌醉欲死的,也是蔣勳。所以,你可以稱他為「一個古今中外客,一介東西南北民」。如果真要為蔣勳定其經緯度的座落方位,我仍然要說,他是「台北蔣勳」。台北的風流人物如何定義,恐怕要寫整整一本書吧?他們和南朝人物有相同處,也有相異處。同者,在於他們都是南方山水所餵養出來的神仙般的雋秀人物,都悄悄的或公然的從儒家出走而稍近釋老(當然,走入基督教或new age的也有)。他們言談詼諧,時發俊語,為人簡慢,偶而有些小小使壞的地方,如孩童。 至於說到相異,兩者有其更多不同處。第一,台北風流人物是滿世界遊走的,即使人在台北,滿心想的卻是下一次的出發。像林懷民,心中早已默認(不,其實不是默認,是公開承認)印度或峇里島是他的某種故鄉,是心靈可以依歸之處。所以台北風流人物是絕不可能因懷念故國而新亭對泣的。 台北風流人物的第二特點是漂亮,這漂亮包括面目的個性化,神采的俊秀,衣著的得體(即使是你看似邋遢的一件舊衣,其實也自有其道理),行止之間的雍容,進退之間的大度。六朝人物其實也多半是漂亮的,但卻偶然有些寢陋的。台北人物不同,他們個個漂亮、年輕,充滿活力(也許等回家以後會累得癱死),換言之,他們可以隨時上電視,供眾人瞻仰丰采。 第三,談到上電視,其實台北風流人物也隨時可以上電台,上座談會,上演講廳,五○、六○年代,台北尚有四大名嘴、四小名嘴之說,但到了七○、八○年代凡稱得上是個人物的,幾乎到了「無嘴不名」的程度。換言之,個個皆名嘴。就算是發音不正,文法倒錯,也說得活靈活現自創風格自成路數。 第四,台北風流人物不一定要有車(因為停車太難),但一定要有一棟小小雅宅。雅宅中還要有幾瓶小酒,「五糧液」、「酒鬼」、「月桂冠」、「威士忌」或「紅酒」、「啤酒」都不拘,但求能在高朋滿座之際能助談興。當年夏濟安先生就曾在日記中提到自己衣食都可不講究,但求居所能雅潔。試想沒有小小雅室,何以交結天下名士?如何能擊壺縱談,如何能長歌當哭。可歎夏先生大約是一生沒能實踐這願望(等到他有經濟能力的時候,他又不幸早逝),台北風流人物多半手頭稍有「阿堵物」,可以略略在居住上花些錢。台北居,大不易,對大環境,誰也不能掌控(例如你家樓下忽然開了麥當勞),但雅緻樸素的室內設計自可給人一方小天地,有了室內設計,人就可以「隱」了,隱於瑪雅、隱於排灣,或隱於宋元,只需要幾件收藏品,就可以進入幻境,也就可以自保。 第五,台北風流人物大體言之都是好人,但他們卻避「好人之名」如避仇。余光中先生某次在婚禮上曾調侃某人既不是「偽君子」,也不是「真小人」,而是「偽小人」。偽小人約略等於俗語中的「剪刀嘴巴豆腐心」或「面惡心善」之類的定義。魯迅當年曾以「正人君子」作為罵人之詞,攻擊他的對手陳西瀅到死而後已。可見得「正人君子」在某些人心目中幾乎是個可怕乃至可恥的字眼。故身為台北風流人物必須有些小奸小壞相,至少至少也要有些頑童的刁蠻。總之千萬不能成為「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方正木訥且又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但私底他卻可能是個隱藏的道德家,也許悄悄支持某藝術家的創作,也許月付某印度小孩的學費若干,也許勤於探視父母,也許把整個假日拿去陪某個殘障小孩…… 第六,台北風流人物要有些特立獨行之處,或愛收藏玉,或愛收藏老唱片,或收藏普洱老茶,或愛使性罵人(或罵阿扁,或罵阿輝,或罵宗才怡皆無不可),或善製格言供人傳誦,或考究美食,懂得如何調理義大利烏賊麵或加州風的壽司,或迷上法國礦泉水沛綠雅,或只肯吃某個牌子的魚子醬,或沉淪於某種巧克力,不肯自拔。或天涯浪跡,尋找一台好看好聽的鋼琴如我早逝的朋友徐世棠…… 總之生命苦短,台北風流人物各有其和歲月相搏的招數。半盞干邑紅酒,可以令人贏命運一目。斂容寂坐,可勝對手一城。奮袂狂歌,便可以睥睨歲月一眼…… 台北是個盆地,既無漁鹽之利,也無農牧資源,此外礦產山產一概闕如。百年千年之後如果有人考察當年台北的出產,算來只有一種,那便是:人物。 在華人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座城,其市民受到如此高的教育,收入如此之豐,與全世界互通聲氣如此方便,人文薈粹的密度是如此之高……毛澤東雖曾寫過: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的詞句,但他和他的從屬都是莽夫,都只有戾氣,而沒有逸氣,離風流人物有十萬八千里之遙。真正數風流人物,當然要看台北,大陸大山大水,當然也會產人物,但,抱歉,因為他們有好一陣子太忙了,忙於文爭武鬥,要談人物,那是八○年以後的事了。 以上花極大的篇幅來談台北人物,其實無非要說明一點,那就是:台北是個濟濟多士的城,蒙上天垂憐,我們享受了比貞觀之治、比開元天寶更漫長的一段承平歲月,也因而哺育了一批精神上的膏粱子弟(這四個字古人用來是有貶義的,我則有褒義)。從前,陳獨秀怒沖沖的要打倒貴族文學,其實,如果有辦法讓人人都很貴族,日子不是很好過嗎?幹嘛要把貴族拉下馬來做平民?把平民抬上轎去做貴族不是更好嗎?台北其實就是一座華美的貴族城池,其間充滿一些比周郎更俊賞,比太白更恣縱,比玉谿更纏綿的風流文人。而在眾多風流人物中,套句台灣土話,蔣勳當然算「一條大尾的」。
縱與橫 以上花了極大篇幅所說明的,其實歸納言之只有兩點: 第一,蔣勳多年來在文學和美學上的耕耘,就時間的縱軸而言,他可算為人類文化的孝友之子(對,不僅僅是老中的文化,對希臘,對美索不達米亞亦然),他是一個恭謹謙遜的善述者。 第二,就空間上的橫軸而言,蔣勳是這個地域的詩酒風流的產物,是從容、雍雅、慧黠、自適的人。 所以說,蔣勳是多元的。如果你在他的作品裡讀到他記錄母親講的故事,說王寶釧當年因為吃太多野菜,結果弄出一個綠肚皮來。你不要先笑,這是他的庶民成分。 而下面這段文字則不免令人驚豔,那是蔣勳談石頭的說詞:
洪荒形成的時候,最早找到形狀的大概是石頭罷。 我們不太會記得石頭也有熔點,在極高溫下也會融化成液體。 一團噴薄的熔岩,赤紅、高熱。它竟不是我們日常理解的石頭的樣子。它在火光中燃燒,高度的熱,使石頭內在的分子解體。分子與分子激盪相撞,巨大的岩塊噴薄分離成蕈雲般的火焰。 那是最初的石頭。 據說,女媧是用石頭煉燒來補天的。只有在中國,古老的神話便知道石頭可以是一種液體。 石頭是一種液體,它飛濺、流蕩、迂迴;到處是石頭的河流,圍繞著蒸騰鬱熱的火焰,緩緩流著、流著。 那被稱為洪荒的時代,是因為一切都尚未命名,一切都還沒有形狀。 宇宙的生殖是在高熱中完成的,石頭便是最初的子嗣。在高熱中旋轉、飛濺、激盪、暈眩,這最初的子嗣久久不願意固定自己的形狀。 當噴薄的雲霧逐漸沉澱為地上的塵埃,洪荒要擘開天地,混沌中分出了光明;當高熱退去,大地變得涼冷,「呀──」在那巨大的嘶叫中,活躍的、奔騰的、散放著生命的光與熱的熔岩,瀕於死亡的時刻,在迸濺著淚水的嘯叫中,他們一一立起固定成了永恆的山脈。 被我們稱為「石頭」的,其實已是石頭的骸骨。它們活著的時候是沒有形狀的。 我們在山脈起伏中還看得見石頭在熔岩時代奔騰洶湧的氣勢。我們細看石頭的紋理,也還看見水波流走的痕跡。 石頭這樣堅硬、固定、冰冷,我們常常在手中把玩一塊石頭。其實,石頭如水般流動,沒有形狀,而且燃燒著高熱。 偶然石頭與石頭相撞,迸閃出火花,我們才知道,原來石頭中還是藏著火的。 人們曾經用兩塊石頭相互擊打蒐取火種。 但是,石頭火焰的部分是不太願意讓人知道的。 熔岩死亡之後,石頭復活了另一種形式的生命。從活躍、熱烈、灼燙、燦爛,變成靜定、沉重、冰冷而且甘願於晦暗。
至於寫平劇〈四郎探母〉的那一段,也令人痛徹肝腸,他這樣寫著:
其實真正教會我看懂〈四郎探母〉這齣戲的,不只是母親,而是服兵役時認識的一些軍中的老士官們。服兵役的時候在鳳山,擔任陸軍官校的歷史教官,從小在台北長大,第一次離開家,第一次接觸到和我的成長背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群人。 ………… 走到校園裡,碰到一些老士官,他們站起來,「少尉好!」他們必恭必敬向我敬禮,他們的年紀比我大很多,臉上蒼老黧黑,我覺得有些不安,和他們一起坐下來,忽然聽到他們身邊的收音機唱著一句:「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我心中一驚,面前這面目蒼老黧黑,一生顛沛流離的老士官,他的故事,彷彿就是楊四郎的故事,是戰爭中千千萬萬與親人隔離的悲哀與傷痛,不可言說的心事,都化在一齣「探母」的戲劇中。 我開始注意鳳山黃埔軍校的校園中,或者整個黃埔新村的眷村中,總是聽到〈四郎探母〉,總是聽到一個孤獨蒼老的聲音,在某個角落裡沙啞地哼著:「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 我在整理黃埔軍校的校史的同時,開始和這些在各個角落聽〈四郎探母〉的老兵們做朋友,聽他們的故事。 一個叫楊天玉的老兵,山東人,民國三十八年,在山東鄉下,連年兵災人禍,家裡已經沒飯吃了。他的母親打了一捆柴,要天玉扛著到青島城裡去賣,那一年他十六歲。扛著柴走了幾天,走到青島,正巧碰到國民黨軍隊撤退,他說:「糊裡糊塗就跟軍隊到了台灣。」 我算了一下,他跟我說故事的那一年是民國五十八年,距離他被抓兵,離開家鄉,已經整整二十年。 他說:「楊四郎十五年沒有見到母親,我娘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是到哪裡去了。」 另外一位姓張的老兵,四川人,第一次認識他,我看他的名字,他笑了說:「少尉,名字不重要。」我不懂他的意思,他也說:「不重要,不重要。」後來熟了,才知道他兵籍號碼牌上的名字也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他說:「打仗啊,到處亂抓兵,軍隊都有一本兵籍簿,按著兵籍簿的名字發餉發糧發衣服彈藥,要是有一個兵逃跑了,就抓另外一個人來頂替。」這個姓張的四川人,逃了很多次兵,又被抓去做另一個逃兵的頂替者,他於是養成一種玩世不恭的調皮,總是說:「名字啊,不重要,不重要,楊四郎,楊延輝,不是也改了名,叫木易嗎?」 是的,許多有關〈四郎探母〉的細節,我是透過這些在戰亂中活下來的老兵讀懂了的,知道了為什麼這齣戲可以歷經百年不衰,在人們口中一再流傳。
喜 捨 當然,例子如果要舉下去,讀者還可以繼續被搥擊被感動,但我要說的是,智慧和深思其實是最大最好的施捨。 曾經,在古老的年代: 有人施粥,以救人之飢。 有人施藥,以癒人之病。 有人施衣,以暖人之軀, 也有人施材,以送人之終。 但第一流的施捨其實是「智慧」的施捨。 智慧的分享和心靈的均富,是施捨者的最終極的嚮往。佛家稱「喜捨」,指的便是怡然欣悅的施予。這種貽贈,在受者,是天恩,在施者,也是天惠,因為彷如懸絲瀑布,垂瀉而下,來自有其來處,去自有其去處,人世美景,其實無非由於活水源頭加上流行布施。 善述和喜捨,以上是我所知道的蔣勳。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蔣勳精選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現代散文 |
$ 300 |
散文 |
$ 300 |
文學作品 |
$ 334 |
中文書 |
$ 342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蔣勳精選集
★ 作家張曉風專文推薦
★ 收錄蔣勳精彩的散文作品
蔣勳善於把低眉垂睫的美喚醒,讓我們看見精燦灼人的明眸。善於把沉啞瘖滅的美喚醒,讓我們聽到恍如鶯啼翠柳的華麗歌聲。蔣勳多年在文學和美學上的耕耘,就時間的縱軸而言,他可算為人類文化的孝友之子,他是一個恭謹謙遜的善述者。就空間上的橫軸而言,蔣勳是這個地域的詩酒風流的產物,是從容、雍雅、慧黠、自適的人。
──張曉風
蔣勳,不論在畫作上、詩作上以及藝術上都有相當傲人的成就,而他在散文的創作上,字字雋永,令人回味無窮。《蔣勳精選集》是將蔣勳的散文作品中,精選出許多動人的作品,這些作品除了耳熟能詳外,更是代表蔣勳的散文創作中的痕跡。散文名家張曉風特為文導讀,讓您更能進入蔣勳的散文世界,認識不一樣的蔣勳。
作者簡介:
蔣勳
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學系畢業,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畢業,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研究,一九八一年受邀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訪問。曾任雄獅美術主編、東海大學美術系創系系主任七年,現專事寫作並重事藝術美學研究工作。
十五歲進高中便學習新詩、小說創作,寫作文類包括詩、散文、評論,由以詩和散文最具個人風格,由於從事藝術工作多年,使其作品處處顯露豐富的視覺意象,彷彿以文字代替線條,透過藝術組合而產生美感。
章節試閱
推薦序
善述與喜捨 張曉風
善述是什麼意思 「善述」這兩個字,如果翻譯出來,就是「善於敘述」的意思,但善於敘述又是什麼意思呢?由於這是我統括蔣勳平生的字眼,所以有必要解釋一下。 善述,如果從文法觀念來看,算是個「述語」。有趣的是,句子中的主詞和受詞卻都省略了,為什麼省略呢?因為,好像沒有必要去說。因為,反正人人明白。 原來,善述,一般都指為人子者,善述其父,(當然,如果你要說成子女善述父母,也請便,但那並非古人的意思)《禮記.中庸篇》裡有: 父作之 子述之
的句子,換言之,在儒家思想體系中,所謂...
善述與喜捨 張曉風
善述是什麼意思 「善述」這兩個字,如果翻譯出來,就是「善於敘述」的意思,但善於敘述又是什麼意思呢?由於這是我統括蔣勳平生的字眼,所以有必要解釋一下。 善述,如果從文法觀念來看,算是個「述語」。有趣的是,句子中的主詞和受詞卻都省略了,為什麼省略呢?因為,好像沒有必要去說。因為,反正人人明白。 原來,善述,一般都指為人子者,善述其父,(當然,如果你要說成子女善述父母,也請便,但那並非古人的意思)《禮記.中庸篇》裡有: 父作之 子述之
的句子,換言之,在儒家思想體系中,所謂...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編輯前言.推薦蔣勳/陳義芝 善述與喜捨/張曉風 蔣勳散文觀 輯一 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 別時容易 淡水河隨想 自私的放肆的愛 石頭記 輯二 大度‧山 無關歲月 春鶯囀 空城計 寒食帖 辭歲之鐘 山 盟 輯三 歡喜讚歎 「人」的電影主題 輯四 今宵酒醒何處 屋漏痕 大 學 美是歷史的加法 芭樂樹始末 輯五 夕陽無語 寒窯上的鐵鏟 夕陽無語 輯六 人與地 靜浦婦人 蘭亭與洗衣婦人 花的島嶼 佛在恆河 阿西西的芳濟灱 阿西西的芳濟牞 天籟唱讚 分享神的福分 輯七 島嶼獨白 獨 白 飆 颱 風 秋 水 島嶼南端 領 域 宿 命 蓮 花 夏之輓...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