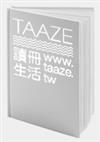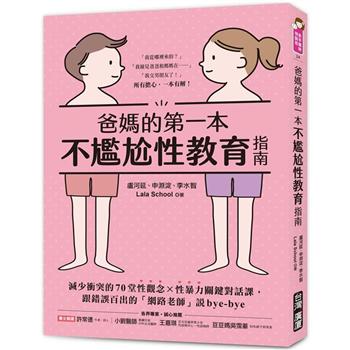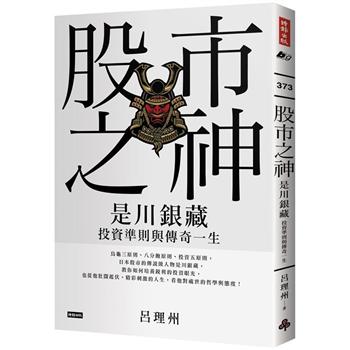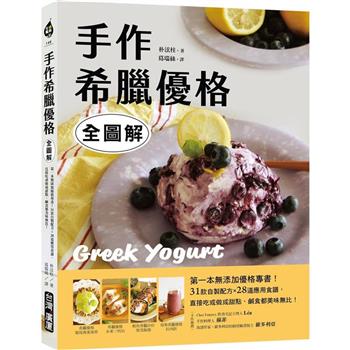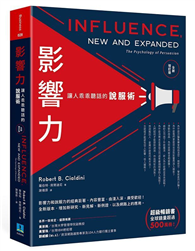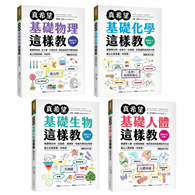梁氏散文所以動人,首先是機智閃爍,諧趣迭生,時或滑稽突梯,卻能適可而止,不墮俗趣。他的筆鋒有如貓爪戲人而不傷人,即使譏諷,針對的也是眾生的共相,而非私人,所以自有一種溫柔的美感距離。——名詩人余光中
梁先生對文學的執著以及在人與事中的進退,在在都給年輕輩如我樹立了一種風範和鼓勵。──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
梁實秋嘗與友人說:「寫雅舍小品時唯恐不傷人,寫雅舍散文時卻唯恐傷了人。」前期小品文藉譏諷批評的語調,呈現幽默的趣味,晚年心境趨於閒適超脫,筆觸也較樸實內斂。本書堪稱一代文學大師完美的天鵝之歌,匯集他晚期最精采的作品,展現出他學養深厚,談古論今,風趣睿智而不尖酸刻薄;運筆恢弘,書寫日常,卻從紙頁透出儒雅智慧。
「談吃」不直接談舌尖上的滋味,反從字裡行間流露出的食物典故與懷鄉情懷,讓我們感受到飲食、人情和故鄉味道的美好。他賞析中西方文學名著、書評藝術風華,從莎士比亞到《醒世姻緣傳》,其讀書樂趣和鑑賞功力,在「談書」中表露無遺。
「人性觀察」與「人生感觸」是作者創作的主軸,他常以細膩的情思、諧趣的文字,從不起眼的人事物中挖掘豐富的意涵,勾勒世間百態。所以讀雅舍可以體會到生活處處是風景,更讓人感悟經典不僅是經典,原來也可以這麼有趣!
本書特色
★ 文學大師梁實秋的散文作品,熔情趣、學問與智慧於一爐,被譽為「學者散文的代表」。
★ 特增文章一篇從不同角度認識梁實秋這位大師。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梁實秋雅舍文選(增訂新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4 |
中文書 |
$ 284 |
現代散文 |
$ 284 |
散文 |
$ 284 |
文學作品 |
$ 284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梁實秋雅舍文選(增訂新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梁實秋(1903-1987)
民前十年生。曾在南北數大學執教,六十五歲退休,「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馳騁於文壇五十多年,曾專業寫作。其文筆雋永,字裡行間感情洋溢。
他以三十年的功力完成《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在翻譯界是空前的盛舉。除了對文學翻譯貢獻良多外,他的散文自成一格,為許多人所喜愛,獨樹一幟的《雅舍小品》小品文風格,被公認為現代文學的典範,為當代知性小品散文的開山祖師,亦是人人敬仰的文學大師。
著有《雅舍小品》、《雅舍散文》、《雅舍談吃》等十餘種;譯有《莎士比亞全集》、《潘彼得》、《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等。時人為紀念他對散文及翻譯的貢獻,陸續舉辦梁實秋文學獎已歷二十七屆。
梁實秋(1903-1987)
民前十年生。曾在南北數大學執教,六十五歲退休,「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馳騁於文壇五十多年,曾專業寫作。其文筆雋永,字裡行間感情洋溢。
他以三十年的功力完成《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在翻譯界是空前的盛舉。除了對文學翻譯貢獻良多外,他的散文自成一格,為許多人所喜愛,獨樹一幟的《雅舍小品》小品文風格,被公認為現代文學的典範,為當代知性小品散文的開山祖師,亦是人人敬仰的文學大師。
著有《雅舍小品》、《雅舍散文》、《雅舍談吃》等十餘種;譯有《莎士比亞全集》、《潘彼得》、《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等。時人為紀念他對散文及翻譯的貢獻,陸續舉辦梁實秋文學獎已歷二十七屆。
目錄
〔導讀〕
文章與前額並高 余光中
輯一 雅舍散文
廣告
麻將
火車
文房四寶
東安市場
賽珍珠與徐志摩
時間即生命
日記
與莎翁絕交之後
二手菸
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
信用卡
紐約的舊書鋪
說胖
說酒
吃醋
小賬
推銷術
房東與房客
略談莎士比亞作品裡的鬼
白貓王子
為什麼不說實話?
流行的謬論
輯二 雅舍談吃
西施舌
火腿
燒鴨
燒羊肉
獅子頭
核桃酪
酸梅湯與糖葫蘆
芙蓉雞片
韭菜簍
佛跳牆
滿漢細點
爆雙脆
薄餅
粥
餃子
豆腐
鍋巴
〔附錄〕
談《雅舍談吃》梁文薔
輯三雅舍談書
影響我的幾本書
漫談翻譯
讀《醒世姻緣傳》
關於莎士比亞
我是怎麼開始寫文學評論的?
漫談《英國文學史》
《雅舍小品》合訂本後記
人生就是一個長久誘惑
《潘彼得》新版後記
〔特載〕
海內外學者談梁實秋
〔附錄〕
梁實秋先生年表
每一筆都是最完美 陳素芳
文章與前額並高 余光中
輯一 雅舍散文
廣告
麻將
火車
文房四寶
東安市場
賽珍珠與徐志摩
時間即生命
日記
與莎翁絕交之後
二手菸
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
信用卡
紐約的舊書鋪
說胖
說酒
吃醋
小賬
推銷術
房東與房客
略談莎士比亞作品裡的鬼
白貓王子
為什麼不說實話?
流行的謬論
輯二 雅舍談吃
西施舌
火腿
燒鴨
燒羊肉
獅子頭
核桃酪
酸梅湯與糖葫蘆
芙蓉雞片
韭菜簍
佛跳牆
滿漢細點
爆雙脆
薄餅
粥
餃子
豆腐
鍋巴
〔附錄〕
談《雅舍談吃》梁文薔
輯三雅舍談書
影響我的幾本書
漫談翻譯
讀《醒世姻緣傳》
關於莎士比亞
我是怎麼開始寫文學評論的?
漫談《英國文學史》
《雅舍小品》合訂本後記
人生就是一個長久誘惑
《潘彼得》新版後記
〔特載〕
海內外學者談梁實秋
〔附錄〕
梁實秋先生年表
每一筆都是最完美 陳素芳
序
導讀
文章與前額並高 余光中
自從十三年前遷居香港以來,和梁實秋先生就很少見面了。屈指可數的幾次,都是在頒獎的場合,最近的一次,卻是從梁先生溫厚的掌中接受時報文學的推薦獎。這一幕頗有象徵的意義,因為我這一生的努力,無論是在文壇或學府,要是當初沒有這隻手的提掖,只怕難有今天。
所謂「當初」,已經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時我剛從廈門大學轉學來台,在台大讀外文系三年級,同班同學蔡紹班把我的一疊詩稿拿去給梁先生評閱。不久他竟轉來梁先生的一封信,對我的習作鼓勵有加,卻指出師承囿於浪漫主義,不妨拓寬視野,多讀一點現代詩,例如哈代、浩斯曼、葉慈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摯友徐志摩雖然是浪漫詩人,他自己的文學思想卻深受哈佛老師白璧德之教,主張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中所說的「現代」自然還未及現代主義,卻也指點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則我在雪萊的西風裡還會飄泊得更久。
直到今日我還記得,梁先生的這封信是用鋼筆寫在八行紙上,字大而圓,遇到英文人名,則橫而書之,滿滿地寫足兩張。文藝青年捧在手裡,驚喜自不待言。過了幾天,在紹班的安排之下,我隨他去德惠街一號梁先生的寓所登門拜訪。德惠街在城北,與中山北路三段橫交,至則巷靜人稀,梁寓雅潔清幽,正是當時常見的日式獨棟平房。梁師母引我們在小客廳坐定後,心儀已久的梁實秋很快就出現了。
那時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風大雨,在大陸上已見過了,避秦也好,乘桴浮海也好,早已進入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他的談吐,風趣中不失仁譪,諧謔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國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機智,近於他散文的風格。他就坐在那裡,悠閒而從容地和我們談笑。我一面應對,一面仔細地打量主人。眼前這位文章鉅公,用英文來說,體型「在胖的那一邊」,予人厚重之感。由於髮岸線(hairline)有早退之象,他的前額顯得十分寬坦,整個面相不愧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加以長牙隆準,看來很是雍容。這一切,加上他白皙無斑的膚色,給我的印象頗為特殊。後來我在反省之餘,才斷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頭白象。
當時我才二十三歲,十足一個躁進的文藝青年,並不很懂觀象,卻頗熱中獵獅(lion-hunting)。這位文苑之獅,學府之師,被我糾纏不過,答應為我的第一本詩集寫序。序言寫好,原來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詩,屬於新月風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進青年,竟然把詩拿回去,對梁先生抱怨說:「您的詩,似乎沒有特別針對我的集子而寫。」
假設當日的寫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獅子一聲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師門去了。但是梁先生眉頭一抬,只淡淡地一笑,徐徐說道:「那就別用得了……書出之後,再跟你寫評吧。」
量大而重諾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後不久,果然為我寫了一篇書評,文長一千多字,刊於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的《自由中國》。那本詩集分為兩輯,上輯的主題不一,下輯則盡為情詩;書評認為上輯優於下輯,跟評者反浪漫的主張也許有關。梁先生尤其欣賞〈老牛〉與〈暴風雨〉等幾首,他甚至這麼說:「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風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風雨的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都描寫出來了,真可說是筆挾風雷。」在書評的結論裡有這樣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輕人,他的藝術並不年輕,短短的「後記」透露出一點點寫作的經過。他有舊詩的根柢,然後得到英詩的啟發。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條發展路線。我們寫新詩,用的是中國文字,舊詩的技巧是一分必不可少的文學遺產,同時新詩是一個突然生出的東西,無依無靠,沒有軌跡可循,外國詩正是一個最好的借鏡。
在那麼古早的歲月,我的青澀詩藝,根柢之淺,啟發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詞固然是出於鼓勵,但他所提示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卻是我日後遵循的綜合路線。
朝拜繆思的長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輩如此的獎掖,使我的信心大為堅定。同時,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結識了不少像陳之藩、何欣這樣同輩的朋友,聲應氣求,更鼓動了創作的豪情壯志。詩人夏菁也就這麼邂逅於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們就慣於一同去訪梁公,有時也約王敬羲同行。不知為何,記憶裡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頻。梁先生怕熱,想是體胖的關係;有時他索性只穿短袖的汗衫接見我們,一面笑談,一面還是不時揮扇。我總覺得,梁先生雖然出身外文,氣質卻在儒道之間,進可為儒,退可為道。可以想見,好不容易把我們這些恭謹的晚輩打發走了之後,東窗也好,東床也罷,他是如何地坦腹自放。我說坦腹,因為他那時有點發福,腰圍可觀,縱然不到福爾斯塔夫的規模,也總有約翰孫或紀曉嵐的分量,足證果然腹笥深廣。據說,因此梁先生買腰帶總嫌尺碼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只大號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是否謠言,卻未向梁先生當面求證。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門子,總有點心招待,想必是師母的手藝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兩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只知他下筆論起珍羞名菜來,頭頭是道。就連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動,饞腸若蠕。在糖尿病發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實也飫足了。有時乘興,他也會請我們淺酌一杯。我若推說不解飲酒,他就會作態佯怒,說什麼「不菸不酒,所為何來?」引得我和夏菁發笑。有一次,他斟了白蘭地饗客,夏菁勉強相陪。我那時真是不行,梁先生說「有了」,便向櫥頂取來一瓶法國紅葡萄酒,強調那是一八四二年產,朋友所贈。我總算喝了半盅,飄飄然回到家裡,寫下〈飲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讀而樂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國》上,一時引人矚目。其實這首詩學濟慈而不類,空餘浪漫的遐想;換了我中年來寫,自然會聯想到鴉片戰爭。
梁先生在台北搬過好幾次家。我印象最深的兩處梁宅,一在雲和街,一在安東街。我初入師大(那時還是省立師範學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將滿,又偕夏菁去雲和街看梁先生。談笑及半,他忽然問我:「送你去美國讀一趟書,你去嗎?」那年我已三十,一半書呆,一半詩迷,幾乎尚未閱世,更不論乘飛機出國。對此一問,我真是驚多喜少。回家和我存討論,她是驚少而喜多,馬上說:「當然去!」這一來,裡應外合勢成。加上社會壓力日增,父親在晚餐桌上總是有意無意地報導:「某伯伯家的老三也出國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經不久。果然三個月後,我便文化充軍,去了秋色滿地的愛奧華城。
從美國回來,我便專任師大講師。這時他已從雲和街故居遷至安東街,住進自己蓋的新屋。稍後夏菁的新居在安東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羨慕的梁府近鄰,也從此,我去安東街,便成了福有雙至,一舉兩得。安東街的梁宅,屋舍儼整,客廳尤其寬敞舒適,屋前有一片頗大的院子,花木修護得可稱多姿,常見兩老在花畦樹徑之間流連。比起德惠街與雲和街的舊屋,這新居自然優越了許多,更不提廣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可以感受得到,這新居的主人住在「家外之家」,懷鄉之餘,該是何等的快慰。
六十五歲那年,梁先生在師大提前退休,歡送的場面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終身大事」,《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之中譯完成,朝野大設酒會慶祝盛舉,並有一女中的學生列隊頌歌:想莎翁生前也沒有這般殊榮。師大英語系的晚輩同事也設席祝賀,並贈他一座銀盾,上面刻著我擬的兩句讚詞:「文豪述詩豪,梁翁傳莎翁。」莎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歲,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歲,其實還不能算翁。同時莎翁生前只出版了十八個劇本,梁翁卻能把三十七本莎劇全部中譯成書。對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聽了我這意見,梁翁不禁莞爾。
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夏菁擔任聯合國農業專家,遠去了牙買加。梁先生一度旅寄西雅圖。我自己先則旅美二年,繼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後才回台灣。高雄與台北之間雖然只是四小時的車程,畢竟不比廈門街到安東街那麼方便了。青年時代夜訪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為溫馨的回憶,只能在深心重溫,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實不僅梁先生,就連晚他一輩的許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見日稀。四小時的車程就可以回到台北,卻無法回到我的台北時代。台北,已變成我的回聲谷。那許多巷弄,每轉一個彎,都會看見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與回聲谷裡。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鄉情怯,怕捲入回聲谷裡那千重魔幻的漩渦。
在香港結交的舊友之中,有一人焉,竟能逆流而入那回聲的漩渦,就是梁錫華。他是徐志摩專家,研究兼及聞一多,又是抒情與雜感兼擅的散文家,就憑這幾點,已經可以躋列梁門,何況他對梁先生更已敬仰有素。一九八○年七月,法國人在巴黎舉辦抗戰文學研討會,大陸的代表舊案重提,再誣梁實秋反對抗戰文學。梁錫華即席澄清史實,一士諤諤,力辯其誣。夏志清一語雙關,對錫華翹起大拇指,讚他「小梁挑大樑」!我如在場,這件事義不容辭,應該由我來做。錫華見義勇為,更難得事先覆按過資料,不但贏得梁先生的感激,也使我這受業弟子深深感動。
一九七八年以後,大陸的文藝一度曾有開放之象。到我前年由港返台為止,甚至新月派的主角如胡適、徐志摩等的作品都有新編選集問世,唯獨梁實秋迄今尚未「平反」。如今大陸上又在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此事恐怕更渺茫了。梁先生和魯迅論戰於先,又遭毛澤東親批於後,案情重大,實在難以為他「平反」。梁實秋就是梁實秋,這三個字在文學思想上代表一種堅定的立場和價值,已有近六十年的歷史。
梁實秋的文學思想強調古典的紀律,反對浪漫的放縱。他認為革命文學也好,普羅文學也好,都只是把文學當做工具,眼中並無文學;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贊成為藝術而藝術,因為那樣勢必把藝術抽離人生。簡而言之,他認為文學既非宣傳,亦非遊戲。他始終標舉安諾德所說的,作家應該「沉靜地觀察人生,並觀察其全貌。」因此他認為文學描寫的充分對象是人生,而不僅是階級性。
黎明版《梁實秋自選集》的小傳,說作者「生平無所好,唯好交友、好讀書、好議論。」這三好之中的末項,在大陸時代表現得最為出色,所以才會招惹魯迅而陷入重圍。季季在訪問梁先生的記錄「古典頭腦,浪漫心腸」之中,把他的文學活動分成翻譯、散文、編字典、編教科書四種。這當然是梁先生的台灣時代給人的印象。其實梁先生在大陸時代的筆耕,以量而言,最多產的是批評和翻譯,至於《雅舍小品》,已經是三十九歲所作,而在台灣出版的了。《梁實秋自選集》分為文學理論與散文二輯,前輯占一九八頁,後輯占一六二頁,分量約為五比四,也可見梁先生對自己批評文章的強調。他在答季季問時說:「我好議論,但是自從抗戰軍興,無意再作任何譏評。」足證批評是梁先生早歲的經營,難怪台灣的讀者印象已淡。
一提起梁實秋的貢獻,無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譯績,這方面的聲名幾乎掩蓋了他別的譯書。其實翻譯家梁實秋的成就,除了莎翁全集,尚有《織工馬南傳》、《咆哮山莊》、《百獸圖》、《西塞羅文錄》等十三種。就算他一本莎劇也未譯過,翻譯家之名他仍當之無愧。
讀者最多的當然是他的散文。《雅舍小品》初版於民國三十八年,到六十四年為止,二十六年間已經銷了三十二版;到現在想必近五十版了。我認為梁氏散文所以動人,大致是因為具備下列這幾種特色:
首先是機智閃爍,諧趣迭生,時或滑稽突梯,卻能適可而止,不墮俗趣。他的筆鋒有如貓爪戲人而不傷人,即使譏諷,針對的也是眾生的共相,而非私人,所以自有一種溫柔的美感距離。其次是篇幅濃縮,不事鋪張,而轉折靈動,情思之起伏往往點到為止。此種筆法有點像畫上的留白,讓讀者自己去補足空間。梁先生深信「簡短乃機智之靈魂」,並且主張「文章要深,要遠,就是不要長。」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證,而中外逢源,古今無阻。這引經據典並不容易,不但要避免出處太過俗濫,顯得腹笥寒酸,而且引文要來得自然,安得妥貼,與本文相得益彰,正是學者散文的所長。
最後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贅,他出身外文,卻寫得一手道地的中文。一般作家下筆,往往在白話、文言、西化之間徘徊歧路而莫知取捨,或因簡而就陋,一白到底,一西不回;或弄巧而成拙,至於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梁氏筆法一開始就逐走了西化,留下了文言。他認為文言並未死去,反之,要寫好白話文,一定得讀通文言文。他的散文裡使用文言的成分頗高,但不是任其並列,而是加以調和。也自稱文白夾雜,其實應該是文白融會。梁先生的散文在中歲的《雅舍小品》裡已經形成了簡潔而圓融的風格,這風格在台灣時代仍大致不變。證之近作,他的水準始終在那裡,像他的前額一樣高超。
文章與前額並高 余光中
自從十三年前遷居香港以來,和梁實秋先生就很少見面了。屈指可數的幾次,都是在頒獎的場合,最近的一次,卻是從梁先生溫厚的掌中接受時報文學的推薦獎。這一幕頗有象徵的意義,因為我這一生的努力,無論是在文壇或學府,要是當初沒有這隻手的提掖,只怕難有今天。
所謂「當初」,已經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時我剛從廈門大學轉學來台,在台大讀外文系三年級,同班同學蔡紹班把我的一疊詩稿拿去給梁先生評閱。不久他竟轉來梁先生的一封信,對我的習作鼓勵有加,卻指出師承囿於浪漫主義,不妨拓寬視野,多讀一點現代詩,例如哈代、浩斯曼、葉慈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摯友徐志摩雖然是浪漫詩人,他自己的文學思想卻深受哈佛老師白璧德之教,主張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中所說的「現代」自然還未及現代主義,卻也指點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則我在雪萊的西風裡還會飄泊得更久。
直到今日我還記得,梁先生的這封信是用鋼筆寫在八行紙上,字大而圓,遇到英文人名,則橫而書之,滿滿地寫足兩張。文藝青年捧在手裡,驚喜自不待言。過了幾天,在紹班的安排之下,我隨他去德惠街一號梁先生的寓所登門拜訪。德惠街在城北,與中山北路三段橫交,至則巷靜人稀,梁寓雅潔清幽,正是當時常見的日式獨棟平房。梁師母引我們在小客廳坐定後,心儀已久的梁實秋很快就出現了。
那時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風大雨,在大陸上已見過了,避秦也好,乘桴浮海也好,早已進入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他的談吐,風趣中不失仁譪,諧謔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國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機智,近於他散文的風格。他就坐在那裡,悠閒而從容地和我們談笑。我一面應對,一面仔細地打量主人。眼前這位文章鉅公,用英文來說,體型「在胖的那一邊」,予人厚重之感。由於髮岸線(hairline)有早退之象,他的前額顯得十分寬坦,整個面相不愧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加以長牙隆準,看來很是雍容。這一切,加上他白皙無斑的膚色,給我的印象頗為特殊。後來我在反省之餘,才斷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頭白象。
當時我才二十三歲,十足一個躁進的文藝青年,並不很懂觀象,卻頗熱中獵獅(lion-hunting)。這位文苑之獅,學府之師,被我糾纏不過,答應為我的第一本詩集寫序。序言寫好,原來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詩,屬於新月風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進青年,竟然把詩拿回去,對梁先生抱怨說:「您的詩,似乎沒有特別針對我的集子而寫。」
假設當日的寫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獅子一聲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師門去了。但是梁先生眉頭一抬,只淡淡地一笑,徐徐說道:「那就別用得了……書出之後,再跟你寫評吧。」
量大而重諾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後不久,果然為我寫了一篇書評,文長一千多字,刊於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的《自由中國》。那本詩集分為兩輯,上輯的主題不一,下輯則盡為情詩;書評認為上輯優於下輯,跟評者反浪漫的主張也許有關。梁先生尤其欣賞〈老牛〉與〈暴風雨〉等幾首,他甚至這麼說:「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風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風雨的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都描寫出來了,真可說是筆挾風雷。」在書評的結論裡有這樣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輕人,他的藝術並不年輕,短短的「後記」透露出一點點寫作的經過。他有舊詩的根柢,然後得到英詩的啟發。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條發展路線。我們寫新詩,用的是中國文字,舊詩的技巧是一分必不可少的文學遺產,同時新詩是一個突然生出的東西,無依無靠,沒有軌跡可循,外國詩正是一個最好的借鏡。
在那麼古早的歲月,我的青澀詩藝,根柢之淺,啟發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詞固然是出於鼓勵,但他所提示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卻是我日後遵循的綜合路線。
朝拜繆思的長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輩如此的獎掖,使我的信心大為堅定。同時,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結識了不少像陳之藩、何欣這樣同輩的朋友,聲應氣求,更鼓動了創作的豪情壯志。詩人夏菁也就這麼邂逅於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們就慣於一同去訪梁公,有時也約王敬羲同行。不知為何,記憶裡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頻。梁先生怕熱,想是體胖的關係;有時他索性只穿短袖的汗衫接見我們,一面笑談,一面還是不時揮扇。我總覺得,梁先生雖然出身外文,氣質卻在儒道之間,進可為儒,退可為道。可以想見,好不容易把我們這些恭謹的晚輩打發走了之後,東窗也好,東床也罷,他是如何地坦腹自放。我說坦腹,因為他那時有點發福,腰圍可觀,縱然不到福爾斯塔夫的規模,也總有約翰孫或紀曉嵐的分量,足證果然腹笥深廣。據說,因此梁先生買腰帶總嫌尺碼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只大號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是否謠言,卻未向梁先生當面求證。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門子,總有點心招待,想必是師母的手藝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兩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只知他下筆論起珍羞名菜來,頭頭是道。就連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動,饞腸若蠕。在糖尿病發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實也飫足了。有時乘興,他也會請我們淺酌一杯。我若推說不解飲酒,他就會作態佯怒,說什麼「不菸不酒,所為何來?」引得我和夏菁發笑。有一次,他斟了白蘭地饗客,夏菁勉強相陪。我那時真是不行,梁先生說「有了」,便向櫥頂取來一瓶法國紅葡萄酒,強調那是一八四二年產,朋友所贈。我總算喝了半盅,飄飄然回到家裡,寫下〈飲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讀而樂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國》上,一時引人矚目。其實這首詩學濟慈而不類,空餘浪漫的遐想;換了我中年來寫,自然會聯想到鴉片戰爭。
梁先生在台北搬過好幾次家。我印象最深的兩處梁宅,一在雲和街,一在安東街。我初入師大(那時還是省立師範學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將滿,又偕夏菁去雲和街看梁先生。談笑及半,他忽然問我:「送你去美國讀一趟書,你去嗎?」那年我已三十,一半書呆,一半詩迷,幾乎尚未閱世,更不論乘飛機出國。對此一問,我真是驚多喜少。回家和我存討論,她是驚少而喜多,馬上說:「當然去!」這一來,裡應外合勢成。加上社會壓力日增,父親在晚餐桌上總是有意無意地報導:「某伯伯家的老三也出國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經不久。果然三個月後,我便文化充軍,去了秋色滿地的愛奧華城。
從美國回來,我便專任師大講師。這時他已從雲和街故居遷至安東街,住進自己蓋的新屋。稍後夏菁的新居在安東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羨慕的梁府近鄰,也從此,我去安東街,便成了福有雙至,一舉兩得。安東街的梁宅,屋舍儼整,客廳尤其寬敞舒適,屋前有一片頗大的院子,花木修護得可稱多姿,常見兩老在花畦樹徑之間流連。比起德惠街與雲和街的舊屋,這新居自然優越了許多,更不提廣州的平山堂和北碚的雅舍了。可以感受得到,這新居的主人住在「家外之家」,懷鄉之餘,該是何等的快慰。
六十五歲那年,梁先生在師大提前退休,歡送的場面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終身大事」,《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之中譯完成,朝野大設酒會慶祝盛舉,並有一女中的學生列隊頌歌:想莎翁生前也沒有這般殊榮。師大英語系的晚輩同事也設席祝賀,並贈他一座銀盾,上面刻著我擬的兩句讚詞:「文豪述詩豪,梁翁傳莎翁。」莎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歲,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歲,其實還不能算翁。同時莎翁生前只出版了十八個劇本,梁翁卻能把三十七本莎劇全部中譯成書。對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聽了我這意見,梁翁不禁莞爾。
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後來夏菁擔任聯合國農業專家,遠去了牙買加。梁先生一度旅寄西雅圖。我自己先則旅美二年,繼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後才回台灣。高雄與台北之間雖然只是四小時的車程,畢竟不比廈門街到安東街那麼方便了。青年時代夜訪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為溫馨的回憶,只能在深心重溫,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實不僅梁先生,就連晚他一輩的許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見日稀。四小時的車程就可以回到台北,卻無法回到我的台北時代。台北,已變成我的回聲谷。那許多巷弄,每轉一個彎,都會看見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與回聲谷裡。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鄉情怯,怕捲入回聲谷裡那千重魔幻的漩渦。
在香港結交的舊友之中,有一人焉,竟能逆流而入那回聲的漩渦,就是梁錫華。他是徐志摩專家,研究兼及聞一多,又是抒情與雜感兼擅的散文家,就憑這幾點,已經可以躋列梁門,何況他對梁先生更已敬仰有素。一九八○年七月,法國人在巴黎舉辦抗戰文學研討會,大陸的代表舊案重提,再誣梁實秋反對抗戰文學。梁錫華即席澄清史實,一士諤諤,力辯其誣。夏志清一語雙關,對錫華翹起大拇指,讚他「小梁挑大樑」!我如在場,這件事義不容辭,應該由我來做。錫華見義勇為,更難得事先覆按過資料,不但贏得梁先生的感激,也使我這受業弟子深深感動。
一九七八年以後,大陸的文藝一度曾有開放之象。到我前年由港返台為止,甚至新月派的主角如胡適、徐志摩等的作品都有新編選集問世,唯獨梁實秋迄今尚未「平反」。如今大陸上又在壓制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此事恐怕更渺茫了。梁先生和魯迅論戰於先,又遭毛澤東親批於後,案情重大,實在難以為他「平反」。梁實秋就是梁實秋,這三個字在文學思想上代表一種堅定的立場和價值,已有近六十年的歷史。
梁實秋的文學思想強調古典的紀律,反對浪漫的放縱。他認為革命文學也好,普羅文學也好,都只是把文學當做工具,眼中並無文學;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贊成為藝術而藝術,因為那樣勢必把藝術抽離人生。簡而言之,他認為文學既非宣傳,亦非遊戲。他始終標舉安諾德所說的,作家應該「沉靜地觀察人生,並觀察其全貌。」因此他認為文學描寫的充分對象是人生,而不僅是階級性。
黎明版《梁實秋自選集》的小傳,說作者「生平無所好,唯好交友、好讀書、好議論。」這三好之中的末項,在大陸時代表現得最為出色,所以才會招惹魯迅而陷入重圍。季季在訪問梁先生的記錄「古典頭腦,浪漫心腸」之中,把他的文學活動分成翻譯、散文、編字典、編教科書四種。這當然是梁先生的台灣時代給人的印象。其實梁先生在大陸時代的筆耕,以量而言,最多產的是批評和翻譯,至於《雅舍小品》,已經是三十九歲所作,而在台灣出版的了。《梁實秋自選集》分為文學理論與散文二輯,前輯占一九八頁,後輯占一六二頁,分量約為五比四,也可見梁先生對自己批評文章的強調。他在答季季問時說:「我好議論,但是自從抗戰軍興,無意再作任何譏評。」足證批評是梁先生早歲的經營,難怪台灣的讀者印象已淡。
一提起梁實秋的貢獻,無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譯績,這方面的聲名幾乎掩蓋了他別的譯書。其實翻譯家梁實秋的成就,除了莎翁全集,尚有《織工馬南傳》、《咆哮山莊》、《百獸圖》、《西塞羅文錄》等十三種。就算他一本莎劇也未譯過,翻譯家之名他仍當之無愧。
讀者最多的當然是他的散文。《雅舍小品》初版於民國三十八年,到六十四年為止,二十六年間已經銷了三十二版;到現在想必近五十版了。我認為梁氏散文所以動人,大致是因為具備下列這幾種特色:
首先是機智閃爍,諧趣迭生,時或滑稽突梯,卻能適可而止,不墮俗趣。他的筆鋒有如貓爪戲人而不傷人,即使譏諷,針對的也是眾生的共相,而非私人,所以自有一種溫柔的美感距離。其次是篇幅濃縮,不事鋪張,而轉折靈動,情思之起伏往往點到為止。此種筆法有點像畫上的留白,讓讀者自己去補足空間。梁先生深信「簡短乃機智之靈魂」,並且主張「文章要深,要遠,就是不要長。」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證,而中外逢源,古今無阻。這引經據典並不容易,不但要避免出處太過俗濫,顯得腹笥寒酸,而且引文要來得自然,安得妥貼,與本文相得益彰,正是學者散文的所長。
最後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贅,他出身外文,卻寫得一手道地的中文。一般作家下筆,往往在白話、文言、西化之間徘徊歧路而莫知取捨,或因簡而就陋,一白到底,一西不回;或弄巧而成拙,至於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梁氏筆法一開始就逐走了西化,留下了文言。他認為文言並未死去,反之,要寫好白話文,一定得讀通文言文。他的散文裡使用文言的成分頗高,但不是任其並列,而是加以調和。也自稱文白夾雜,其實應該是文白融會。梁先生的散文在中歲的《雅舍小品》裡已經形成了簡潔而圓融的風格,這風格在台灣時代仍大致不變。證之近作,他的水準始終在那裡,像他的前額一樣高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