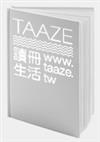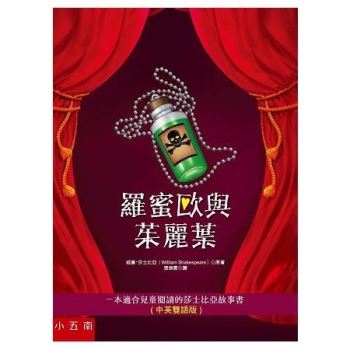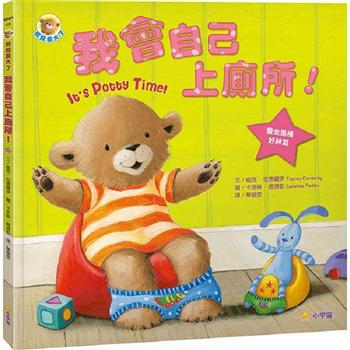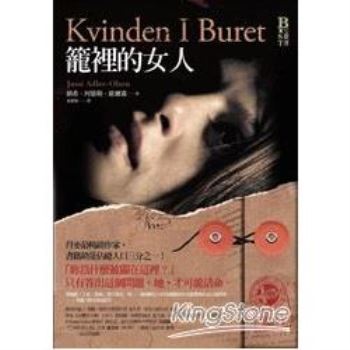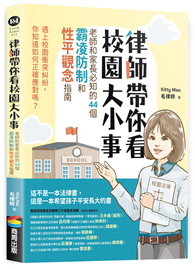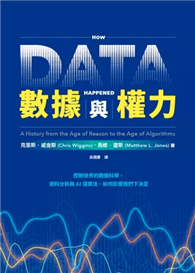推薦序
哲思的喜悅與旋律
須文蔚
兩年前你來到臺北,提出畢業製作,一本充滿哲思的詩集。
雖然你在山風海雨中度過了三年,花蓮的草木變形成「幽靈草」,遊客如織的沙灘用來悼亡排練,溯溪時意識流動思索死亡與憂傷,並沒有太多縱谷風光進入詩集中,多的是憂愁。
海德格將「憂愁」視為人類存在的基本結構,他從一則羅馬寓言中揭示「憂愁」的本源意義:憂愁女神塑造了人,朱庇特賦予靈魂,農神(時間之神)則判定人活著時就屬於憂愁。因此,「憂愁」與「時間」構成了存在的源頭和基本方式。而你筆下的世界多是閱讀所得,是你糾結、思辯與質疑的各式各樣恐懼與害怕,或許正因如此,你執著在創世神話或宗教中,尋找題材。
〈序章〉以三幕劇的形式展開,描寫世界的初始。第一幕描繪了渾沌的狀態,暗示著創世之前的虛無。第二幕則以擬人化的手法,讓「天空」與「海洋」對話,並提及「道生一,一生二,三生萬物」,這明顯是引用了道家的創世觀。旁白的角色也彷彿是造物主一般,引導著生命的誕生。整首詩以戲劇性的方式揭開序幕,以文字打造一則創世神話。
你更揉合多個與宗教和創世神話在〈靜物〉一詩中,你直接引用了《古蘭經》的經文,描述安拉降水創造色彩各異的果實,以及山上不同顏色的道路。你更提到了台灣原住民(卑南族、達悟族、泰雅族)的創生神話,例如從石頭或竹節中誕生人類的故事。各色不同文化的創世敘事,並置在同一首詩中,展現了多元的宗教和神話色彩,也開展了存有的辯證。
在屬靈的思索外,你也執著以科學為意象,已極其罕見的天文或物理的意象,用以譬喻人生或藝術的意涵。
〈軌道〉表面上以火星運行的現象,用以觀察情人的隱瞞:「欣賞你踱步的軌跡/歪七扭八的八/而星系同宇宙沉思著/『這兒並沒有祕密呀』」,將情人日常迂迴的行走,以克卜勒定律比喻,揭示宇宙的規律性並無奧秘,但人性看來要複雜得多。
更為精彩的是〈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即興〉 一詩,你寫到「下班後的科學家暫且卸下了肩膀/也揉一揉鏡片後侷限的肉眼/連日失眠已瀕極限」,描繪了科學家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詩中直接提及了「測不準原理」,這是量子力學的一個核心概念,「總是這樣當他越凝神/光火就如同爵士節拍變化、躲藏/忽快忽慢無法數/『必然是/不準確的』他尋思字詞中的矛盾/這不確定性的重擔」。 你巧妙地將科學原理與爵士樂的即興性相類比,讓讀者理解你反覆迷失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間,充滿的各種困惑。
〈夸克的歧義性〉的標題和內容都直接指向粒子物理學。詩中解釋了「夸克」這個詞的雙重含義,一是文學作品《芬尼根守靈》中的用法,一是物理學中基本粒子的名稱。「物理學家的夸克/比光波還短,比質子、中子更/基本。看不見所以無色,構成/『我在桌子前敲打詩篇』/夸克,帶著清脆的哀音/埋進萬物至深邃處,猶如靈光」。 這段描寫清晰地呈現了夸克在物理學上的意義,指的是比原子中的質子更小的基本粒子存在,而你想說明,文學能夠探究世界更為細微、遙遠與深邃的意義,無以名之的靈光小如塵埃,也巨大如星雲。
記得我花了許多時間向你解釋,詩或許不太適合談哲學,你最深愛的柏拉圖總以為詩人並不具有真正的知識,也總是沒辦法說出真理,哲學家的理性總能壓倒詩的非理性,讓繆斯神授的詩的智慧顯得蒼白無力。而你的作品初稿中,又太耽溺於散文形式的結構,或許是急著說道理,並沒有特別重視音樂性,在你開天闢地的想像中,不免可惜。
遠古的時候,詩與歌不可分,又與舞蹈密切有關,詩歌茁壯於祭祀,表達出自人類心底亟欲表達心思情感的願望,又能傳達人類出入「現實」與「未知的世界 」的想像。因此,在中國上古歷史漫長的時光中,「詩歌不分」的現象表現在詩樂並起的宗教儀式中。其後無論是詩經國風中的記載著來自田野中的情思,楚辭把散文時代的悲哀轉為詩歌,你想帶讀者穿梭「開天闢地」的世界應當是最講究音樂性的,不是嗎?
現代詩的音樂性確實難以掌握,節奏是音樂性的基礎,余光中就曾明確指出,詩的音樂性最基本是由節奏造成的,節奏的來源是動作的經常重複,週而復始。因此,如何在分行的自由詩中加入適當的迴環複沓的段落,藉由語音的重複,由同樣的語詞或句式,産生複沓的音樂效果,這是現代詩人必須體會、實驗與掌握的秘訣。
你原本的〈手肘與奔奔石〉版本,句子較長,象徵繁複,在新的版本中,語言結構簡潔而富有意象,通過簡短的句子和動態的動詞,描繪出手肘支撐和奔奔石滾動的畫面。「奔奔石」這個雙音節詞語的重複出現,在簡短的語句中形成一個輕微的節奏點,讀來就更為率真與輕快。
在你用了將近兩年的修改後,我發現你重視前後段落使用重複的句型,用以控制節奏,最明顯的莫過於〈比丘問佛〉 一詩,原本散文詩的結構,調整為分行詩,不僅如此,這首詩以「應不只是」和「應不只是」的句型開頭,形成一種層層遞進的詰問,帶有探索的節奏。加上首尾都以:
比丘問佛
世界
世界究竟為何物?
兩次扣問,一次比一次更逼近真相,也顯示出你已經掌握了「內在音樂性」。
又如〈水漫至胸口這麼重〉 一詩,你反覆動用「水漫至胸口這麼重」這個句型,在不同段落重複出現,彷彿海浪的拍打,強調了沉重感,並作為節奏上的錨點,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當閱讀你大幅度調動的版本,看到許多重複的句型閃現在詩作中,有的營造出穩定的韻律感,有的則透過重複和變化產生特殊的節奏效果,增強詩的音樂性,相信你一定在文字、呼吸與脈動中,偷偷收穫了寫詩的喜悅。
當你希望能透過詩傳達思想,誠如海德格在《走向語言之途》中說:「一切凝神之思就是詩,而一切詩就是思。」你確實是這個時代少見的,願意探索崇高的青年詩人,很開心你不止讓文字停留在在思想中游動,更以節制與控制力,展現出哲思的喜悅與旋律。
自序
當我們談論世界
下載了可以指認山名的App之後某天,我騎上摩托車,準備沿著東華大學的外環道路畫一個半圓,回到位於後門的租屋處。很難不注意到近在眼前的山色如此碧藍,那是一種因為空氣中濕潤的水氣而顯得更加飽和的一種碧藍。大雨確實下過了。
半空中浮起一座青色、透明、彷彿剛從假寐後甦醒,比其他山脈更高大也更疏遠一些的山,她彷彿是其他山頭的影子,又或者是油墨未乾的印子,我將鏡頭對準她,App顯示:「木瓜山」。
隔日驅車離開學校,途經和榮大橋時,又被層層交疊的山脈群所吸引,烈日下的山有明確的形狀,好像從藍天白雲的背景下跳了出來,展示著方位與姿態,凸出的是深綠,凹塌的是湛藍,我興沖沖又往最高的山頭照相。一看,竟又是木瓜山。那時我待在花蓮剛滿一年,看山只道是山,於是留下一個「到處都是木瓜山」的直覺印象後,我在腦海中建構出一個奇怪的地理模型,以為木瓜山伸出手臂環抱著校園。
校園的確四面環山,當我走出圖書館、或從研究室的走廊上往外張望,每次抬頭都加深和驗證了我的想像。此後好幾個月──
直到有天,我意外看見一張旅遊中心印製的壽豐地圖,這才發現校園的正門原來朝著東南方,從那裡望見的並不是木瓜山,而是海岸山脈的月眉山系。一年多來,我都活在錯誤的認識裡頭。
不知道該如何啟齒情感的五味雜陳,感覺就像房間的窗簾被掀起了一角,我朝外瞥了一眼,赫然看見原本以為是斑駁牆壁的所在,竟然有一個顯而易見、理所當然的「真正的世界」。木瓜山和月眉山明擺著長駐於此,然而正是因為她如此明顯、毫無欺騙與遮掩的意圖,當原本的真實被推翻,另一種真實被揭露,這一刻反而令人不知所措。
柏拉圖曾在《理想國》中記述一個寓言故事:地下洞穴裡住著一群人,人們被鎖鍊限制住因此只能面朝著牆壁。他們的身後有一堵矮牆,且矮牆後有一較高的火堆,時不時就有些野獸或另一群沒有鎖鍊的人經過,被囚禁的人們終其一生只看得見牆壁上那些來來回回、各式形狀的影子,他們為之命名、分類與討論,並且得到一個共識,堅信這些影子就是事物的真實。難道我也是這樣嗎?我是否長期活在自圓其說的幌子之中?
外面的世界分毫未動,我重複規律的生活,只是在這天之後我懷著一點點存疑,當說出「一定、絕對、總是」時,會因感到心虛於是改口為:「說不定,可能,有時候」。
柏拉圖的洞喻,故事還有後半部。其中有個囚徒被帶領著越過矮牆與火堆,最後穿過洞口,來到所謂的「外面的世界」。河流、山坡、花朵盡現眼前,然而這囚徒已經歷過先前的啟蒙,他很快學會質疑,即使是這炫目又迷人的花花萬物,也未必全然可信,最終所能信賴的只有太陽光。
那裝不起、帶不走的太陽光,比摘得走、可裝飾在衣上的一朵花更加真實嗎?我現在也是懂得質疑的囚徒之一了。我持續著如此這般鬼打牆的自我辯證,儼然是個愛恨交織的懷疑論者。思辨的最後,或者說半途,也終於因為疲倦或者惱羞成怒的緣故,我決定反倒過來怪罪給世界﹙現在它有一張藏在面具後的臉,臉上有皮笑肉不笑,無法看清的表情﹚。
我多想拆穿世界的假面,知道這隨時都在變動又好像會永遠這般存在的世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令我為之起舞、奔忙、虛耗,又無視我在其中頓足和落淚的世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曾和朋友熊與秀辯論關於世界的話題,彼時我們圍著一張撿來的雕花小桌席地而坐,桌上還有幾瓶啤酒、幾包洋芋片,哲學研討所需的一切已萬事俱備。「『房間』並不存在。」我剛剛斷章取義地讀過德國年輕哲學家馬庫斯•加布里埃爾(Markus Gabriel)的「世界不存在」 說,所以我借題發揮:「房間除了是現在看到的房間之外,還是我對房間的看法與你們對房間的看法,三種交集的事物,所以沒有一個共識的房間存在。」
秀說:「不,還是有一個客觀的房間存在,這個有地址、坪數和高度的立方體是可以觸碰到的,我們待在同一個房間裡。」秀在農業研究單位上班,她曾在研究所時期找到過一隻沒有人發現的菌種,我認為她是個可信賴之人。不過後來她告訴我,其實嚴格說來應該是為土壤裡面篩選出來的菌取了一個編號,學術上的描述需要更精確一些,而且並不是研究所時期,而是大學時代。
「我們應該先定義『房間』這個詞,我們談的是可見、可觸碰的房間,還是抽象的房間的概念?」接著開口的熊研究所念的是國際關係,畢業後五年來他嘗試過許多工作領域如音樂、教育、報社,卻都未有歸屬感,他抵達過幾次身心症的低谷,仍頑強地在起伏不定如海浪般的狀態裡維持著平衡。
而我呢,大概是一個從城市出逃的殘兵敗將,表面上以念研究所為名義,實則在拖延長大所需要面對的種種社會期待,藉著花蓮的隱蔽,山海無盡的容錯率,爭取一份思考與休息的時空。我們三個膝蓋抵著膝蓋,在我迷你的雕花小桌旁,談論房間好幾個鐘頭,直到洋芋片和啤酒罐都空了才停止。
是夜,燈關了,秀打地鋪睡在我的右下方,熊在我的左側沉沉睡著,幾乎察覺不到呼吸,睡眠像小小的死亡讓我們預演分離。
窗外滴滴答答,我從經驗的直覺而非身體的確認判斷那是雨聲,半夜的花蓮經常有雨,如果你曾花一天的時間只是賞雨,你或許也會同意,雨才是大地這座舞台的主角,我們這樣微小的龍套則肅靜地平躺著,等待天亮。
很久之後,我仍會想起那個晚上,想起熊反覆說著對城市和陰雨天的不適應,他說像全身都要腐爛,他說像沒有盡頭的洞穴,當他說:「這是一個爛掉的世界。」時,我心中一沉,最終決定永遠地關上耳朵與訊息的視窗。
當時我並不知道,他的痛苦是如何轉移為我的,我只知道我必須躲起來,否則就要被淹沒。
現在,三百個日子後我逐漸明白,或許只是因為,我實在愛極了「世界」這個龐大又抽象的概念,遠甚於面前脆弱又迷惘的個體。
帶著巨大的疑問,不知從何而生的罪惡感,也許還有些遊說他者的意圖,一種想讓他見識一番更好世界的心情,我湧起寫作的慾望。
「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存在,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的巨大命題。古希臘的泰利斯和亞里斯多德,應不是最早產生好奇心的人,卻可能是第一批相信「世界能被了解」的信徒,亞里斯多德首次將世界當作一整體來看待,並認為在這些隨機與雜亂的花花萬物之中,應該有某個簡約的法則,一個「為什麼」。從中出現了數學、物理學、科學和天文學。有時候,在某些地方,「世界」更像是一個渾然天成的答案,而非一個可供拆解的問題。許多創世神話與宗教信仰都有「造物神」出現,在《古蘭經》與《聖經》裡頭,上帝說了有,世界便在彈指間配備齊全、瞬間到位﹙跟漫長的幾億光年相比,七天應該也算是彈指之間﹚。這股理直氣壯的氣魄,確實與木瓜山和月眉山的不言自明,帶給我相似的感受。
中文的「世界」一詞,起源於梵語漢譯,由「世」﹙loka﹚與「界」﹙dhātu﹚兩個詞組成,前者譯為時間,後者則是空間。時間與空間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可以分而論之,不過自從二十世紀初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後,「時空」已成為互相牽引、本質相連的整體,再精細的地球儀或衛星圖都不可能呈現它的全貌。英文的「world」一詞,也與地理空間的「Earth」有一定的區別,常用在更抽象、具精神性的概念,我想或許很適合引用阿拉丁電影中的歌詞來解釋:「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一全新的世界,一橫出的觀點﹚。
奇妙的是,當我讀得越多,當我談論得越多,世界就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左橫右豎著一些我不曾思及的面向、一些我不曾看過的背面。閱讀與書寫這份創作計畫的一年多來,我就像那個在海灘上拾海星丟回大海的少年。笨拙地打開了一個文件檔,將讀到的所有有關世界觀的段落摘要下來,一只、一只、一只、再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