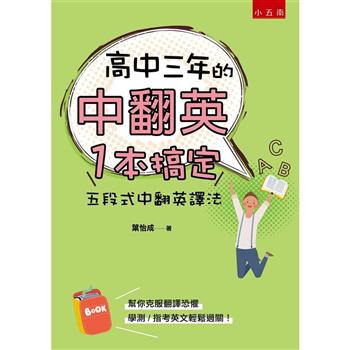楔子 午夜驚夢
「哥,我好累!我堅持不住了!」
漫漫的海域,沒有船隻,沒有燈火,唯有兩個約莫只有十來歲的孩子在海水裡掙扎。
沒有可以讓人視線變得清晰的色彩,只有一片磨人心志的漆黑。
海水冰冷刺骨,兩個孩子唯有拼命的向前游去,可是,前方那隱隱約約的小島,彷彿可望而不可即!
「柔兒,不要放棄!永遠都不要放棄!不要怕,有哥在!」
然而兩個身處大海的孩子,感覺到了死亡在降臨,彷彿整個天下只剩下他們兩人。
天上沒有明月,沒有星光,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只有無窮無盡,蔓延不止的黑!
被喚為柔兒的孩子意識已模糊,手腳在冰冷的海水裡變得遲緩笨拙,最後停止拍打。
「柔兒,不可以!不要閉眼睛,妳再堅持一下!抱著哥,相信哥,娘會來找我們的,妳再堅持一下,我們游到那個小島上就有救了!」
冷,彷彿將五臟六腑都凍裂了,這致命的寒冷讓睡夢中的余秋男感覺到四肢百骸都在顫抖!
「不……不要!」
余秋男驚聲而起,已跳離了身下的氣墊床,冷汗涔涔。
夢,這個困擾了她多年的夢,總是讓她在午夜夢迴時驚出一身的冷汗,然後是深深的痛!
撫著自己的左胸,她確定自己的心臟很健康,但每次夢醒時,心總會隱隱作痛!
夢裡那兩個孩子的容顏始終是模糊不清的,但那種瀕臨死亡的絕望氣息,總讓她感覺到好像有塊千斤大石壓在胸口,無法呼吸,導致整顆心似乎在痙攣!
她推開船艙的鐵門,冬夜的海風呼嘯著灌入,一個猛顫之後,她急忙披上大衣。
站在甲板上,今晚的海面一片死寂,看不到任何的光亮,海風嗆得她有片刻的窒息,她只好轉過身,背風而站。
她是這次被派往索馬利亞執行任務的狙擊手,整個組織裡的唯一一個女狙擊手。此時,自己身處的這一艘大船正航行在距離索馬利亞還有一百海里的海域上。
能成為狙擊手,她當然與一般女子不同,她的敏感度和抗壓性,甚至都強過她的男性隊友。
譬如此刻,她猛然聞到危險的氣息,與那夢境相同的氣息,意味著死亡即將降臨。
擁有世界一流設備的軍用船隻,居然未曾探測到海水底下的異樣,當余秋男感覺到異樣的時候,來不及叫醒隊友,船頭船尾已同時著火了!
「不好了!」
只是一聲,船艙內飛出幾十道身影,余秋男想要回艙拿出屬於她的裝備,卻聽得一聲巨響,整艘船被炸得粉碎!
她以最快的速度跳躍而出,掉進海裡時,她已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被大大小小的碎片襲中!
冰冷刺骨的海水瞬間將她緊緊裹住,余秋男看到海面上火光映天,隨著那團熊熊燃燒的大火,她的一切也被燒盡,包括她的生命!
她只覺得有一股熟悉的痛楚向她襲來,意識逐漸模糊,她彷彿看到了有兩個小孩在為生命而努力!
「不要死啊!求求妳不要死!求求妳!」
余秋男也不想死,可是碎片扎進她身體的各個要害,她已經沒有力氣為自己的生命而努力了!
可是,充斥在耳邊永遠有著這麼一個聲音──不要死啊!求求妳不要死!求求妳!
第一章 無恥之徒
裕夏朝永嘉四年臘月。
北鄴頌城。
頌城地處沿海,是北鄴的商業重城,南來北往的商賈、文官武將、江湖人士,或紮腳留宿,或長期逗留。
如此繁華大城,除了各種各樣的商舖櫛比鱗次,隨街兩旁還有來自各地的小行商沿地擺賣,當然還不乏那煙花之地,溫柔之鄉。
戌時三刻,店鋪早已打烊,街道上行人三三兩兩,相較於白日的熱鬧,顯得冷清許多。不過,在這寒冷的冬夜,完全不影響頌城第一青樓「錦雀樓」的生意。
三層高的樓房,層層懸掛著絹製燈籠,遠遠望去就像是屹立於夜色之中的海市蜃樓,彌漫著瑰麗綺靡的氣息。
富麗堂皇的大廳正牆雕刻著百花爭豔圖,色彩斑斕,栩栩如生,大廳中央朱漆圓柱撐起一個圓臺,身著碧紗羅裙的歌姬正揮動著水袖在輕歌慢舞。
絲竹之聲不絕於耳,輝煌燈火下鶯鶯私喁,燕燕低語。不過,仔細一看,今晚的錦雀樓似乎較以往有所不同,好像少了什麼?
男人,沒錯,此刻的錦雀樓裡,竟只有一個男人!
大廳中央的看臺下,只坐著一個華服少年,少年眉眼彎彎的看著眼前一個個嬌豔貌美的女子,似春水瀲灩的桃花眼中閃爍著邪魅的光芒,身處一片奼紫嫣紅之中,已然成為那一點引人矚目的碧綠,看這架勢,少年今晚是將錦雀樓包下了。
「公子,錦雀樓的所有姑娘如今都站在您面前了,美的、豔的、俏的、媚的……,您慢慢挑,慢慢選!」
錦雀樓的老鴇喜逐顏開,做這行這麼多年,她最為擅長的便是看人,堂中所坐的少年非富即貴,出手闊綽猶勝當年北鄴司徒堡的少堡主──司徒磊。
少年眉梢一挑,勾唇一笑,一手伸向身側的粉裝女子,那女子順勢倒進少年的懷裡,「公子,小女子霽雲。」
「豔若霽月,麗勝新雲……嗯,只是,豔麗有餘,嬌俏不足,可人不可愛!」少年一邊搖頭,一邊已經懷裡的美人推開,嘴裡還不忘嘖嘖而語,「可惜了!」
名喚霽雲的女子好不懊惱的瞪了少年一眼,跺著腳,甩著錦帕,扭臀走了。
少年仍是笑若燦花,順手攬過右手側的翠衫女子,那女子蛾眉微顰,紅唇輕啟,柔聲道:「公子抬愛,小女子玉秀。」
那少年托起玉秀溜尖的下巴,饒是人家姑娘楚楚可憐,柔情脈脈的與他四目相對,他卻毫不掩飾他的惋惜之色。
「美似馥蘭,柔勝婉柳,雖說溫婉動人,卻不夠清新脫俗,可憐不可人!」
「你……」玉秀眼眶一紅,竟似哭了,以帕拭淚。
少年卻一點都不憐惜的揮手趕人。
老鴇站在一側,臉色漸沉,還從來沒有人挑剔過她錦雀樓的姑娘,整個北鄴,誰不知錦雀樓的姑娘是最美麗、最溫柔、最動人,也最能討客人歡心的了。
少年於此時起身,雙手負後,一眼掃過排排站在跟前的數十個女子,那笑仍是肆無忌憚,沒心沒肺。
而那些女子在他毫無威懾之力的眼神注視下,竟個個莫名的心虛起來,人前賣笑,所得回報除了金錢,還有一些虛無不切實際的讚美。
但當讚美變成平生不曾聽到過的批評時,很自然的就怒意橫生了。
「面若桃花,剪水秋眸,只可惜,姑娘兩肩削耷,如此輕紗薄衫之下,襯不出窈窕之軀。」
「你……」身著水湖藍輕衣薄紗的女子以寶扇掩臉,忿忿而退。
這下老鴇沉不住氣了,上前一步,心裡雖然不滿,但還是八面玲瓏的賣笑討好,「公子,我這錦雀樓的姑娘豔名遠播,不要說是在頌城,即使是整個北鄴,乃至京城都未必能挑出這般好模樣的姑娘來呀!」
「媽媽說得沒錯,妳這錦雀樓的名聲確實是響徹全國,在下就是遠從京都慕名而來的,一擲就是萬兩黃金,妳難不成還看不出我的誠意嗎?」
老鴇一看就知道這不是一個能輕易打發的人,她拉過雕花木椅,以袖拂之,笑容可掬道:「公子且坐下吧!」
少年一撩繡著螭紋的袍角,舉止極為優雅,即便是以玩世不恭之態翹起二郎腿,還是難掩通身的貴氣。
臺上的舞姬這時水袖一拋,那少年竟伸手而接,和那舞姬各持一端的眉目傳情。
「想來公子必定出身名門,看多了國色天香的佳人,一般女子在您眼裡自然就成了庸脂俗粉了!」
少年放縱而笑,原本握在手中的綠色水袖已鬆手,原本充滿期待的美豔舞姬,臉上不禁露出失望之色。
「媽媽,妳是不是還藏著什麼絕色尤物?」
「不敢,不敢,今晚整個錦雀樓都是您的,我怎敢私藏什麼姑娘啊!」
「唉,看來要虛此行了!」少年意興索然的拍拍手。
「公子啊,離這不遠的緬城還有錦雀樓的分號,如果公子有興趣,我可將那裡的姑娘叫來。」
「好,明日本公子再包下妳這錦雀樓,媽媽,到時妳可不要再讓在下失望了!」
「公子放心!公子放心!」
老鴇心中打著如意算盤,眼看著明晚又有萬兩黃金可以到手,臉上厚厚的脂粉因為她的笑而抑止不住的開始抖落。
* * * * * * * * * * * * *
臘月初八,樂正家祭祖之日,冬風凜冽,雪白千里,寒光映射,祠堂前幾株梅花開得較於往年更為絢麗。
有一少年白衣勝雪,白狐毛領襯著他無與倫比的容顏。
他走至祠堂門前,身後著一身素色衣裳的五旬婦人忙為他打起厚重的門簾,恭敬的說道:「公子請。」
少年點頭,便進了堂內。
四十八塊樂正家的祖宗牌位分成數排,烏木鎏金的牌位在燭火的映照下顯得莊嚴肅穆。
祠堂兩側分別立著兩個黑衣家丁,在見著少年之後彎腰行禮,「公子。」
少年仍是一言不發的點頭,走到右下側一塊繫著紅線的牌位前,牌位上刻著「樂正華柔」四個金字。
深邃的眼眸中霧氣漸濃,半晌才緩緩嘆了口氣,收回視線。
「公子,事情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您就別再放心上了!」
聲音略顯蒼老,卻溫柔親切,說話之人正是一直跟在少年身後的老婦人。
少年點頭,啟唇想要說話,卻聽得祠堂外有聲音響起,「老夫人和夫人來了!」
少年走至門簾前,親手挑起。
屋外白雪皚皚,冬風隨著門簾挑起而迅速灌入,祠堂內的燭火頓時被吹得晃晃悠悠,整個祠堂彷彿也隨之晃動起來。
「都來齊了?」
隨著一聲蒼老威嚴的聲音響起,門簾放下,燭火繼續燃燒,一切恢復如初。
祠堂內多了三個人,正中的那位一頭銀髮,穿著簡潔卻不失華貴,正是剛剛問話之人,也是先帝當年親封的一品誥命,北鄴頌城樂正家輩分最高的老夫人。
只是短短一句問話,便顯現出老夫人在家中的威信。
扶著老夫人左手的是著一身藕色錦服的中年婦人,丰姿冶麗卻妝容簡潔,只在髮髻斜插一支碧玉簪,雖近不惑之年,卻是保養得宜,纖纖弱質,居然不亞於雙十女子!
據說,樂正家的夫人年輕時以美貌而聞名天下。這中年婦人如此簡裝淡妝卻仍是難掩驚世之豔,想來就是六年前過世的侯爺樂正赦的妻子──鄢敏。
樂正老夫人右手挽著的則是一絕色少女,少女的肌膚白皙無瑕,五官輪廓精緻的好像經過精心雕琢一般。
那少女在見著少年之後便放開了原本挽扶著祖母的手,跑到他跟前。
嫣然一笑百花遲,少年覺得院前的白雪紅梅皆成了她的陪襯,他的手臂被少女緊緊纏繞,只聽得她那如早春黃鸝之聲響起,「哥,你說過這白狐皮要送我做披氅的,你怎能說話不算數,用自個兒身上了!?」
少女凝脂般的肌膚在燭光的映襯下,煥發著珍珠般細緻光暈,顧盼之間,光彩奪目,容貌和樂正夫人有著幾分相似,想來便是樂正家的三小姐──樂正華濃。
北鄴人人都知,上天將天下間的一切美好都給了樂正家,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樂正家到了樂正赦這一輩,人丁過於單薄。
長女樂正華柔於十二歲那年溺水而亡,眼下只留得樂正夕和樂正華濃兄妹。
樂正華濃一邊抱怨,一邊抬手撫弄著少年的白狐毛領。
天下間恐怕只有她敢這麼做,因為「琉璃公子」樂正夕平素最不喜有人近身於他。
樂正夕清貴俊美的臉上因為樂正華濃親昵的舉動而流露出難得一見的溫和,眉眼之間添了幾許笑意,「放心,給妳留著呢,妳讓蘇嬤嬤來取便是!」
低沉而富有磁性的聲音,帶著說不出的魅惑,短短幾句便足以讓人陶醉其中。
「華濃,不許再胡鬧了,會誤了時辰的!」
鄢敏蓮步輕移,走至兄妹跟前,樂正華濃俏皮的吐舌,轉而挽住母親的胳膊。
而樂正夕已然收起剛剛的溫和,朝老夫人躬身一禮後,吩咐身後的老婦人祭祀之禮可以開始了。
樂正老夫人和樂正夫人同時看著樂正夕那孤傲的背影,就像一堵冷硬的高牆,生生將外界的一切隔開,讓人難以靠近。
焚香、獻花、獻果與獻酒後,跪拜於案前,雙手合十虔誠默禱,整個過程莊嚴而隆重。
半個時辰後禮畢,樂正夫人和樂正華濃攙扶年事已高的老夫人坐於祠堂一側。
樂正夕沒打算多做停留,朝老夫人躬身一禮,「夕先告退了。」
言語間仍是清淡疏離,全無尋常之家祖孫間應有的融融之情。
老夫人睇了樂正夕一眼,亦是冷冷應聲,「下去吧!」
樂正夕轉身時,只見厚重的門簾被人撩開,祠堂內的燭火被趁勢而入的冬風吹熄了幾盞。
一灰袍老者躬身而進,對著老夫人和樂正夫人行禮之後再轉向樂正夕鞠躬道:「公子,京都又來密函了!」
老者將一封書信恭敬的呈於樂正夕,樂正夕面無表情的接過打開,一目十行的看完後,揚眉淡淡問道:「東西呢?」
老者身後一個家丁雙手擎著一只烏木雕花的錦盒,老者指著錦盒道:「在這裡,請公子驗收。」
樂正夕伸手制止,轉身對老夫人和樂正夫人道:「陛下親函,說是敬王已到頌城,夕想知道老夫人和母親對於華濃和敬王的婚事到底有何主張?」
「我不嫁!」不等老夫人和樂正夫人回話,一旁的樂正華濃已蹙起蛾眉,拉住樂正夕,斷然拒絕,「敬王放蕩不羈,不思進取,無才無德,你們不可以將華濃的終身託付給他!」
「華濃!」老夫人厲聲制止樂正華濃的任性,「這是皇命,兩宮欽賜的婚事,豈可違抗!」
「他自己不也抗旨不想娶我嘛!」
這是令她最氣憤不滿之處,那個聲名狼藉的敬王赫連駒,居然先她一步抗旨逃婚!
沒想到,他竟然還敢來北鄴,雖說他身分尊貴,可這北鄴一百零八島好歹是樂正家的天下,強龍難壓地頭蛇,她樂正華濃是打定主意要為自己出這口惡氣的!
「夕兒,皇命難違,你就按著陛下的意思去做就是了。」老夫人做出決定,語氣堅定,不容置疑,「咱們樂正家深受皇家恩惠,才有今日的輝煌,斷然不可做出抗旨不遵之事!」
樂正華濃嘟著嘴,強忍著委屈不讓眼淚往下掉,萬般哀怨的看著樂正夕。
樂正夕心疼妹妹,卻也無可奈何,只能逃避轉身,出了祠堂。
屋外雪花紛飛,紅梅傲然屹立,樂正夕忍不住嘆了一口氣,他依稀記得多年前,一樣的寒冬,有兩個孩子在侯府的柳葉湖畔嬉鬧……
「哥,你瞧,這雪人長得像不像你?」
「柔兒,妳真是個傻丫頭,我和妳是孿生兄妹,長得極為相似,若說雪人長得像我,便也長得像妳啊!」
八、九歲的孩童,一個在柳葉橋西,一個在橋東,手裡抓著雪團使勁的砸向對方,笑聲響徹整個侯府……
「公子,回房吧,您這身子受不得凍的!」
樂正夕回頭,發現自己竟不知不覺中立於柳葉橋上,橋下河水已凝結成冰,他皺眉,扶著橋欄而行。
樂正一族其實並非皇親國戚,樂正先祖來到三面環海的頌城,便開始經營造船廠,因為用心鑽研,造船技術獨步天下,成了皇商,但凡裝備精良的軍用船以及裝飾華麗的官船,均出自頌城樂正家,也有了「船王」的美名。
後來因樂正一族不但能文,而且善武,深得帝王重用,擔起鎮守北鄴一百零八島的重任。
不過,當財富與權勢日益高漲,可與皇族相比時,就難逃功高震主的命運,百年前樂正家輝煌無比,富甲天下,也在那時,被當時的皇帝削勢減權,直至樂正赦一輩才重振家業,被先帝封為「定北侯」。只是樂正赦英年早逝,身為樂正家唯一的男丁,樂正夕身上的擔子無疑更為沉重。
樂正夕業精六藝,才備九能,十五歲便名揚天下,世人都道他神似琉,形似璃,光芒照人,「琉璃公子」之名便這樣傳開來了。
十六歲世襲侯位,十八歲掌權,掌管北鄴一百零八島大小事宜,其名其威早已超越樂正家歷代先輩。
呵,樂正,樂正一姓給了他無上的榮耀,也給了他不可推拒的宿命。
* * * * * * * * * * * * *
「蛾眉欲顰,雙眸點漆,似喜非喜,似嗔非嗔,好一個標緻的美人兒!」
是夜,仍是鶯歌燕舞,仍是燈火通明,仍是在錦雀樓,仍是那個長得異常俊美,身著華服的少年。
以極為張揚不羈的神態,打量著站在他眼前的黃衣女子。黃衣女子雙眸流轉成光,體態輕盈,嫣然一笑,傾城又傾國。
少年忍不住屏息,那女子不僅外貌出眾,更讓人為之驚嘆的是她周身散發出來的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
一身鵝黃衣衫若飛若揚,環佩叮咚,菱唇微啟之時,好似梅蕊綻雪。精緻的五官如精琢在白玉上一般,立體完美,剔透無瑕。
「絕色!絕色啊!」
終於有姑娘可以搞定這位難纏的主兒了,本該鬆口氣的老鴇,卻不知為何,眉頭輕蹙,手撫鬢角,好似頭疼了。
黃衣女子對上那個怔怔看著自己發呆的少年,眸中閃過一絲鄙夷之色,隨即,菱唇輕啟,那如早春黃鸝之聲緩緩響起。
「公子謬讚了,三兒這廂有禮了!」
「哈哈哈……」少年笑聲恣意,眉眼舒展,那泛著精光,亦正亦邪的桃花眼,猶如一彎新月,左手揚起,迅速的撫過女子細嫩的臉頰,「嘖嘖,真是滑嫩啊!」
女子杏目圓瞪,怒意在眼底展開,臉上卻仍強作笑顏,一手順勢覆上少年的手腕,絕色之顏頓生殺意,手上一用力,狠狠的扼住了少年的手腕,並開口冷斥,「真是天下第一不要臉之人,今日看我怎麼收拾你!」
少年俊美的臉上竟然還是一貫的悠哉,被那黃衣女子抓住的手腕,此時竟如魚在水般靈活,只是輕輕一轉便脫離了她的禁錮。
「姑娘好身手,好功夫啊!」
「可惡!」那女子眼看著這登徒浪子從自己的手掌心逃脫,不由得一陣懊惱,「今天我一定要廢了你!」
「哎哎哎,不要啊!在下初臨頌城,並不曾與人結下任何仇怨,姑娘何苦要置在下於死地呢?」
那少年嘴上雖在求饒,可是動作卻是不疾不徐,一邊說,一邊跑向站在一旁愁眉不展的老鴇。
「媽媽,妳得保我性命無憂啊!」
他不顧不管躲在老鴇身後,老鴇剛想開口說話,只是,那黃衣女子哪裡還有時間容她開口,施展輕功,高高躍起的同時,從腰後抽出一條軟鞭。
只見她一手輕揚,鞭子在空中閃出一道漂亮的弧度之後,直直的劈向他們。
少年提著老鴇的身子一閃,好不容易躲過那一鞭,老鴇早就嚇得臉色發白,顫顫巍巍的喊道:「我的姑奶奶,您就高抬貴手,饒了我吧!我這錦雀樓可經不起您這般折騰呀!」
「媽媽,妳閃開,今天我一定廢了這世間第一淫魔!」
語畢,女子手中的鞭子作勢又要揚起,少年卻仍是不慌不忙,不驚不乍的從老鴇身後閃出。
「姑娘會這般怨恨在下,定然是因為和我共赴雲雨之後,我卻將妳忘了,可我怎就想不起來了呢?」
女子俏臉頓時通紅,狠狠的啐了一口,「你這無恥的狂徒,看我不打爛你那張臭嘴!」
「姑娘怎知在下的嘴是臭的,莫非在下真曾一親芳澤於姑娘?唉,在下流連花叢無數,倒真是想不起姑娘來了!」
那少年也知此語一出,無疑是雪上加霜,語音一落,他早早躍開數丈之遠,臉上仍是盈滿笑意,看上去竟似和人在玩笑打鬧一般。
而那女子手中的鞭子已以極快的速度飛出,乍看之下,鞭子是朝向大廳的另一端,可是不知為何,那鞭子像長了眼睛似的,突然在空中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回轉,反朝少年的方向而去。
少年眉梢一挑,眼中狡黠一閃而逝,臉上隨即露出明顯的驚慌之色。
黃衣女子美目內笑意陡增,握著鞭子的手一提力,少年的身子順著鞭子旋轉兩圈,整個人也被捆得緊緊的,女子臉上終於露出了勝利的微笑。
「哼,果真是個廢物,三兩下就被本姑娘給生擒了!」
不過,少女話音剛落,少年的身子已飛快而轉,站在大廳一側看著這兩個不知為何鬥得死去活來的姑娘以及老鴇,個個都沒看清是怎麼一回事,在聽到一聲嬌叱之後,情勢完全倒轉了!
剛剛不是這番情形的啊!
只是眨眼,不!連眨眼的工夫都不到,為何被綁的人,從那少年變成了那女子?
再看看兩人的神情,一個仍是天塌下來都是笑嘻嘻、樂呵呵的樣子,而另一個,那傾城之容已全然扭曲,粉面通紅,呼吸急促。
少年愜意的拉過一把黃花木椅,一屁股坐下,將兩條腿擱在桌子上左擺右晃,一隻手握著鞭子一端。
「媽媽,妳今日果然沒讓我失望,倒酒!」少年另一手朝老鴇一揚,眼睛卻仍盯著那個被他反捆的黃衣女子,迎上女子似火在燒的眼眸,他倒是一副很享受的樣子。
「嗯,雖說性子辣了點,可是我喜歡,哈哈哈……」
「混蛋,你最好馬上將我放了!要不然你只要待在頌城一天,我便叫你一日不得安寧!」
黃衣女子說話的同時,眼裡的淚光也開始閃爍,她幾時受過這等侮辱,一個姑娘家被人綁得跟粽子似的任人笑話。
老鴇執壺為那少年斟酒,一臉討好的笑道:「公子,這姑娘是新來的,性子剛烈,只怕伺候不好,您看,要不要換一個?」
「媽媽,妳只要老實回答我,她當真是妳錦雀樓的姑娘?」
少年端起琥珀酒杯,看了看杯內深紅色的液體,輕啜一口,眼角的餘光將老鴇和那女子對視一幕盡收眼底。
「呵呵呵,公子,在錦雀樓裡出現的姑娘自然是錦雀樓裡的人!」老鴇拍著胸部保證。
這話猶如一顆石子投在少年俊美無儔的臉上,隨即便蕩漾起一波又一波的笑,「啊哈哈哈,如此就好辦了!」
話音未落,握著鞭子的手力道一收,黃衣女子便跌入了他的懷裡,「那今晚就讓妳來服侍爺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非君不娶(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98 |
后宮小說 |
$ 198 |
羅曼史 |
$ 198 |
言情小說 |
$ 213 |
后宮小說 |
$ 225 |
華文羅曼史 |
$ 22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非君不娶(上)
十一顏 繼《后來居上》《妃常神探》後,再度穿越古今,勇敢追愛
這不可能!這不合理!這太不可思議了!
坐擁無數美姬,風流到令人髮指的少年王爺
竟然決定──為了「他」,捨棄一整片森林!
不對,不對,這裡面肯定有不為人知的「內幕」……
雖說人不風流枉少年,但風流到享譽天下的程度,
會不會太誇張,太超過了!?
別懷疑,一提到敬王赫連駒,那可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啊!
據說他不僅攬盡天下美色,還好男風!
王府裡,姬妾成群也就算了,為了力捧京都第一名伶慕蓮生,
甚至不惜一擲千金,為其修築的「男寵巢」,堪比皇宮之殿!
這不,就連皇帝、太后都看不下去了,
一道聖旨將定北侯的妹妹樂正華濃指給了他,
就是希望,有正妻坐鎮,他可以收斂一些,
沒想到,踢到鐵板的赫連駒,不哭不鬧,乾脆直接逃!
只是他萬萬沒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皇帝早就下了密旨,要定北侯樂正夕將人逮了,
連同他的妹妹,一起護送回京拜堂完婚!
哪知,赫連駒一見到豐神俊朗的少年侯爺,竟做出驚人決定,
要為了「他」,捨棄一整片森林!
這不可能!這不合理!這太不可思議了!
這裡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內幕」……
作者簡介:
十一顏
宅女一枚,擅長寫古典言情、穿越言情小說。
平生無大志,最愛江南煙雨,回首斑駁時光,編織舊時回憶,靜默對待生命,願與時間平行。
出版作品:《夙締良緣》、《后來居上》、《妃常神探》、《非君不娶》。
章節試閱
楔子 午夜驚夢
「哥,我好累!我堅持不住了!」
漫漫的海域,沒有船隻,沒有燈火,唯有兩個約莫只有十來歲的孩子在海水裡掙扎。
沒有可以讓人視線變得清晰的色彩,只有一片磨人心志的漆黑。
海水冰冷刺骨,兩個孩子唯有拼命的向前游去,可是,前方那隱隱約約的小島,彷彿可望而不可即!
「柔兒,不要放棄!永遠都不要放棄!不要怕,有哥在!」
然而兩個身處大海的孩子,感覺到了死亡在降臨,彷彿整個天下只剩下他們兩人。
天上沒有明月,沒有星光,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只有無窮無盡,蔓延不止的黑!
被喚為柔兒的孩子意識已...
「哥,我好累!我堅持不住了!」
漫漫的海域,沒有船隻,沒有燈火,唯有兩個約莫只有十來歲的孩子在海水裡掙扎。
沒有可以讓人視線變得清晰的色彩,只有一片磨人心志的漆黑。
海水冰冷刺骨,兩個孩子唯有拼命的向前游去,可是,前方那隱隱約約的小島,彷彿可望而不可即!
「柔兒,不要放棄!永遠都不要放棄!不要怕,有哥在!」
然而兩個身處大海的孩子,感覺到了死亡在降臨,彷彿整個天下只剩下他們兩人。
天上沒有明月,沒有星光,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只有無窮無盡,蔓延不止的黑!
被喚為柔兒的孩子意識已...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楔子 午夜驚夢
第一章 無恥之徒
第二章 自食惡果
第三章 麻煩人物
第四章 斷腸百草
第五章 福壽天齊
第六章 會是誰?
第七章 訂下賭約
第八章 狡猾蒼狼
第九章 攻心之術
第十章 她亦是他
第十一章 已然動心
第十二章 心結難解
第十三章 發下重誓
第十四章 洞房花燭
第十五章 甘願沉淪
第十六章 處心積慮
第十七章 迎娶牌位
第十八章 揪出真凶
第十九章 驚人真相
第二十章 以命抵命
第二十一章 煩惱依舊
第二十二章 勇敢追愛
第一章 無恥之徒
第二章 自食惡果
第三章 麻煩人物
第四章 斷腸百草
第五章 福壽天齊
第六章 會是誰?
第七章 訂下賭約
第八章 狡猾蒼狼
第九章 攻心之術
第十章 她亦是他
第十一章 已然動心
第十二章 心結難解
第十三章 發下重誓
第十四章 洞房花燭
第十五章 甘願沉淪
第十六章 處心積慮
第十七章 迎娶牌位
第十八章 揪出真凶
第十九章 驚人真相
第二十章 以命抵命
第二十一章 煩惱依舊
第二十二章 勇敢追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