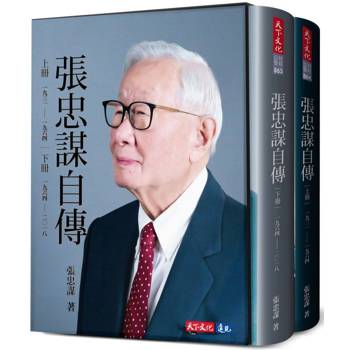一代奸臣首輔重生而來,人生目標大轉變
首要任務→規劃全新的養妻之路
唯一準則→妻子至上,以妻為尊
想要成為盛世賢臣的第一要件是──寵妻必須無極限!
曾經的超級渣男 如今的無敵暖男
薛庭儴,位極人臣,是大昌朝人人敬畏的首輔,
但最後卻落了個妻離子散,只有一個忠僕替他送終的下場。
原因無他,實在是他渣,太渣,霹靂無敵渣啊!
或許連老天爺都看不下去,讓他重新回到自己少年之時,
薛家還是窮得家徒四壁,家裡為了一個讀書名額打得頭破血流,
而王招兒還是他的童養媳,年紀比他大,還是個目不識丁的小村姑。
前世種種,他只能認定那是一場夢,
打從那個夢出現開始,他就在思索著為何會做那樣的夢?
現在他明白了,也許就是想讓他補足夢裡所有的不圓滿。
所以這一世,他決定要換一個活法。
首要任務就是──對她好,對她好,各種的對她好。
規劃全新的養妻之路,一切以妻為尊,讓她過上好日子。
夢裡那個靠招兒養活,卻一再嫌棄招兒的小男人已死,
如今的他,將成為能為招兒遮風擋雨的體貼大丈夫。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家養小首輔(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0 |
二手中文書 |
$ 175 |
華文羅曼史 |
$ 195 |
小說/文學 |
$ 198 |
羅曼史 |
$ 198 |
言情小說 |
$ 198 |
穿越文 |
$ 225 |
穿越文 |
$ 225 |
文學作品 |
$ 900 |
華文羅曼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家養小首輔(一)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假面的盛宴
有著各種奇思妙想卻又是個現實主義者的熟女一枚,性格天真而又爛漫,理想而又現實。
經常幻想各種稀奇古怪的故事,做著不切實際的白日夢,將之付諸筆下,發現著實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之後一發不可收拾。
假面的盛宴
有著各種奇思妙想卻又是個現實主義者的熟女一枚,性格天真而又爛漫,理想而又現實。
經常幻想各種稀奇古怪的故事,做著不切實際的白日夢,將之付諸筆下,發現著實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之後一發不可收拾。
|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