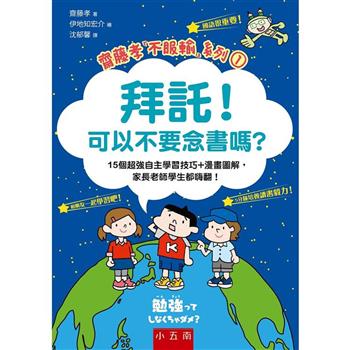第一章 勇猛妾室
白幡高直豎,廡房結靈花。
安徽宣州,陳家三房靜悄悄地辦著一場喪事。
靜悄悄,「靜」在人少,「悄悄」在不敢大膽聲張。
人自然是少,大半陳家人都去了前院哀悼──陳家唯一在朝為官的大房大爺也死了。
「賀小娘連死都不湊巧!」後院三房外廊,張婆子捏了把從前院順來的南瓜子,邊嗑邊感嘆,「大爺前夜嚥的氣,賀小娘昨兒閉的眼,三爺一早備下的橡木棺材壓根兒沒用上。」一頓,呶呶嘴,意在東南角,「被三太太生生摁下來了,說一個小妾入殮的風光蓋過朝上做官的爺們兒,腦袋打了鐵的人才會這麼做!」
張婆子說得那叫一個眉飛色舞,澄澈光暈下,嘴裡不斷噴射出幾道綿長的水霧拋物線。
拱柱後立著的賀顯金翻了個白眼,避開了這無差別物理攻擊。
廊下梳雙平髻的小丫鬟聽了好奇不已,「照您這麼說,要是賀小娘錯開時間死,豈不是能風光大葬了!」
「豈止風光大葬,我聽說三爺甚至在墓碑上刻了自己的名字,等百年後要和賀小娘合葬呢!」
「還得是張媽,啥都知道!」
張婆子被奉承得通體舒暢,分了一把瓜子給她,「我跟妳說,那棺材裡,賀小娘手裡攥著的和田玉,值這個數!」說著把手一抬,亮出五根肥胖的手指。
「五兩銀子?」小丫鬟嗑起瓜子猜測。
「沒見識!」張婆子順手一巴掌拍在小丫鬟頭上,「是五十兩!三爺一個月的花銷!」
「哇!賀小娘真是好福氣!」
這早死的福氣給妳要不要?賀顯金撇撇嘴,動了動手中的攢盒,內裡四色碟子碰撞在一起發出清脆的聲響。
張婆子偏過頭,見是賀顯金,拿瓜子的手一滯,隨後露出諂媚笑臉,「金姐兒可憐見的,快去看看妳娘吧!」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正好三爺也在,趁爺們兒正傷心,趕緊把自個兒的事定下來!」
張婆子再看四下無人,好心提醒她,「有些事逾時不候,妳身邊伺候的那四個丫頭一早就托我另找差事了!」
賀顯金低頭理了理攢盒,再抬頭,臉上掛著恰當的悲和敬,「多謝張媽疼我。」說完提著攢盒頭也不回地往裡走。
少女戴孝最是俏,白白的麻紗,小巧的白花,哭紅的鼻頭和微腫的眼睛,再加上侍疾數月蹉跎出的纖細弱瘦的身姿。
張婆子看著賀顯金的背影,瞇了瞇眼,目光渾濁,「妳別說,金姐兒比她娘還勾人。」
張婆子這話含在喉頭呢喃,小丫鬟沒聽清,疑惑的「啊」一聲。
張婆子回過神笑著搖頭,「我是說,金姐兒指不定福氣更好。」
被三太太隨便嫁到哪家,當個福氣更好的小娘。
也只能這樣了,女人嘛,能幹啥?特別是賀顯金,主不主,僕不僕的,甚至還不如她們呢!
她們就算是下人,也是三書六禮,明媒正娶的,毛了急了,還能給當家的一頓罵,這些當小娘的敢嗎?
賀顯金提著攢盒繞進靈堂,一眼就瞅見蔫頭耷腦,跪在棺材前的陳家三爺。
「您先起來坐坐吧!」賀顯金平靜地打開攢盒,依次拿了四碟糕點擺在鼓腿彭牙四方桌上,「您跪了兩天了,飯沒吃,覺沒睡,太太記掛您,特意叫我去她院子拿了糕點過來。」
陳三爺一聽,猛抬頭,氣得目眥欲裂,「她叫妳去幹麼!艾娘都死了,她還想做什麼?」
陳三爺滿臉通紅,手撐在膝蓋上,顫顫巍巍地起身,一把將桌子上的盤子掀翻,「叫她少管漪院的事!」
盤子砸地上,發出乒乒乓乓的聲響,倒沒碎,只是糕點摔了個粉爛,肯定是不能吃了,真是可惜了。
賀顯金想起三太太說的話──
「前頭大爺擺靈悼念,闔府上下誰敢不去?」
「就他是個癡情種?就他是個梁山伯?」
「妳娘的死,也不是一日兩日間攢下的果,纏纏綿綿病了好幾年,誰心裡都是有準備的。」
「妳若是個好孩子,真心心疼三爺,就叫三爺換身衣服,抹把臉,趕緊去前院跪著哭一哭他那英年早逝的大哥!」
賀顯金再看一眼雙目赤紅的陳三爺──吼得中氣十足,精神頭還好,還能哭。
內心評估完,賀顯金順手遞了把小杌凳在陳三爺身後,「三太太沒想做什麼,也沒對我做什麼,您先坐。」
小姑娘神色淡淡的,瞧不出喜怒,只有紅紅的鼻頭洩露了她喪母的哀痛。
他痛,顯金只會比他更痛。
他死了女人,顯金死了媽啊!
這世上,如今只有他和顯金是真心難過。
陳三爺癟癟嘴,眼裡一下子湧出淚,一下子頹唐地坐在小杌凳上,「妳娘她死了!」
賀顯金點點頭,「阿娘死時,我就在她身邊。」
「她再也回不來了!」
賀顯金再點頭,「每年清明您可以去給她上香,若想她了,也能去墳前陪她說說話。」
「我再也握不住她的手了!」
賀顯金還是點頭,「人死了,陰陽兩隔,入土為安,自然勿擾亡者清淨。」
陳三爺滯了滯,陡然號啕大哭,「可我想她,我好想她的啊!再沒有人真正覺得我好了!」
愛之深,思之切,對亡者的想念,總是難以輕易消退。當時間夠久到你以為你已經忘記她,忘記她的逝去帶給你的悲痛時,突然出現的她喜愛的花,她熱愛的食物,她時常翻閱的書,會像把利劍再次刺穿你的胸膛,這才讓你痛徹心扉。
賀顯金等待陳三爺慢慢平靜。
棺前的香燃盡,靈堂裡的哭聲終於漸漸弱了下來。
「比起看到您痛不欲生,阿娘或許更願意看到您好好過日子,看到您好好吃飯,好好睡覺。」賀顯金聲音輕輕的,「您可以為她哭泣,但只能哭三日。三日之後,就把阿娘的箱籠收拾好,您若願意就好好封存,若不願意就埋進土裡,陪著她去下一世。看到您衣食無憂,喜有所好,愛有所依。看到您一生瀟灑,不為困苦所拘。甚至看到您兒女成群,膝下稚童可愛,盡享天倫。」
陳三爺哭得雙眼腫成一條縫,「這些都是妳娘告訴妳的?」
賀顯金抿抿唇,輕輕點了點頭。
這些不是賀小娘囑咐她的,是她死時,對病床前那群至親至愛之人,唯一所願。
賀顯金死了,準確的說,她死過,是過去式。
人死了,最後消失的是聽覺,賀顯金以親身經歷證明,這個說法是對的。
在她眼前漆黑一片,意識快要消散時,她耳邊全是一片哭聲。
上輩子,她活了二十四年,至少有十年都在病床上。
先天孱弱的心臟讓她不能大喜大悲,不能劇烈活動,甚至不能像正常人一樣的生活,她的人生充滿了小心翼翼與意外事故。
感恩家裡充足的經濟實力,幫助她一路避開意外與事故,努力地活下去,在活下去的基礎上讀書、升學,甚至成功拿到企業管理學士學位,進入家族企業從基層做起,慢慢累積經驗。
她以為她能一直小心翼翼地活下去,卻倒在即將跨入二十五歲的前夜。
親人與朋友的哭聲交織在一起,賀顯金卻能精準分辨出媽媽的聲音。
撕心裂肺,卻無力回天。
媽媽沒事的……這是好事……媽媽……
賀顯金很想安慰媽媽,努力張嘴,渾身卻像被混沌細密的線纏繞住。
耳邊的哭聲一點點弱了下來。
大家再見,小金走了。
賀顯金終於什麼也聽不見了。
當賀顯金再睜眼時,就變成了渾身濕漉漉的賀顯金。
大魏的賀顯金,宣州的賀顯金。
造紙世家,陳家三房的如今十五歲的賀顯金。
同名同姓同字,但截然不同的賀顯金。
這個賀顯金身體健康,通身無病,但有災。
這具身體的原主是因落水溺斃,一命嗚呼了,被她這抹剛死的,異時空的遊魂莫名其妙接替了身體。
作為一個臥病在床,常年混跡於二次元的新青年,她異常迅速地接受了借屍還魂,穿越重生等離奇事件的發生,並且立刻投入到新身分的摸索探查工作。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
原主賀顯金,身世是有點小曲折的──她姓賀,但負責她吃喝拉撒的人家姓陳,這姓陳的主家是她娘的第二任郎君,她娘是這陳三郎君的寵妾,而她是她娘和前夫的種。
簡而言之,她是個拖油瓶,而且是依附著妾室生存的,不那麼名正言順的拖油瓶。
賀顯金咋舌,在封建時代二嫁,還帶上與前任的孩子,她娘真是個勇猛的妾室。
當賀顯金認真打量自己金碧輝煌的寢室和貼身侍候的四個丫鬟後,不禁再度感嘆,她娘真他娘的是個戰鬥力爆棚的妾室啊!
她一個拖油瓶物質條件這麼好,真的合理嗎?
只可惜賀顯金來的時候,賀小娘已經纏綿病榻好些年了,而原主的落水加速了賀小娘的病程──賀顯金借屍還魂後的第五日,賀小娘最終撒手人寰。
風動窗櫺,嘎吱嘎吱作響。
賀顯金思緒緩慢回轉,目光輕輕落在陳三爺臉上。
每一個勇猛妾室的背後,都有個戀愛腦的男人。
陳三爺確實是個戀愛腦,這個認知,是整個陳家的共識。
陳家造紙起家,現已有百年。
如今的大魏朝雖不存在於賀顯金有關封建時代的任何認知,但無論是風土人情、地域劃分還是文化背景、統治體系都留有宋明清時期的影子。
許多熟悉的地名和物件,讓賀顯金代入起來不算困難。
宣紙宣紙,其實就是宣州出產的紙張,而在宣州這個地界,陳家又算排得上號的紙商。
賀顯金剛來前幾天就拿著陳三爺三房的丙字牌,在陳家內院裡裡外外走了一圈。
光是內院就有四進,分作五個院子。
話事人陳老太太獨住篦麻堂,在京做官的陳大爺、陳家長房的選草堂,二房的漿造堂,三房的撈紙堂,另有一個空院子掛了晴曬堂的牌子。
一聽就是造紙的。
篦麻、選草、漿造、撈紙和晴曬,組成了一張張肌清玉骨的紙,也組成了闔家主僕七十六口的宣州陳氏。
簡單來說,陳家就是宣州做得不錯的本地民營企業。
老太太內外一把抓,老大負責開拓仕途市場,老二跟著老太太打理生意,等待著繼承陳氏紙業。
至於老三嘛……小兒子基本都是拖後腿的,陳老三也不例外。
陳三爺,名曰陳敷,六歲啟蒙,現如今三十有六,文不成武不就,十八娶隔壁江南道織造行業的孫家嫡幼女為妻,本應就此過上鬥雞走狗的富二代草包生活。
奈何在二十七歲的高齡,遇上了碰到災荒,看似柔弱如菟絲花的賀艾娘,和小拖油瓶賀顯金。
陳老三的戀愛腦開了竅,頂著壓力固執地納了二嫁的賀艾娘為妾,從此就跟魔怔似的,但凡陳三太太孫氏有的,管他龍肝鳳膽,他一定要給賀艾娘弄到手,就算被母親指著鼻子罵也毫不退讓。
賀艾娘纖細敏感,又體弱多病,陳老三便日日不離身,自掏腰包,人參燕窩如流水般地往賀小娘房裡送。
不僅送,還要敲鑼打鼓地讓所有人都知道。
讓所有人都羡慕,讓所有人都看到他陳老三雖然文不成武不就,但他會寵人,會疼人,不是幹啥啥不行!
三房內院都羡慕賀艾娘「盛寵」加身,賀顯金卻一邊打聽,一邊在陳老三戀愛腦的標籤前默默貼上「叛逆」與「幼稚」。
賀顯金東拼西湊出,陳老三和原主她娘,大概就是中二病叛逆草包富二代與小白花柔弱女主的故事。
賀顯金的目光從戀愛腦陳老三的臉上,移到棺材前的牌位上,上面刻著「吾妻賀艾娘之位」。
吾妻,吾妻!賀顯金輕輕嘆了口氣,陳老三真正的妻,能忍了這口氣?
恐怕早就不想忍了。
正是原主莫名其妙的落水,才導致賀小娘病情突然惡化的啊!
陳敷又跪著哭了兩場,哭到膝蓋腫痛才扶著長隨站起來,有氣無力地囑託賀顯金,「妳給妳娘守夜吧,明兒第三天得出殯了,我必須跟去看著。」
賀顯金看了眼漸落的天色,輕聲勸道:「您記得去前院給大老爺上炷香。」
陳敷癟癟嘴角,有些不屑的樣子。
既沒說去也沒說不去,只朝賀顯金擺擺手,半邊身子靠在長隨身上一瘸一拐往外走。
賀顯金決定先去上個廁所再回來守夜,只是剛從茅房裡出來,卻被陡然竄出的黑影嚇了一大跳。
「小金妹妹!」
聲音是個男子!賀顯金有點怕。
這大魏,若是比照程朱理學的明朝,她私會男子,可是會被打死的!
賀顯金下意識向後退,那影子卻迫切地追過來,面部暴露在光裡。
是這幾日沒見過的男子,十七、八歲的樣子,手長腳長,臉上鬍鬚一茬青過一茬,就是個在抽條的高中生。
賀顯金心裡鬆了口氣,不那麼怕了。
可她不知道這是誰,不敢隨意搭話,低了頭又避開半步,「嗯」了一聲,就要往裡走。
男子見賀顯金要走,急切地道:「小金妹妹妳莫怕,我沒有惡意,只是想和妳道個歉,在湖邊是我孟浪了,妳落水後可沒事?」
賀顯金腳下一滯,就是你這個瘟傷讓原主落的水!?
高中生見賀顯金躲避的步子停了,便知自己這個歉道對了,長呼一口氣,抓緊向前逼近一步。
白燈籠掛得低低的,白光透過微黃的麻布絹紙照射在少女的臉上。
深茶色的瞳孔配上狹長的鳳眼,小巧挺立的鼻,還有像花瓣一樣的嘴,像在邀請他。
男子心頭一悸,緊跟著喉頭微動。
她太漂亮了,賀小娘已足夠漂亮,但賀顯金更漂亮。
賀小娘的美是凡間唾手可得的戰利品,賀顯金的美卻是來自地下十八層地獄的考驗,勾引人佔有她,揉碎她,欺辱她。
高中生刻意壓低聲音,聽同窗說,男人要低聲沉吟,要把鉤子放在話裡,沒有女人聽了不動心的。
「小金妹妹,妳聽我說,上回在湖邊我說的話是真的。我今年下場鄉試,我娘答應我要是鄉試過了,就准我一件事!」
高中生在變聲末期,聲音本來就難聽,壓低嗓門說話,就像喉嚨卡了口痰似的,聽著都覺得噁心!
「你若無事,我要去給我娘續香了。」賀顯金本來就煩,埋頭就往裡走。
高中生微微一愣,她似乎哪裡不一樣了,但他來不及細想,伸手擋住賀顯金的去路,自顧自地把後話說出,「等我過了鄉試,我就求我娘把妳給我!爹喜歡賀小娘,也同樣愛護妳,妳留在陳家,正好他也能繼續照拂妳。」
賀顯金眉頭一皺,不可思議地抬頭看向高中生,「你是三太太的兒子陳四郎?」
這是賀顯金打聽出來的,陳三爺和孫氏有三子一女,最小的兒子就是這個年紀。
此話一出,賀顯金頓覺不妥,立刻改了口,「你這樣的身分……把我給你,是什麼意思?」
少女說得坦蕩又自然,陳四郎卻因她的直接有些惱羞成怒,「就是……當我房裡的人。」
房你個頭!賀顯金本想忍了,畢竟她如今處境不明朗,看陳三爺也絕不是個靠譜的。
按道理,她忍下來比發洩出來明智,但是……去他娘的明智。
她在病床上躺了十來年,為了活下去,不敢生氣,不敢高興,七情六慾快被絕完了。
她與太監唯一的不同是,太監絕情慾用的物理手段,她則是生物手段。
如今這具身體卻健康得像頭牛!
賀顯金揚眉,「什麼叫當你房裡人?無名無分住到你院子去?」
「會有名分!等我過了鄉試,就抬妳做小娘!」
「那你要是一直沒過鄉試,我就一直免費陪你睡覺?」
陳四郎差點兒被口水嗆到。
「你跟我來。」賀顯金領他走進靈堂,拿了三炷香遞給陳四郎,「來吧,在我娘靈前說出你的願望,看她應是不應?」只要你有這個臉。
三支長香直衝衝地懟到陳四郎的下巴,打了他一個猝不及防。
「去啊!」賀顯金聲音清冷地催促,三支長香快要杵進陳四郎鼻孔了。
陳四郎條件反射地趔趄著往後退了一步,略帶驚慌地抬頭,卻見賀顯金抬頭挺胸地站著,眼神深暗,透出他不太熟悉的情緒。
她,她是在蔑視他嗎?陳四郎被這個認知驚到了。
賀小娘柔弱可憐,這個女兒向來沉默溫馴,非常有寄人籬下的認知。
見到他,要麼退避三舍,要麼忍耐安靜。
就連上次,他企圖趁夜黑一親芳澤,也只是把賀顯金逼得踩空落了水。
他被娘惡狠狠地揪著耳朵罵了半個時辰,後來又聽說賀顯金病了兩日,緊跟著賀小娘就駕鶴歸西了。
不是因為他吧!?陳四郎怕得要死,躲了幾天,就怕賀顯金跟他爹告狀,等到現在他都沒等到他爹來找他,便大著膽子摸進了後院。
賀小娘死了,沒有人保護賀顯金了!
況且離鄉人賤,誰能為她做主?
當初賀小娘來陳家前,還在逃災荒!一母一女渾身上下就只有兩套破布衣服,連名籍都被人搶了!
葡萄成熟了,可以摘了。
陳四郎膽子陡然壯了三分,將賀顯金手上的香一把拂掉,「賀小娘不過是妾,是僕!沒有我給她上香的道理!」然後不好意思地一笑,「不過小金妹妹成了我的人,她也算我半個丈母娘,我給她磕個頭、上個香也是無妨的。」
陳四郎逼近,手搭在賀顯金腰間,「小金妹妹別怕,我必不負妳。」
像一碗油潑到腰上,賀顯金看了眼腰,又看了眼陳四郎,笑了笑,抬眼高喚了一聲,「三爺,您又回來了!」
陳四郎「刷」地將手抽回,慌忙回頭看。
沒人!鬆了口大氣。
剛轉頭過來,卻感到右手火辣辣的疼!
不知何時,賀顯金將白燭落下的蠟油盡數倒在了陳四郎的右手上。
蠟燭油貼肉燙!陳四郎上竄下跳甩右手,嘴裡哇哇亂叫。
賀顯金將裝熱油的碗「啪」地摜到地上,瞬間四分五裂,然後一把捏住陳四郎的下巴,踮起腳,惡狠狠地盯著他,一字一句道:「你給我記住,你再敢碰我,你右手碰我,我廢你右手;你左手碰我,我剁你左手。我一條爛命,換你錦繡前程,我賺了!」
賀顯金表情太過於凶狠。
原先花瓣般誘人的唇,變成了妖怪吃人的嘴。
原先狹長上挑勾人的眼,變成了惡鬼索命的劍。
面冷心狠──陳四郎腦海中閃過這四個字,渾身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哆嗦。
「聽清楚了嗎!」
賀顯金手指使勁,眼看陳四郎的臉上多了四指掌印。
陳四郎慌不迭地點頭。
賀顯金手一鬆,向後背手,偷偷活動微微發抖的關節。
「百福,水!涼水!給我找水!」此情此景,陳四郎也不在乎什麼低音炮了,齜牙咧嘴地往外跑著找涼水。
賀顯金一個眼神都不想多給,隔了一會兒,廊外哇哇亂叫的聲音消失殆盡。
躲在白幔後,將這一切盡收眼底的張婆子手裡摳著攢盒,渾身止不住發抖。
她看到什麼?她看到賀顯金那個拖油瓶,潑了陳四郎一碗滾燙的蠟油!
那蠟油遇冷就凝固,就像貼了一層甩不掉的滾燙鍋巴,四郎的右手背紅得像煮熟的蝦殼!
那可是主子,還是三太太最喜歡的小兒子,而且是寫字讀書的右手!
張婆子的手抖抖抖,手裡的攢盒「磕磕磕」。
賀顯金凌厲的眼神橫掃過去。
張婆子膝蓋一軟,差點兒跪在地上,「金……金姐兒!」
賀顯金輕輕點點頭,「您給我娘送四色攢盒?」
「是是是!」張婆子慌忙點頭,「一天了,供奉的攢盒該換了!」
賀顯金朝她一笑,「多謝張媽疼我。」
張婆子快速將攢盒放下,一邊往後逃,一邊連連擺手,「不敢不敢!分內分內!」
快要逃出生天,張婆子咬了咬牙,還是半側身探了個頭道:「金姐兒,剛剛的事,妳最好趕緊知會三爺一聲,服個軟,哭一哭,三爺吃這套。別等到三太太興師問罪,到時候一切就都晚了!」
賀顯金有些驚訝挑了挑眉。
張婆子趕忙加了句,「妳也是我們看著長大的,妳小時候,我還幫妳洗過尿床單呢!」
哦,原來是一張尿床單結下的友誼。
賀顯金移開眼,沒說話。
沉默讓張婆子後背莫名起了一層冷汗。
「他不會聲張的。」在張婆子以為賀顯金不會說話時,賀顯金輕聲打破沉默,「前院大爺正在擺靈,他偷偷潛入後院女眷住所,被當家的知道了,他沒好果子吃。」緊跟著話鋒一轉,「不過,零碎收拾肯定是少不了的。您若真疼我,就幫我在外頭買十張黃麻紙,還有墨。」說著,塞了半吊錢給張婆子。
陳家啥沒有,紙還能沒有?
隨便到哪個門房,要也能要到幾張紙,況且還是最便宜的黃麻紙。
這半吊錢純屬送給她的。
張婆子搓搓手,沒敢拿,「還能要妳錢?妳娘剛死,做什麼都不容易,多留點錢傍身吧!」
賀顯金想了想又道:「那咱們有好寫的筆嗎?筆尖硬硬的那種。」
這個專業就不對口了,筆,這個生意,是隔壁王家的。
張婆子搖搖頭。
賀顯金前世在博物館裡見過竹管筆,記不得是哪個朝代挖出來的,估摸不是這個朝代。
「那煩您幫忙找一小截竹子尖頭,我有用。」
張婆子想問有啥用,又想到陳四郎被燙得通紅的手背,趕緊噤口,點頭應下。
不到一刻,張婆子便拿著東西回來了。
武力值這種東西吧,有時候就是簡單又好用。
當所有人都離開,整個靈堂安靜得連蠟燭燃燒都有了具象的聲音。
管他白日人聲鼎沸,來往如織,面子情了後,終究塵歸塵、土歸土,分道揚鑣,再無關聯。
前世在病床上,她的目標是活著。
那現在呢?
在這個男人出一個月的花銷給女人買鎮棺玉,就被人交口稱贊的荒誕時代。
在這個「我是主,妳是僕,連上香都沒妳份兒」的奇葩時代。
在這個「妳好好求求三爺,趁他心軟把自己的事定了」的狗屁時代。
她的目標是什麼?
她的人生、她的價值、她的未來,都由別人決定,可誰也不能決定她腦子裡面想什麼。
賀顯金跪在棺材前,眸光裡如有火苗跳動。
靈堂的燭火,一夜未滅。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一紙千金(一)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一紙千金(一)
董無淵 繼《妙手生香》後,穿越另類行商,開啟全新征程
現代暴發戶病嬌女成了古代妾室的拖油瓶
主不主,僕不僕,連個丫鬟都不如!?
與其任人作踐,不如另闢蹊徑,創造價值,這一世她要活出名堂!
★★編輯強推,必讀理由★★
有穿越重來一世的機會,誰都想要好好活著,不會坐以待斃。書中女主也是,她穿越到造紙世家,身分雖然低賤,對紙更是一無所知,但她點子新,有創意,又肯努力學習,是個極為聰慧的女子,圓滑卻不世故,善良卻不縱容。看她從一家小鋪子開始,慢慢殺出一片天地,真的很過癮!而且文風歡快中帶著細膩,主角配角都是戲精,閱讀起來一點不枯燥,接地氣又有趣。
賀顯金怎麼也沒想到,當她再次睜開眼,
竟成了大魏宣州造紙世家陳家三房的賀顯金!
作為一個常年臥病在床,混跡於二次元的現代青年,
異常迅速地接受了借屍還魂,穿越重生的離奇事件。
只是這身分──實在是太尷尬,太悲催了啊!
親娘是陳家三爺陳敷的寵妾,自己則是前任留下來的拖油瓶!
在眾人眼中,她主不主,僕不僕,別說庶女,
連個丫鬟都不如,甚至是父不詳的奸生子!
能依靠的親娘已離世,胸無大志的戀愛腦繼父只會啃老,
三房太太孫氏視她為眼中釘,除之而後快,
繼兄把她當成送到嘴邊的肉,哪有不吃的道理?
前世因先心病,躺在病床上,唯一的目標就是活著,
重活一世,她豈能辜負,繼續躺平,
她的價值由她自己創造,她的未來由她自己決定,
這一世她要活出美好,活出名堂!
作者簡介:
董無淵
川蜀人士,自小喜舞文弄墨,又喜述事陳情,永懷初衷寫下文字,希望芸芸看客可在故事中尋找快樂。
出版作品:《妙手生香》、《一紙千金》。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勇猛妾室
白幡高直豎,廡房結靈花。
安徽宣州,陳家三房靜悄悄地辦著一場喪事。
靜悄悄,「靜」在人少,「悄悄」在不敢大膽聲張。
人自然是少,大半陳家人都去了前院哀悼──陳家唯一在朝為官的大房大爺也死了。
「賀小娘連死都不湊巧!」後院三房外廊,張婆子捏了把從前院順來的南瓜子,邊嗑邊感嘆,「大爺前夜嚥的氣,賀小娘昨兒閉的眼,三爺一早備下的橡木棺材壓根兒沒用上。」一頓,呶呶嘴,意在東南角,「被三太太生生摁下來了,說一個小妾入殮的風光蓋過朝上做官的爺們兒,腦袋打了鐵的人才會這麼做!」
張婆子說得那...
白幡高直豎,廡房結靈花。
安徽宣州,陳家三房靜悄悄地辦著一場喪事。
靜悄悄,「靜」在人少,「悄悄」在不敢大膽聲張。
人自然是少,大半陳家人都去了前院哀悼──陳家唯一在朝為官的大房大爺也死了。
「賀小娘連死都不湊巧!」後院三房外廊,張婆子捏了把從前院順來的南瓜子,邊嗑邊感嘆,「大爺前夜嚥的氣,賀小娘昨兒閉的眼,三爺一早備下的橡木棺材壓根兒沒用上。」一頓,呶呶嘴,意在東南角,「被三太太生生摁下來了,說一個小妾入殮的風光蓋過朝上做官的爺們兒,腦袋打了鐵的人才會這麼做!」
張婆子說得那...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勇猛妾室
第二章 伏龍鳳雛
第三章 展現價值
第四章 無人敢欺
第五章 這心太黑
第六章 連本帶利
第七章 畫個大餅
第八章 雕蟲小技
第九章 八鴨秀才
第十章 夜探民居
第十一章 一場交易
第十二章 心驚膽顫
第十三章 值得敬佩
第十四章 升職加薪
第十五章 臉皮要厚
第十六章 另闢蹊徑
第十七章 延聘名師
第二章 伏龍鳳雛
第三章 展現價值
第四章 無人敢欺
第五章 這心太黑
第六章 連本帶利
第七章 畫個大餅
第八章 雕蟲小技
第九章 八鴨秀才
第十章 夜探民居
第十一章 一場交易
第十二章 心驚膽顫
第十三章 值得敬佩
第十四章 升職加薪
第十五章 臉皮要厚
第十六章 另闢蹊徑
第十七章 延聘名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