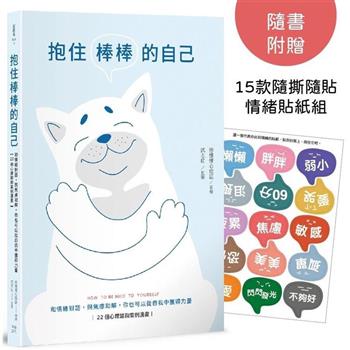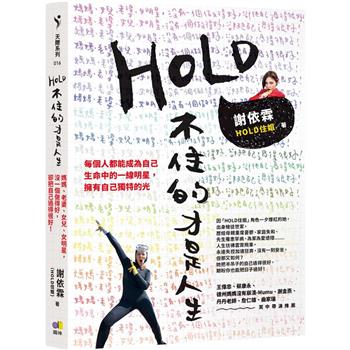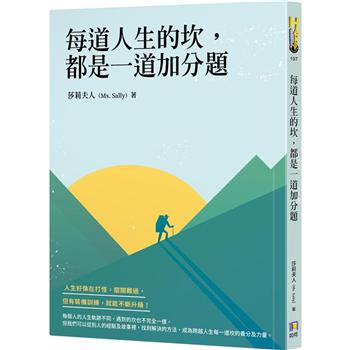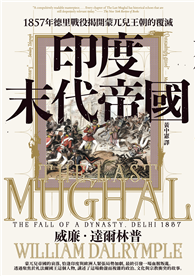回憶中的一夜
當時,我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在丸之內的某棟辦公大樓裡的貿易商──合資公司S‧K商會擔任辦事員。老實說,微薄的月薪只夠我自己花用。無可奈何,誰教我的家境不好,無法供我從W職校畢業後繼續升學呢?
我從二十一歲開始上班,到那年春天正好滿四年。我負責核對部分會計帳簿,從早到晚只需打算盤。而我雖僅職校畢業,卻熱愛小說、繪畫、戲劇及電影,自以為懂得藝術,因此遠比其他職員討厭這種機械性的工作。我的同事大多是光鮮亮麗、勇於嘗試且活在當下的人,不是每晚勤跑咖啡廳或舞廳,就是滿嘴的運動話題。喜歡幻想又內向的我雖然在公司裡待了四年,卻沒半個朋友,使得我的上班生活變得更為枯燥乏味。
然而,從半年前開始,我不再那麼厭惡每天早起上班了。因為當時十八歲的木崎初代進入了S‧K商會,擔任實習打字員。木崎初代是我打從出生以來便在心中描繪的理想女性,她的膚色是憂鬱的白色,卻沒有不健康的感覺;身軀像鯨骨般柔韌且富有彈性,卻不似阿拉伯馬那麼壯碩;白皙的額頭以女人而言稍嫌過高,左右不對稱的眉毛蘊含一股不可思議的魅力,一雙丹鳳眼帶有微妙的神祕色彩,不太高的鼻梁和不過薄的嘴唇點綴著下巴小巧的緊緻臉龐,人中比一般人狹窄,上唇微微向上翹起──其實這樣細細描寫,反倒不像初代了。不過,她大致上就是如此,雖然不符合一般美女的標準,對我而言卻充滿無比魅力。
內向的我苦無機會,整整半年都沒和她說上半句話。早上即使碰面,也是連個注目禮都沒有。(辦公室裡員工眾多,除非是工作上有交集或特別親近,否則沒有互道早安的習慣。)然而,某一天,我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勁,居然開口向她攀談。事後想想,這件事──不,連她進我們公司工作都是命運的安排。我指的並非她和我的戀情,而是當時向她攀談,導致日後經歷了促使我撰寫本書的駭人遭遇。
當時,木崎初代頂著似乎是她自己打理的、頭髮全往後梳的漂亮髮型,垂臉望著打字機,微微弓起穿著藤紫色制服的背,專注地敲著鍵盤。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HIGUCHI
仔細一看,信紙上排滿某人的姓氏,應該是「樋口」吧?看起來活像花紋一樣。
我本來想寒暄一句:「木崎小姐,妳真專心啊。」卻犯了內向之人的通病,臨陣慌了手腳,笨頭笨腦地用高八度的聲音叫她:
「樋口小姐。」
聞言,木崎初代轉向我,宛若在回應這道呼喚。
「什麼事?」
她一派鎮定,卻又像小學生一樣天真無邪地如此回答。對於被稱呼為「樋口」,她沒有絲毫疑問。我再度慌了手腳,莫非我誤以為她姓「木崎」?其實她只是打著自己的姓氏而已?這個疑惑讓我暫時忘了害羞,忍不住說出長一點的句子。
「妳是姓『樋口』嗎?我一直以為妳姓『木崎』。」
聞言,她猛省過來,眼眶微微泛紅地說:
「哎,我一時沒留意……我姓木崎沒錯。」
「那樋口是?」
妳的意中……話說到一半,我驚覺自己多言,連忙閉上嘴。
「沒什麼……」
木崎初代慌慌張張地把信紙從機器中抽出來,揉成一團。
我把這段無聊的對話寫下來是有理由的。這段對話不只是加深我們關係的契機,她所打的姓氏「樋口」,以及她被喚作樋口卻毫不遲疑地回應的事實裡,其實包含與故事核心相關的重大意義。
這篇故事的主題並非愛情,該寫的事情太多,沒有多餘的篇幅可以花在這上頭。因此,關於我和木崎初代的戀情進展,我僅概略敘述幾句。經過這段偶然的對話以後,我們雖然沒有相約,卻常一起踏上歸途。如此這般,電梯裡、辦公大樓到電車站的路上,以及搭上電車後,抵達她往巢鴨、我往早稻田的轉乘站前的短暫期間,成了我一天最開心的時光。不久,我們變得越來越大膽。有時候,我們會晚一點回家,前往公司附近的日比谷公園,坐在角落的長椅上閒談片刻;有時候,我們會在小川町的轉乘站下車,走進那一帶的老舊咖啡廳,各點一杯飲料。至於清純的我們鼓起莫大勇氣走進郊區的旅社,已經是近半年後的事。
過去我時常感到寂寞,木崎初代亦然。我們都不是勇於嘗試的現代人。可喜的是,如同她的容貌是我打從出生以來就在心中描繪的理想形象一般,我的外貌也是她有生以來便心嚮神往的。說句奇怪點的話,其實我對於自己的相貌小有自信。有個名叫諸戶道雄的人,同樣在這個故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畢業於醫科大學,在大學研究室裡從事某種奇妙的實驗。這個諸戶道雄打從還是醫學生,而我還是職校生時,就對我抱著真心實意的同性情愫。
無論外表或內在,他都是我所認識的人之中最為高貴的美男子。雖然我對他並沒有任何特殊感情,但是一想到自己居然能讓挑剔的他看上眼,我對自己的外貌便多了幾分自信。至於我和諸戶的關係,就留待之後的機會敘述吧。
總之,我和木崎初代在郊區旅社裡的第一個夜晚,至今仍令我難以忘懷。當時我們在一家咖啡廳,像私奔的情侶般多愁善感、自暴自棄。我喝了三杯喝不慣的威士忌,而初代也喝了兩杯甜甜的雞尾酒,兩人都滿臉通紅,醉意醺醺,因此站在旅社櫃台前時並不怎麼羞恥。我們被帶往的客房裡放了張大床,壁紙上遍布汙漬,看起來陰森森的。服務生把房門鑰匙和粗茶放在角落的桌上之後,默默地離去。這個時候,我們突然大驚失色,面面相覷。初代外表看來柔弱,其實內心十分堅強。然而,此時的她卻是醉意全消,臉色發青,失去血色的嘴唇不斷顫抖。
「妳害怕嗎?」
為了掩飾自己的恐懼,我如此輕聲說道。她默默閉上眼睛,微微地搖了搖頭。然而,不用說,我也知道她很害怕。
這真是既詭異又尷尬的場面,我們壓根兒沒料到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都深信自己可以處之泰然,就像世上的男男女女一樣享受最初的夜晚。然而,當時的我們根本沒有躺上床的勇氣,更沒有寬衣解帶、袒露相見的念頭。簡單地說,我們非常焦慮,連早已親過好幾次的嘴也沒親。當然,其他事更是完全沒做,只是並肩坐在床上,為了掩飾尷尬而生硬地擺動雙腳,沉默了將近一小時。
「欸,不如我們來聊聊天吧?我突然想說小時候的事。」
她用低沉清澈的嗓音說道,而我由於生理上過度焦慮,物極必反,心情反而舒坦了起來。
「嗯,好主意。」
我讚許她的慧黠,回答:
「談談妳的身世吧。」
她換了個輕鬆的姿勢,用清澈細膩的聲音道出兒時的奇妙回憶。我默默聆聽,好一陣子動也不動,專注於她的身世之中。她的聲音宛若搖籃曲,聽來相當悅耳。
在那之前與之後,我也斷斷續續地聽她提過幾次她的身世,但是從未像這次這般感觸良多。至今我仍然能夠鮮明地憶起她所說的一字一句,不過撰寫這篇故事用不著鉅細靡遺地記錄她的身世,因此我只節錄日後與這個故事有關的部分。
「以前也跟你說過,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出生、是誰家的孩子。現在的媽媽──你還沒見過她,我和她相依為命,工作就是為了養她──她對我這麼說:『初代,妳是我們夫妻年輕時在大阪一個叫川口的碼頭撿到、拉拔長大的。當時妳的手上拿著一個小包袱,在候船室的陰暗角落哭哭啼啼。我們打開包袱一看,裡頭有一本族譜,上頭應該是妳的祖先吧;還有一張紙,我們就是看了這張紙,才知道妳的名字叫初代。妳當時三歲。我們沒有孩子,認為妳是老天爺賜給我們的女兒,所以去警署辦了手續正式收養妳,把妳一點一滴地拉拔長大。所以妳也別見外,把我──當時我爸已經死了,只剩下我媽一個人──當成妳真正的媽媽。』聽了這番話,感覺就像在聽故事一樣,我其實一點也不難過,可是說來奇怪,我的眼淚卻不停掉下來。」
初代的養父在世時曾經多方調查那本族譜,費盡心力尋找她真正的父母。然而,族譜有些地方破損,上頭又只有祖先的名字、別號及諡號──從這一點看來,初代的家族應該是頗有地位的武士家系──完全沒有記載祖先隸屬於哪個藩、居住在哪個地方,因此養父也無能為力。
「都怪我太笨,三歲了還記不得爸媽的長相,才會被拋棄在那種人來人往的地方吧。不過,有兩件事我記得一清二楚,現在只要閉上眼,便會鮮明地浮現在黑暗之中。其中一件事,是我在某個陽光普照的海岸草地上和一個可愛的小寶寶玩耍。那個小寶寶真的好可愛,我想我大概是以大姊姊自居地照顧他吧。下方的大海蔚藍無比,遠遠地可望見另一頭有一片籠罩著紫色霧氣的陸地,看起來像頭牛在睡覺。我常想,或許那個小寶寶是我的親生弟弟或妹妹,沒有像我一樣被拋棄,現在仍然在某個地方和爸媽一起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每次這麼想,我的胸口便會緊緊揪起來,產生一種既懷念又悲傷的感覺。」
她凝視著遠方,宛若自言自語。而她的另一個兒時回憶則是──
「我在一座盡是岩石的小山山腰處看風景,不遠處有座別人家的大宅院,外圍是一道森嚴的土牆,看上去活像萬里長城。主屋的屋簷宛如大鵬展翅氣派,旁邊還有個白色的大倉庫,在陽光照耀下顯得格外鮮明。不過,除了這座宅院以外,附近沒有其他人家。宅院後頭同樣是蔚藍的大海,大海彼端依然是像頭牛在睡覺般景色朦朧的陸地。我想,那裡和我陪小寶寶玩耍的地方鐵定位於同一塊土地上。我夢過那個地方好幾次。在夢裡,我只要想著:『啊,又要去那裡了。』繼續往前走,就會走到那座岩山。如果我走遍日本各地,一定會發現景色和夢中一模一樣的土地,而那片土地就是我懷念的故鄉。」
「等等、等等。」此時,我打斷初代說道:「雖然我的畫技不高明,但是應該可以把妳夢裡的景色畫出來。要我試試嗎?」
「真的?那我描述得更詳細點。」
於是,我拿起桌上籃子裡的旅社信紙,用客房提供的筆,畫下她在岩山上望見的海岸景色。想當然耳,此時的我完全沒料到這個隨手塗鴉,日後將會發揮重大的效用。
「哇,太不可思議了,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見了我畫好的圖,初代開心地叫道。
「這張圖我可以留著嗎?」
我說道,把這張紙折得小小的,收進上衣口袋,像收藏情人的夢想。
接著,初代又訴說許多自她懂事以來的悲喜回憶,這部分便不多贅述。總之,我們共度了美夢般的初夜。當然,我們並未留宿旅社,而是在深夜各自踏上歸途。
異樣的戀情
我和木崎初代的感情日益深厚。過了一個月,我們在同一間旅社度過第二夜,關係已不似之前如同少年的夢境般純真。我先前往初代家拜會她慈祥的養母,不久,我和初代各自向母親表明心跡,而雙方的母親並未積極反對。只是我們太過年輕,結婚對於我們而言仍然遙不可及。
年少無知的我們學小孩打勾勾,稚氣地互贈禮物。我花了一個月的薪水,買了枚碧璽戒指──這是初代的生日石──送給她。某一天,我在日比谷公園的長椅上,用從電影中學來的手法將戒指套在她的手指上,而初代像小孩一樣開心(家境不好的她手指上沒有半枚戒指)。思考片刻之後,她一面打開從不離手的手提袋,一面說道「啊,我想到了」。
「你知道嗎?我剛才煩惱著該回送什麼才好。雖然買不起戒指,不過我有個好東西,就是之前跟你說過的,我那不知去向的爸媽留給我的唯一紀念品──族譜。我一直很珍惜這本族譜,出門時也放在手提袋裡隨身攜帶,這樣才能與我的祖先寸步不離。這是連繫我和千里之外的媽媽唯一的物品,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不願意讓它離手。不過,我沒有其他東西可以送給你,就把這本重要性僅次於性命的族譜交給你保管。你說,好不好?雖然只是沒有用處的廢紙,你還是要好好珍惜喔。」
說著,她從手提袋中拿出一本又舊又薄的布面族譜交給我。我接過族譜翻了翻,只見上頭用紅色線條串連著許多老派又威武的名字。
「這邊寫著樋口,對吧?你應該知道,就是我從前用打字機亂打,被你看見的姓氏。欸,其實我一直認為我真正的姓氏不是木崎,而是樋口,所以那時候你叫我樋口,我忍不住答腔了。」
她如此說道。
「別看這只是沒有用處的廢紙,從前可是有人開出高價收購呢!是我家附近的舊書店。大概是我媽說溜嘴,輾轉傳到書店老闆耳中。不過,無論價碼開得再高,我都婉拒。所以這並不是一文不值的東西。」
她又說了這番孩子氣的話。
換句話說,這就是我們的訂婚信物。
然而,不久後,我們遇上一點小麻煩。有個無論地位、財產或學識都遠勝於我的求婚者,突然出現在初代面前。他透過有力的媒人,鍥而不捨地向初代的母親提親。
初代從母親口中得知此事,是在我們交換信物的隔天。初代的母親告訴她,其實早在一個月前,媒人已經透過親戚的介紹登門提親。聞言,我大吃一驚。但最讓我驚訝的不是求婚者的條件遠勝於我,也不是初代的母親似乎比較中意對方,而是向初代求婚的正是和我有著奇妙關係的諸戶道雄。這股驚訝之情強烈得足以抵銷其他的驚訝及心痛。
要問我為何如此驚訝,我就得坦白說出一段有些難堪的往事了……。
在前文中我也曾略微提及,其實科學家諸戶道雄這幾年來都對我懷抱著某種不可思議的情愫。至於我呢?當然,我無法理解這種情愫,但基於他過人的學識、才氣橫溢的言行舉止及充滿異樣魅力的容貌,我並未感到不快。只要他的行為沒有逾矩,我都把他的好意當成單純的友情,不吝接受。
在我就讀職校四年級時,雖然老家與學校同樣位於東京,但一方面是出於家庭因素,而絕大部分是出於幼稚的好奇心,我在神田一棟名叫初音館的公寓租了間雅房。我就是在那兒認識同為房客的諸戶。我們年紀相差六歲,當時我十七歲、諸戶二十三歲。他是個大學生,又是出了名的才子,因此每當他提出邀約,我總是抱著尊敬之心欣然接受。
我得知諸戶的感情,是在相識的兩個月後,但並非從他的口中直接得知,而是聽他的朋友閒聊時發現的。有人四處說:「諸戶和蓑浦之間有曖昧。」之後我便仔細留意,發現諸戶唯有在面對我時,白皙的臉上才會流露出些微的羞赧之情。當時我只是個孩子,學校裡也有人抱著好玩的心態從事同樣行為,因此當我想像諸戶的心情時,不禁獨自紅了臉。那並不是一種十分不快的感覺。
我想起他常邀我去澡堂,在澡堂裡也曾替彼此洗背,而他總是替我的全身上下抹滿肥皂泡沫,活像母親替幼兒洗澡那般仔細。起初我以為他是單純出於好心,後來得知他的心意,仍是刻意讓他這麼做。這麼點小事不至於傷害我的自尊心。
散步時,我們也會拉手或搭肩,這也是我刻意而為的。他的指尖有時會帶著強烈的熱情緊握我的手指,我總是裝作不以為意地任他握住,其實心跳略微加速。說歸說,我從來不曾回握他的手。
除了肢體上的行為,他在其他方面當然亦對我呵護有加。他常送我禮物,也常帶我去看戲、看電影或觀賞運動比賽,還幫我溫習語學。每逢我考試,他便像關懷自己的孩子般,百般照應、替我操心。這類精神上的呵護,使得我至今仍然難忘他的好意。
不過,我們的關係自然不會永遠停留在這種階段。過了一段時間,他變得一見我就發愁,默默嘆息;在相識滿半年之後,我們終於碰上危機。
那天晚上,我們嫌公寓供應的飯菜難吃,前往附近的餐廳用餐。不知何故,他像是豁出去似的,黃湯一杯接一杯下肚,並且再三向我勸酒。當然,我當時還不會喝酒,順著他的意喝了兩、三杯之後,臉頰便倏然發燙,腦袋瓜裡活像盪鞦韆一樣搖搖晃晃,一股放縱感逐漸占據我的心房。
我們勾肩搭背,沿途唱著一高的宿舍歌,回到公寓。
「去你的房間,去你的房間吧!」
諸戶說道,把我拉回我的房間,房裡擺著我從不收拾的被褥。也不知道是被他推倒,或是我自己絆倒,我突然倒向被褥。
諸戶站在我身旁,目不轉睛地凝視我的臉龐,生硬地說道:
「你好美。」
說來奇妙,這一剎那,我腦中閃過一種異樣的念頭,彷彿我化成女性,眼前這個因酒意而滿臉通紅卻多了股魅力的美貌青年,就是我的丈夫。
諸戶跪了下來,牽起我擱在一旁的右手。
「你的手好燙。」
我也同時感受到對方滾燙如火的掌心。
我臉色發青,縮到房間角落,而諸戶的眉宇之間隨即浮現鑄下大錯的後悔之色。
「開玩笑的、開玩笑的,我剛才是鬧著玩的,不會做那種事。」
他啞著嗓子說道。
接著有好一陣子,我們都只是把臉撇向一旁,默默不語。突然,喀噹一聲,諸戶在我的桌子上趴下來,把臉埋在盤起的雙臂之中一動也不動。見狀,我猜想他也許是在哭泣。
「請別輕蔑我。你一定覺得我很齷齪吧?我和你是不同的人種,在所有意義上都截然不同,可是我無法說明這些意義。有時候我一個人獨處,都會害怕得渾身打顫。」
不久,他抬起臉來如此說道。不過,我不明白他在害怕什麼,直到許久以後遇上那種場面的那一刻。
正如我的猜想,諸戶的臉龐滿是淚痕。
「你能諒解嗎?我只求你的諒解。若是奢求更多,或許就是我強人所難。不過,請你別逃開,陪我說說話,至少接受我的友情,給我繼續單相思的自由,好不好?欸,蓑浦,起碼讓我保有這點自由……」
我頑固地保持沉默,然而,看著諸戶一面訴說一面流淚,我也不禁熱淚盈眶。
我隨心所欲的租屋生活因為這件事而中止。雖然我並未對諸戶產生嫌惡感,但兩人之間的尷尬氣氛與我的薄臉皮,讓我無法在公寓繼續待下去。
話說回來,我實在難以理解諸戶道雄的心。在那之後,他非但沒有放棄這段異樣的戀情,用情甚至隨著時光流逝越來越深。有時偶然相遇,他會不著痕跡地在談話之間表露心跡;大多時候,他都是透過前所未見的情書訴說他的相思之苦。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我二十五歲時,教我如何不費解?縱使我滑嫩的臉頰仍舊帶有少年時的影子,且肌肉不似一般的成年男性發達,倒如婦女般豐潤。
這樣的他竟突然向我的情人求婚,我的震驚自然不在話下。在對他產生情敵的敵意之前,反而先感受到一股近似失望的感情。
「莫非……莫非他知道我和初代談戀愛,為了不讓異性搶走我、為了在他心裡永遠獨占我,才化身求婚者,阻撓我們的戀情?」
自大的我無法克制猜疑心,做出這種無謂的想像。
怪老人
這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某個男人由於過於深愛另一個男人,居然企圖搶走那個男人的情人。這是普通人絕對無法想像的情況。當我妄自揣測諸戶是為了從我身邊搶走初代而求親時,忍不住嘲笑自己的多疑。然而,一旦心生猜疑,這股疑忌便揮之不去。我還記得諸戶曾經對我詳述他的異樣心態:「我從女人身上不但感受不到任何魅力,甚至感到厭惡、覺得骯髒。你能懂嗎?這種心態不僅可恥,更是可怕。有時候,我害怕得不知該如何自處。」
生性厭惡女人的諸戶道雄突然想結婚,而且如此鍥而不捨地提親,實在太奇怪了。我之所以用「突然」兩字形容,是因為直到不久前,我都還持續收到諸戶那種異樣但真心實意的情書;一個月前,我甚至曾受諸戶之邀,一同去帝國劇場看戲。想當然耳,諸戶邀我看戲的動機是出於對我的愛。從他當時的舉止看來,這一點無庸置疑。然而,僅經過一個月,他的態度就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拋棄了我(這麼形容活像我們之間有什麼曖昧,但絕無此事)向木崎初代求婚,這確確實實是不折不扣的「突然」。非但如此,他的對象居然正好是我的情人木崎初代,若說是巧合,未免太過牽強。
如此這般,經過我這番解釋,相信大家便能明白我的猜疑並非毫無根據。不過,正常人難以理解諸戶道雄的奇妙行動及心理,說不定會反過來責怪我浪費諸多篇幅在無謂的揣測之上。不像我這樣曾直接目睹諸戶異樣舉止的人,會有這種反應很正常。既然如此,或許我該稍微顛倒一下順序,向讀者說明我之後得知的事。換句話說,我的猜疑並非妄想。諸戶道雄確實如我猜想,為了拆散我和初代,才大張旗鼓地向初代求婚。
至於他如何大張旗鼓──
「真的很煩人。媒人幾乎天天上門遊說我媽,而且對你瞭若指掌,舉凡你家的財產、你在公司領的月薪,全都跟我媽報告。還說憑你的本事,無法娶我進門、養活我媽。實在太過分了。最讓我懊惱的是,我媽看了那個人的照片、聽聞他的學歷和家境以後,就開始動心。我媽是個好人,可是這回我真的怨恨起她來,太可悲了。最近我媽和我簡直成了仇人,一開口就是這件事,講到最後一定吵架。」
初代如此訴說。從她的口氣,可知諸戶是多麼鍥而不捨地提親。
「都是那個人,害得我媽和我鬧得很僵,一個月前的我根本無法想像。比方說,我媽最近常趁我不在家時,偷翻我的書桌和書信盒,好像是想找你寫的信,打探我們進展到什麼地步。我這個人向來一絲不苟,抽屜裡都收拾得整整齊齊,最近卻常常變得亂七八糟。真的太可悲了。」
原來還發生了這樣的事。初代向來乖巧又孝順,但是在這場和母親的戰爭之中,她並未投降。她始終堅持己見,不惜惹惱母親。
這個意料之外的障礙,反而讓我們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深厚。初代對於我一度畏怯的情敵不屑一顧,一心一意愛著我,她的真切情意令我感激不盡。當時正值暮春,為了減少初代回家之後與母親相處的時間,我們下班便在燈光燦爛的大路上,或是嫩葉味瀰漫的公園裡並肩散步。到了假日,則是在郊外的電車站會合,漫步於綠意盎然的武藏野。如今閉上眼睛,我仍能看見小河、看見土橋、看見石牆、看見宛若鎮守之森的高大老樹林。在這般美景的環繞中,二十五歲卻仍然稚氣未脫的我,和身穿花俏銘仙、腰間高綁我最愛的礦物顏料色織帶的初代並肩同行。請別笑我幼稚,這是我的初戀之中最快樂的回憶。雖然僅僅維持了八、九個月,但兩人一直形影不離。我將工作與家庭拋諸腦後,猶如漫步雲端般陶醉得意。我不再畏懼諸戶的求婚,因為我完全沒有理由擔心初代變心。如今初代已不把母親的斥責放在心上,絲毫沒有接受其他人求婚的念頭。
至今,我仍然無法忘記那種如夢似幻的快樂。然而,那段美好的時光稍縱即逝。在我們初次交談的九個月後──我記得一清二楚,那是大正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們的關係畫下休止符。說來悲哀,這並非因為諸戶道雄求親成功,而是木崎初代死了。不僅如此,她的死法極不尋常。她成了凶殺奇案的被害者,悽慘地離開人世。
然而,在敘述木崎初代的橫死事件之前,我想先請讀者留意某件事,就是初代在死前幾天向我訴說的怪事。這件事也與後續發展有關,請讀者務必牢記在心。
某一天,初代上班時始終臉色蒼白,像在害怕什麼一般。下班後,我們並肩走在丸之內的大道上,我問起這件事。初代邊窺探身後邊依偎著我,說出以下這番駭人的經歷。
「昨晚是第三次了,每次都是在我大半夜洗澡的時候遇上。你也知道,我住的地方很偏僻,晚上都烏漆抹黑。我漫不經心地打開格子門,走到門外,發現有個奇怪的老爺爺站在我家的格子窗邊,三次都是這樣。我一打開格子門,他就驚覺過來,立刻改變姿勢,若無其事地走開。瞧他的樣子,在我開門的那一瞬間之前,似乎一直在窗口窺探我家裡的情況。一、兩次或許是我多心,可是,昨晚又發生同樣的事,他絕對不是碰巧路過的人。說歸說,我從來沒在附近看過那樣的老爺爺。總覺得這是個壞兆頭,害怕極了。」
見我險些笑出來,她氣急敗壞地繼續說道:
「他不是普通的老爺爺,我從沒看過那麼恐怖的老爺爺。他的年紀可不只五、六十歲,鐵定超過八十,腰彎得活像從背部將身子折成兩半似的;走路時也一樣,拄著拐杖像把彎了的鑰匙,只有頭朝著前方,遠遠看上去只有普通成年人的一半高,活像隻噁心的蟲子在爬。還有,他的臉上滿布皺紋,都快看不清楚五官,不過瞧他那副模樣,年輕的時候長得一定也很嚇人。我心裡害怕,不敢多看,可是就著我家門前燈的光線,我瞥見了他的嘴巴。他的嘴唇活像兔子裂成兩半,我到現在還記得他和我四目相交、咧嘴一笑的模樣,直教我忍不住發毛。一個活像妖怪、八十好幾的老爺爺,接連三次在三更半夜站在我家前頭,實在太奇怪了。這會不會是什麼壞兆頭?」
初代的嘴唇血色全失、微微顫抖,她定然很害怕。當時,我只笑著說她想太多。畢竟,即使她看到的是真的,我也不明白其中意義。再說,一個年過八十、彎腰駝背的老爺爺,能有什麼危險的企圖?我只當成是少女無謂的恐懼,根本沒當一回事。然而,事後我才知道初代的直覺準確得有多可怕。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江戶川亂步傑作集1 孤島之鬼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江戶川亂步傑作集(1):孤島之鬼 作者:江戶川亂步 / 譯者:王靜怡 出版社: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9-29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1 |
二手中文書 |
$ 269 |
文學 |
$ 269 |
推理/驚悚小說 |
$ 289 |
小說/文學 |
$ 306 |
神怪/推理 |
$ 306 |
中文書 |
$ 306 |
推理小說 |
$ 30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江戶川亂步傑作集1 孤島之鬼
「日本推理之父」江戶川亂步首部長篇小說。
★「日本推理之父」江戶川亂步逝世五十週年紀念版本,跨世紀的跨界合作──江戶川亂步 X 咎井淳,
耽美插畫再現大師筆下陰鬱、扭曲卻又令人著迷的不可思議世界。
★「江戶川亂步傑作集」共三冊:BL亂步《孤島之鬼》、變態亂步《人間椅子 屋頂裡的散步者》、
血腥亂步《蟲》,自2016年10月初起,連續三個月出版。
-「BL亂步」收錄江戶川亂步唯一一部同性愛作品《孤島之鬼》;
-「變態亂步」收錄了《人間椅子》、《D坂殺人事件》、《屋頂裡的散步者》、《帶著貼畫旅行的男人》、《鏡子地獄》、《帕諾拉馬島奇談》等充滿異色及人性黑暗面的精采短篇;
-「血腥亂步」則收錄了《芋蟲》、《跳舞的侏儒》、《蟲》、《陰獸》等帶有獵奇狂氣感的中、短篇。每篇皆是眾所皆知、令人印象深刻的經典傑作選,搭配富含張力的全新封面,十分值得珍藏。
★《孤島之鬼》是江戶川亂步首部長篇小說,結合本格推理與孤島冒險劇情,深入刻劃人性幽微與醜陋,
以及同性之戀、殘酷之美,被譽為亂步最佳傑作。
★「江戶川亂步傑作集」三本首刷皆附贈江戶川亂步X咎井淳簽名收藏小海報。
我未及三十歲已滿頭白髮,
這非天生,而是受到極大震驚,黑髮一夜變白。
妻子在左側大腿上方有個大得可怕的傷疤,
她的傷疤與我的白髮,源自同一件難以置信的事。
雖然我拙於言辭,
還是想寫下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
關於我死在密室裡的戀人,
關於對我懷有戀慕的男人,
以及,宛如人間地獄的那座孤島……
作者簡介:
江戶川亂步
Edogawa Ranpo
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
本名平井太郎,生於三重縣名張町,自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從事過各種職業,一九二三年以短篇小說《兩分銅幣》出道。著作等身,作品不僅有本格推理小說,還有幻想小說、犯罪小說、青少年文學、文學評論等眾多傑作,被譽為「日本推理之父」。
封面插畫
咎井淳
Jo Chen
七月四日生,生於台灣台北,現居美國。專職漫畫、插畫家,曾擔任UDON、DC、Marvel、Dark Horse等出版社的美漫封面,與繪製遊戲的封面。
與編劇鬼畜貓合組兩人社團「Guilt | Pleasure」,自二○一○年起連載原創BL作品《言之罪(In These Words)》,並已譯為中文、英文、日文等多種語言。
官方網站:www.jo-chen.com
譯者簡介:
王靜怡
1980年生,高雄市人。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興趣為閱讀、寫作以及電玩。目前為專職譯者,譯有《花鳥風月》系列、《偵探.日暮旅人》系列、《劇團!Theatre》系列、《空之中》、《海之底》、《諸神的差使》等書。
TOP
章節試閱
回憶中的一夜
當時,我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在丸之內的某棟辦公大樓裡的貿易商──合資公司S‧K商會擔任辦事員。老實說,微薄的月薪只夠我自己花用。無可奈何,誰教我的家境不好,無法供我從W職校畢業後繼續升學呢?
我從二十一歲開始上班,到那年春天正好滿四年。我負責核對部分會計帳簿,從早到晚只需打算盤。而我雖僅職校畢業,卻熱愛小說、繪畫、戲劇及電影,自以為懂得藝術,因此遠比其他職員討厭這種機械性的工作。我的同事大多是光鮮亮麗、勇於嘗試且活在當下的人,不是每晚勤跑咖啡廳或舞廳,就是滿嘴的運動話題。喜歡幻想又內...
當時,我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在丸之內的某棟辦公大樓裡的貿易商──合資公司S‧K商會擔任辦事員。老實說,微薄的月薪只夠我自己花用。無可奈何,誰教我的家境不好,無法供我從W職校畢業後繼續升學呢?
我從二十一歲開始上班,到那年春天正好滿四年。我負責核對部分會計帳簿,從早到晚只需打算盤。而我雖僅職校畢業,卻熱愛小說、繪畫、戲劇及電影,自以為懂得藝術,因此遠比其他職員討厭這種機械性的工作。我的同事大多是光鮮亮麗、勇於嘗試且活在當下的人,不是每晚勤跑咖啡廳或舞廳,就是滿嘴的運動話題。喜歡幻想又內...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序言
我還不到三十歲,一頭濃密的髮絲已全數變白,沒有半根倖免。天底下還有像我這般不可思議的人嗎?年紀輕輕,頭上就戴了頂雪白的棉帽,私毫不遜於古時候的白頭宰相。不認識我的人一見到我,便會對我的腦袋投以狐疑的視線;有些比較不客氣的,連招呼都還沒打完,就劈頭問起我的白髮。提出這種問題的人男女皆有,同樣令我煩惱。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問題,只有內人的閨中密友才會悄悄詢問我,就是關於我妻子左腿上側那道駭人的巨大疤痕。那是個不規則的圓形紅斑,看起來也像是大型手術的痕跡,令人觸目驚心。
其實這兩件異事並非我們夫...
我還不到三十歲,一頭濃密的髮絲已全數變白,沒有半根倖免。天底下還有像我這般不可思議的人嗎?年紀輕輕,頭上就戴了頂雪白的棉帽,私毫不遜於古時候的白頭宰相。不認識我的人一見到我,便會對我的腦袋投以狐疑的視線;有些比較不客氣的,連招呼都還沒打完,就劈頭問起我的白髮。提出這種問題的人男女皆有,同樣令我煩惱。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問題,只有內人的閨中密友才會悄悄詢問我,就是關於我妻子左腿上側那道駭人的巨大疤痕。那是個不規則的圓形紅斑,看起來也像是大型手術的痕跡,令人觸目驚心。
其實這兩件異事並非我們夫...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江戶川亂步 繪者: 咎井淳 譯者: 王靜怡
- 出版社: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9-29 ISBN/ISSN:978986473277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52頁 開數:25開(14.8x21 cm)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