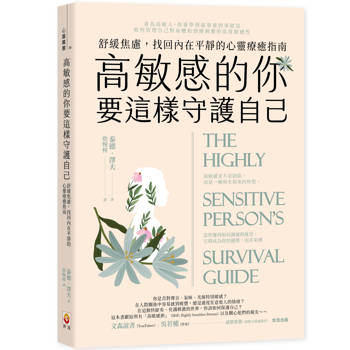沉睡中的少女,
孤獨的在夢中
茫然地
跨出了步伐……。
推開的門扉前方,
是一片謎樣的景色。
執筆‧日日日(《鎖鎖美@不好好努力》)、插畫‧有坂あこ(漫畫《夢沉抹大拉》),新銳製作群打造、編織出的『夢日記』世界觀。
由英才們所描繪,夢之世界的答案是……!?
本書特色
●傳說的免費遊戲『夢日記』小說化
●由『夢日記』原作者確認,基於原作者的解釋而製作的作品。『夢日記』謎團完全揭露!
●日日日、碧風羽、有坂あこ,眾多名作者/繪者集結,用文字/圖像完整詮釋夢日記的世界!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夢日記 你的夢中,我已不在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夢日記 你的夢中,我已不在(全) 作者:ききやま、日日日 / 譯者:ASATO 出版社: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7-2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198 |
輕鬆/校園/戀愛 |
$ 225 |
幻奇冒險 |
$ 225 |
戀愛情事 |
$ 225 |
文學作品 |
$ 225 |
小說/文學 |
$ 232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夢日記 你的夢中,我已不在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原作:ききやま
免費遊戲『夢日記』製作者。由ききやま氏製作的這款同名遊戲,是個將舞台設定於「夢中」,讓玩家在幻想世界四處探索的遊戲。故事不存在明確的目的,就連角色的名稱也只揭露一小部分。本作獨特的世界觀獲得眾多玩家的好評,雖然已經公開數年之久,至今仍不斷吸引新的粉絲。
執筆:日日日
小說家。漫畫原作者。遊戲劇本作家。高中時期便創下同時獲得五項新人獎的佳績,順利出道。代表作有《狂亂家族日記》、《蟲,眼球系列》、《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大奧之櫻》等。執筆作品中有不少改編為跨媒體作品,受到極高的注目。
插畫:有坂あこ
漫畫家。插畫家。是位以凜然的絕美畫風、各種人物細緻表情見長的畫師。作品橫跨雜誌、小說、漫畫等各種領域。現於《YOUNG ACE》連載《夢沉抹大拉》改編漫畫。
原作:ききやま
免費遊戲『夢日記』製作者。由ききやま氏製作的這款同名遊戲,是個將舞台設定於「夢中」,讓玩家在幻想世界四處探索的遊戲。故事不存在明確的目的,就連角色的名稱也只揭露一小部分。本作獨特的世界觀獲得眾多玩家的好評,雖然已經公開數年之久,至今仍不斷吸引新的粉絲。
執筆:日日日
小說家。漫畫原作者。遊戲劇本作家。高中時期便創下同時獲得五項新人獎的佳績,順利出道。代表作有《狂亂家族日記》、《蟲,眼球系列》、《鎖鎖美小姐@不好好努力》、《大奧之櫻》等。執筆作品中有不少改編為跨媒體作品,受到極高的注目。
插畫:有坂あこ
漫畫家。插畫家。是位以凜然的絕美畫風、各種人物細緻表情見長的畫師。作品橫跨雜誌、小說、漫畫等各種領域。現於《YOUNG ACE》連載《夢沉抹大拉》改編漫畫。
目錄
009第一部 你
010第一話/小房間
014第二話/門之後
019第三話/紅雨傘
024第四話/單行道
029第五話/紅綠燈
035第六話/紅絲線
041第七話/日記本
046第八話/暴風雪
053第九話/BED
062第十話/你是誰?
069第二部 我
070第十一話/旁觀者
075第十二話/榮格
082第十三話/潛意識
090第十四話/小青蛙
101第十五話/霓虹燈
110第十六話/夢遊症
119第十七話/下水道
126第十八話/寫生文
136第十九話/墜落死
154第二十話/別看我
163第三部 夢日記
164第二十一話/紙劇場
175第二十二話/血文字
193第二十三話/地獄變
206第二十四話/走馬燈
213第二十五話/夢解析
235第二十六話/聯想法
247第二十七話/宇宙船
255第二十八話/薨殂者
261第二十九話/活下去
268最終話/你的夢中,我已不在
010第一話/小房間
014第二話/門之後
019第三話/紅雨傘
024第四話/單行道
029第五話/紅綠燈
035第六話/紅絲線
041第七話/日記本
046第八話/暴風雪
053第九話/BED
062第十話/你是誰?
069第二部 我
070第十一話/旁觀者
075第十二話/榮格
082第十三話/潛意識
090第十四話/小青蛙
101第十五話/霓虹燈
110第十六話/夢遊症
119第十七話/下水道
126第十八話/寫生文
136第十九話/墜落死
154第二十話/別看我
163第三部 夢日記
164第二十一話/紙劇場
175第二十二話/血文字
193第二十三話/地獄變
206第二十四話/走馬燈
213第二十五話/夢解析
235第二十六話/聯想法
247第二十七話/宇宙船
255第二十八話/薨殂者
261第二十九話/活下去
268最終話/你的夢中,我已不在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