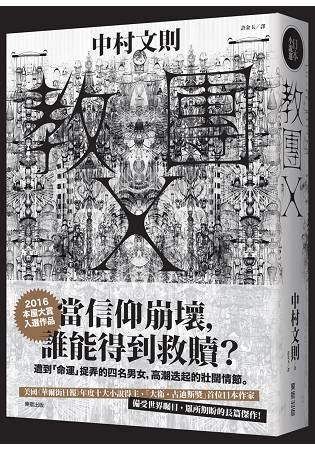人類是種希望自己是好人的種族,
世界卻是由漠然的邪惡所建立。
我曾想過,我這種人要是沒出生就好了……
世界卻是由漠然的邪惡所建立。
我曾想過,我這種人要是沒出生就好了……
引起殺人事件而躲避警方調查的謎之邪教「X教團」,正在進行一個偏激的世界改造計劃。為了找出失蹤女友下落的楢崎透,儘管知道危險,卻仍決定深入這個邪教,等待著他的真相究竟如何?神是什麼?命運又是什麼?黑暗的反面是光明?抑或是更深沉的黑暗?當信仰崩壞,又有誰能得到救贖?
本書特色
日本賣破10萬冊!
入選2016年本屋大賞!
曾榮獲美國《華爾街日報》年度十大最佳小說、
首位榮獲美國「大衛.古迪斯獎」的日本作家中村文則,
備受世界矚目,眾所期盼的最新長篇巨作!撼動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