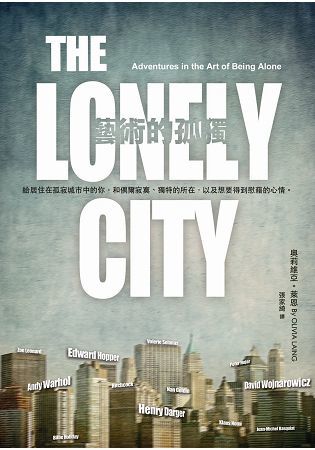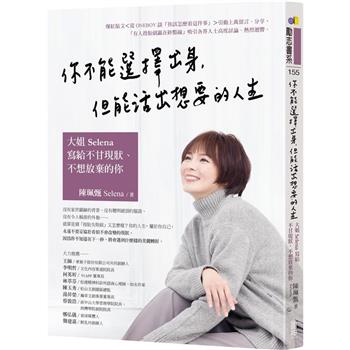序
「傑出之作......文字精湛醉人。」—亞當.福爾茲(ADAM FOULDS)
「強而有力,正中靶心,充滿魔力。」—海倫.麥克唐納(HELEN MACDONALD)
試想夜裡站在一幢高樓的第六、第十七或第四十三層樓窗邊,整座城市以好幾個小房間、十萬扇窗的面目呈現,其中一些昏暗無光,一些瀰漫著或綠或白或金的光線。室內的陌生人腳步來回游移,在自己的時間裡忙著各自的事。你看得見他們,卻觸摸不著,這就是你我都習慣的都會現象,世界各個城市隨便一個夜晚都觸目可見,就連最活躍的人都不禁感受到寂寞的震顫,交雜著令人不安的距離與赤裸。
雖然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感到寂寞,但在都市裡生活、被好幾百萬人包圍的寂寞卻有它獨特的味道。有人可能會想,這狀態跟都市生活及集體生存這兩點背道而馳,但身體親近卻不代表能排解內心的孤寂感。與他人摩肩擦踵生活,還是很有可能—甚至很容易—感到孤單冷落。城市很可能讓人感到寂寞,坦承這一點,我們就能明白寂寞指的不見得是形單影隻的孤立,更可能是缺少交集、親密、親切感:出於某些原因,無法找到內心所渴望的那種親密。字典的解釋是:少了他人陪伴的不快樂。因此在人群中寂寞若達到巔峰也不意外了。
寂寞往往教人難以啟齒,也難以歸類。寂寞的狀態跟憂鬱症類似,往往在一個人的體內盤結交錯,深深紮根,就好比有的人天生愛笑或有一頭紅髮。再者,寂寞可能轉瞬即逝,跟著外在環境反應,來回往復,隨著喪親之痛、分手或社交圈的轉變接踵而來。 跟憂鬱症、抑鬱與焦躁雷同,寂寞被視為一種疾病,也需要靠醫學治療。我們曾聽過別人不斷強調,寂寞沒有目的,而羅伯.懷斯(Robert Weiss)在他別開生面探討寂寞的著作中也提到,「寂寞是一種沒救的慢性病」。如此這般的說法不脫一個信念,那就是人類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成雙成對,幸福可說是或應該是永恆的狀態,但並非每個人的命運都相同。也許我錯了,但我並不贊同這種說法,我不認為人生中這個常見的生活經驗毫無意義,沒有豐富層次,不具某種價值。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一九二九年的日記描述內心的寂寞,她覺得分析寂寞感受或許能帶來啟發,更補充:「若這種感受能夠捕捉得到,我便不會鬆手:在人們居住的世界,受寂寞與沉默的驅使,吟唱出對真實世界的感受」。有意思的是,寂寞或許能帶你體會真實觸碰不了的經驗。 不久前我在紐約待了一段時間。紐約,這座充滿粗花崗岩、混凝土和玻璃建築,每天都被孤寂佔據、喧鬧沸騰的小島。雖然紐約的生活經驗讓人絲毫感覺不到自在,但若這種生活無法讓人思考活著的意義等深奧問題,若除了眼見為憑的真相,就真的沒別的了,我不禁好奇吳爾芙是否說錯了。
我內心有些東西正燃燒殆盡,不單是我個人的感受,更是身為這個世紀的子民,數位時代的人群一份子。寂寞的意義為何?要是我們不和其他人類親密接觸,要怎麼生存?我們是怎麼和他人交流的?要是交談困難呢?性會是寂寞的解藥嗎?答案如果是,那我們的身體或性慾要是不正常或損害,要是我們病了或者天生不夠有魅力,又該怎麼辦?科技幫得上忙嗎?科技拉近人們的距離,抑或只是將我們困在螢幕後方? 我絕對不是唯一一個好奇想知道這些問題答案的人。不同派別的作家、藝術家、製片和詞曲創作者都用各自的方式探討過寂寞,想要釐清寂寞為何物,解決寂寞帶來的問題,但那一陣子我反而漸漸愛上影像,從中找到我在其他地方都遍尋不著的慰藉,開始探究視覺藝術的領域,著魔似的想要找出其中關聯,以及其他人經歷類似遭遇的真實證據。在曼哈頓的那段時間,我開始收集傳達寂寞或從寂寞中誕生的藝術品,特別是現代都市裡顯現的寂寞,尤其是過去七十多年來的紐約市。
一開始吸引我注意的是影像,但隨著我愈掘愈深,我開始與影像背後的人相遇:在人生和作品中,與寂寞及其後遺症羈絆糾結的人。在眾多記載孤寂城市的人當中,其中一些人的作品讓我學到東西或感到觸動,也讓我在這本書深思—這些藝術家包括希區考克(Hitchcock)、瓦勒麗.索拉納斯(Valerie Solanas)、南.戈丁(Nan Goldin)、克勞斯.諾米(Klaus Nomi)、彼得.胡爵(Peter Hujar)、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佐伊.李歐納(Zoe Leonard)和尚.米榭.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我對四位藝術家最感興趣: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安迪.沃荷(Andy Warhol)、亨利.達格(Henry Darger)以及大衛.瓦納羅維奇(David Wojnarowicz)。這四人不全是永久棲息於寂寞的居民,個別代表著五花八門寂寞的處境和角度,然而他們對人與人之間的鴻溝及人群中的孤立感受特別敏銳。
但對安迪.沃荷,似乎不該寂寞,他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他永不嫌膩的交際本能,身旁幾乎無時不刻都有耀眼的跟班,但他的作品卻凸顯出孤獨及寂寞帶來的問題,這都是他終其一生抵抗的問題。沃荷的藝術在人與人之間遊走,深度探究遠近距離、親密與陌生之間等深刻的哲學問題。就跟許多寂寞的人一樣,他有無藥可醫的囤積癖,沃荷製作物品,並且讓物品包圍自己,藉此在人類親密關係的需求之間架起藩籬。安迪.沃荷害怕與人面對面接觸,很少見到他沒帶相機和錄音機等裝備就出門,他把這些當作緩衝物,減緩互動交流:充分說明了我們為何會在所謂互聯網的二十一世紀使用科技。
工友兼非主流藝術家亨利.達格則恰恰相反,他獨自住在芝加哥市的宿舍,在這幾近沒有同伴或觀眾的情況下,創作出充滿美妙卻恐怖生物的虛構世界。八十歲時,他不得不離開宿舍前往天主教會度過餘日,原本的宿舍充斥百餘張精雕細琢、讓人不安的畫作,這些作品他從未公諸於世,沒人看過。達格的人生說明了社會勢力是怎麼導致孤立—更說明想像力能夠對抗孤寂。
在這些藝術家的交際方式迥異,因此作品以五花八門的方式探討寂寞這個題材,或繞著寂寞打轉,有時正面直擊,有時討論各種招致污名或孤立的主題—性、疾病、虐待。瘦皮猴又惜字如金的愛德華.霍普雖然有時嘴上不承認,實際上卻用視覺手法呈現都市孤寂,將它轉譯成顏料。近一個世紀以來,他用畫筆下畫出空無一人的咖啡館、辦公室和飯店大廳玻璃後方的孤男寡女,一幅幅都成了城市裡的孤寂印記。
你可以展現出孤獨面貌,也可以高舉武器對付它,創造出能夠溝通表達的東西,抗拒審查制度與沉默。這就是大衛.瓦納羅維奇的動力,這位美國藝術家、攝影師、作家兼激進主義份子至今仍寡為人知,但他勇敢非凡的作品卻最能將我從羞於承認自己孤獨的重擔中獲得解放。
而我漸漸明白,寂寞是一個熙來人往的地方:它就是城市的代名詞。即便是像曼哈頓這種活力充沛又以邏輯打造的城市,剛開始住進城市的人都會迷失自我。隨著時間過去,你會在內心發展出一張地圖,收藏你最愛的地點和偏好的路線:像是一個無人能精確複製或拷貝的迷宮。我這幾年來累積打造出的,就是一張依照需求和興趣,以我個人與他人經驗拼湊起的地圖。我想了解寂寞究竟為何物,寂寞在人們的生活裡是什麼模樣,試圖紀錄追蹤寂寞與藝術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好久以前,我曾聽一首丹尼斯.威爾森(Denis Wilson)的歌曲,那首歌來自海灘男孩(The Beach Boys)解體後的一張專輯:《太平洋藍》。我很喜歡其中一句歌詞:寂寞是多麼獨特的所在。還是青少年時,我會在秋天夜晚坐在床上,想像那獨特所在是一座城市,也許在日落時,每個人都踏上歸途,城市裡霓虹燈閃爍活現。我當時便明白自己也是其中一位居民,我很喜歡威爾森的說法,他唱出孤寂城市的豐沃與惶恐。
寂寞是多麼獨特的所在。威爾森的這句歌詞並非向來清楚明瞭,我卻在旅行中慢慢認同他的這句話,寂寞絕不是一個毫無價值的體驗,反而正中我們珍惜與需求核心的經驗,許多偉大的事物都源自孤寂城市:不只有孤寂打造出的事物,還有解救寂寞的事物。
奧莉維亞.萊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