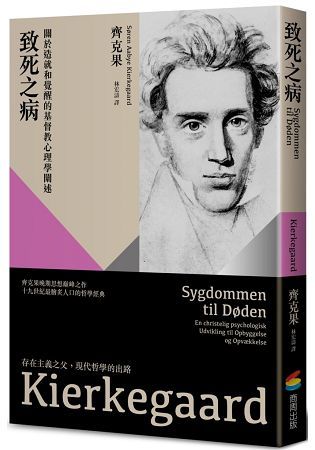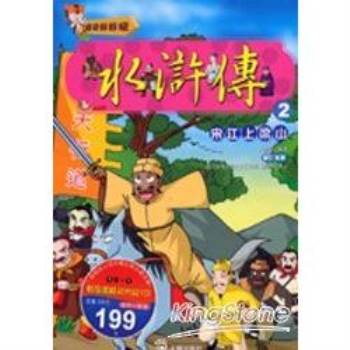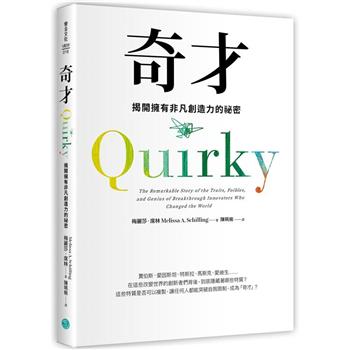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致死之病:關於造就和覺醒的基督教心理學闡述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在齊克果筆下,絕望是一種屬靈的疾病,源自於人對於自我的誤解,以及人神關係的失衡。絕望不是一時的病症,也和外在環境無關,它是一種存在處境,就連死亡也不能擺脫的處境。因此,所謂的絕望是對於自我、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的存在境況的絕望。齊克果描述了三種絕望的形式:第一種形式是人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絕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甚至不認識他的自我是什麼;第二種形式則是在絕望中不想做自己,那是一種軟弱的絕望,不管是對於塵世或永恆的絕望,只想隨波逐流,而不想做自己;第三種形式是在絕望中想要做自己,也是抗拒的絕望,人意識到自己的絕望而想要努力掙脫它,到頭來卻因為種種挫敗而放棄了救贖的希望。最後,齊克果也指出真正擺脫絕望的方法:一、認識人的自我是什麼;二、完全透明地接受神的安排。
作者簡介
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
出生於丹麥哥本哈根,是個憂鬱且多產的作家,曾被稱為「丹麥瘋子」,在他短短四十二年的生命裡,寫下無數的作品。
齊克果在哥本哈根大學攻讀神學學位,亦涉獵歷史、文學、哲學與心理學,因此他的作品涵蓋神學、文學批評、心理學和宗教學。他對當時的社會和基督教的改革提出許多針砭之言,對於哲學更有重大的突破性見解,尤其是對於黑格爾和浪漫主義的批評,為現代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也為聖經的角色賦予現代的意義,對二十世紀的神學和宗教哲學影響甚鉅。
齊克果也是個文思敏捷的詩人,他的日記成為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主要作品有:《反諷的概念》、《恐懼與戰慄》、《非此即彼:生活片簡》、《生命途中的階段》、《對哲學片簡的非科學性的結論附語》、《愛在流行》、《致死之病》、《憂懼之概念》等等。(詳細介紹請見內文作者年表)
相關著作:《齊克果日記》
譯者簡介
林宏濤
台灣大學哲學碩士,德國弗來堡大學博士研究。譯著有:《血田》、《獵眼者》、《人的條件》、《自我的追尋》、《等待哥倫布》、《人造地獄》、《無私的藝術》、《藝術想怎樣》、《正義的理念》、《與卡夫卡對話》、《人的形象與神的形象》、《上帝的語言》、《神子》、《我的名字叫耶穌》、《如何改變世界》、《文明的哲學》、《奧斯卡與我》、《g先生》、《鈴木大拙禪學入門》、《啟蒙的辯證》、《菁英的反叛》、《詮釋的衝突》、《體會死亡》、《美學理論》、《法學導論》、《愛在流行》、《隱藏之泉》、《神在人間》、《眾生的導師:佛陀》、《南十字星風箏線》、《神話學辭典》、《與改變對話》、《死後的世界》、《讀論語學英語》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