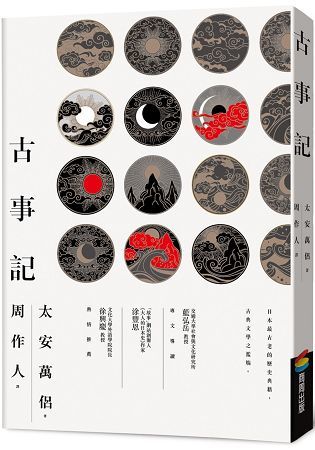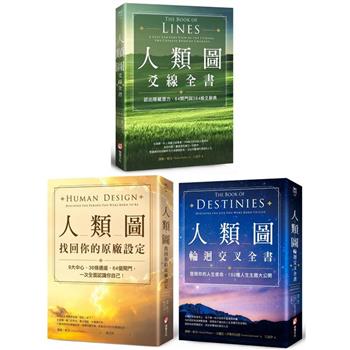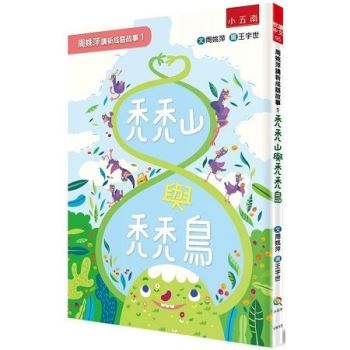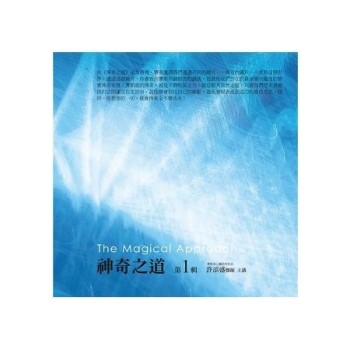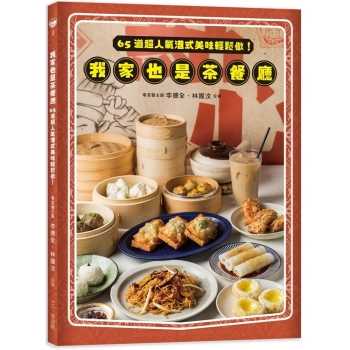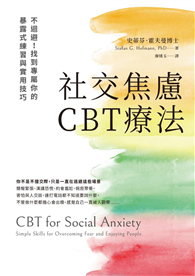從《古事記》探索日本文化的源頭/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副教授 藍弘岳
日本曾是臺灣的殖民母國,即使在殖民統治已結束七十幾年後的今天,臺灣的地理空間、語言中,仍隨處可見日本文化遺留的痕跡,媒體與街頭也充斥著動漫等當代日本流行文化。就此來說,日本文化對臺灣人是熟悉的,但若仔細觀察流行日本動漫中所講述的「怪力亂神」,或在日本旅行時,瀏覽整潔的街道、古老的神社等古蹟,許多人對於日本的觀感,可能不僅止於美麗、新奇,還有著異國的陌生感。
其實,神社中所祭祀的諸神,乃至像《少年陰陽師》那般日本動漫作品中出現的許許多多鬼神,都源於日本神話。而所謂日本神話,大多是來自於《古事記》、《日本書紀》等書。
《古事記》與《日本書紀》
《古事記》是太安萬侶(?~西元七二三年) 據稗田阿禮所背誦的「帝紀」「舊辭」,在和銅五年(西元七一二)所編寫成的書,也是現存最古老的日本史書。分為上卷(序文、神話)、中卷(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第十五代應神天皇)和下卷(第十六代仁德天皇到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
《日本書紀》則是由舍人親王等人用漢文在養老四年(西元七二○年)編撰完成的,記載從神代到持統天皇(第四十一代天皇)時代的歷史。全書共三十卷、系圖一卷(但已遺失)。
這兩本書的重要差異,如下所述:
一、相對於《古事記》是寫給天皇及其周遭相關人看的,《日本書紀》則是有意識到彼岸大陸的國家,因此被認為是代表日本正史之書。
二、在《古事記》中不用「日本」,自稱為「倭」;而《日本書紀》其直接以「日本」為國名。
三、《日本書紀》是以正統漢文寫成的;《古事記》則是用「音訓交用」的方式寫成的。即用漢字來表示語意外,也同時用漢字標出日本音。這也就是說,《古事記》是由變體漢文文體記錄下來,被認為是很難完全正確解讀的文本 。
四、與上一點相關,《日本書紀》繼承來自《准南子》、《三五曆紀》等古代中國漢文書籍中的陰陽世界觀,《古事記》則有日本獨自的世界生成的觀念,及「高天原」的世界觀 。
五、《日本書紀》從奈良時代已有人研究,但在江戶時代之前,《古事記》幾乎無人研究。
因上述的差異,江戶時代的國學大家本居宣長(西元一七三○~一八○一))認為,相較於幾乎完全以漢文書寫的《日本書紀》已被「漢意」(からごころ,指來自中國的漢字、漢籍中的道德原理與觀念等)嚴重汙染;《古事記》被汙染的程度比較少。他相信透過對《古事記》的研究,可重現古代日本的「皇國」(みくに),即一種人與神共生的理想國度 。所以,本居宣長花了三十年以上的時間注釋《古事記》,寫出《古事記傳》。這本至今依然是解讀《古事記》必備的經典。但《古事記傳》不只是注釋書,更代表江戶國學對於古代日本的理解與想像之書。而對於《古事記傳》的繼承與批判,是十八、十九世紀日本國學運動的一大重點。在國學文本中,透過對日本神話的分析,和對儒學、中華(漢、韓)等的批判,對何謂日本、日本人(和)做出一種本質性的描述與論斷。這些國學相關著作是近代思想史、國文學等學術領域在發明、思考日本傳統時的重要思想來源,故也成為近代日本國族敘事的重要文本。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可說《古事記》不只是古代日本的歷史、神話或文學,更是企圖在近代日本打造日本國族、日本意識形態時所依據的重要作品 。
再進一步說,儘管《古事記》或《日本書紀》有上述的差異,但兩書編纂的目的都是為表現天皇統治之正統性,即兩書中所談的神話,都是關於天皇神話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也成為日本在二戰戰敗之前,主張天皇制國家正統性的主要依據來源。
《古事記》與天皇神話
如上述,由於《古事記》上卷記載的神代部分内容過於玄妙,日本史學者很難直接將之視為正史來看待,而是把它理解為是神話故事,透過對其中文字與修辭解釋的方式,試圖還原其所欲表現的歷史。
單純就神話的角度來說,《古事記》上卷記載的日本神話至少整合了「高天原神話」與「出雲神話」這兩大日本古代神話體系。
所謂高天原神話,包括:眾神的出現、日本列島的誕生、伊邪那美與火神、伊邪那岐前往黄泉之國、伊邪那岐返回地上與祓禊、天照大神與須佐之男命的對立、天之岩戶等故事情節。
而所謂出雲神話,則有須佐之男命殺死八岐大蛇、大國主命的建國與讓國等故事。
按神野志隆光的解釋,《古事記》上卷的這些故事被串連在一起,詮釋了為何天皇具有統治日本的正統性。其正統性的生成原理,就在天照大神的出現,及天孫攜帶神器降臨地上世界,並促使大國主命讓國的這一連串神話的情節中 。
其次,就《古事記》中卷部分,即從神武天皇至倭建命、應神天皇、神功皇后的部分,那主是要詮釋「大八島國」(淡路島、四國、隠岐島、九州、壱岐島、對馬、佐渡島、本州),乃至朝鮮半島如何在歷史進行中,成為天皇統治之世界(「天下」)的過程 。
至於下卷之中包括許多反叛與平定的故事,即是要敘述天皇的「天下」如何被維持,並實現具正統性皇統的過程 。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民族學、民俗學、考古學、神話學,乃至比較神話學的角度,來理解《古事記》中出現的諸神。從這些角度來看,例如伊邪那岐、伊邪那美等,被認定原本是淡路島的地方神,而天照大神原本只是伊勢地方信仰的太陽神。
而以太陽之子從天而降成為王朝始祖的神話來說,還可與東南亞、朝鮮半島等地類似的神話比較 。
這也就是說,在歷史或文學領域,在其他學術領域中,《古事記》記載的内容依然是重要的研究對象,是提供我們理解上古日本歷史的重要線索。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中蘊含的神話,也是不斷刺激當代日本文化創作的重要資源。
周作人與《古事記》
根據紀錄,一九五九年,周作人翻譯完成《古事記》,至一九六三年正式出版了中文譯本,但他沒有以周作人之名擔任譯者,而是用筆名周啓明之名出版。直到一九九○年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時,譯者才改回為周作人 。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據周作人撰寫的《知堂回想錄》中文章〈我的工作(五)〉 所述,周作人早在一九二○年左右就開始翻譯《古事記》,並陸續發表於《語絲》雜誌,共十次左右。
一九四九年後,因為想要介紹世界古典文學運動的關係,他再次開始翻譯《古事記》的後續。他強調說,自己對這個譯本並不滿意,希望有更多注釋。但這個譯本依然是現今最好的中文譯本。周作人在有限的材料中,除依據本居宣長的《古事記傳》內容,也使用《日本書紀》、《古語拾遺》、《倭名類聚抄》等古代日本的文獻,乃至中國的《莊子》、《唐韻》、《玉篇》等古典文獻進行了補充注釋。這顯示了儘管周作人對譯本尚不滿意,但也是下足了功夫的。
其次,周作人認為《古事記》的真實價値當不是作為歷史,而是作為文學書來看,是記錄古代傳說的書。所以他將此之視古代日本神話和民間故事等俗文學之類的作品看待,將之翻為白話文石,文中經常出現諸如「我的身子」、「親愛的妹子」等非常口語的用詞表現。所以,雖然文中的日本神名等不好讀,有些繞口,但譯文本身是輕快易懂的。
老實說,若非周作人的貢獻,《古事記》的中文譯本恐怕將會更晩問世 。
本書不僅對於古代日本的歷史、神話感興趣的人該讀,對於喜歡周作人文學之人也是値得翻讀、賞析的。而且,對於《古事記》的研究者而言,周作人的翻譯與注釋,作為首部《古事記》中文譯本,更是値得關注與研究的。
對一般大衆而言,《古事記》或許可以是一本引領你理解日本的神話、文創乃至展開自我想像之旅的經典。
| FindBook |
有 14 項符合
古事記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古事記
日本第一部文史典籍,經典地位有如中國《山海經》!
《古事記》是日本第一部文字典籍,也是現存最早的日本文學與歷史著作,於西元712年由稗田阿禮口述,太安萬侶編寫撰寫而成,全書分為三卷。
上卷內容是日本的起源、諸神的由來與神話傳說,主要講述日本國土與天皇是如何形成。中、下卷講述從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第三十三代日本天皇)的相關事蹟與傳說,包括平亂、征討、施政、制度、皇室傳說。全書編寫的主要目的,在於傳達帝王與國家的傳承,讓後世之人能夠理解日本的緣起。
對於想要理解日本神話(如天照大神、日本起源、八岐大蛇),或者想要理解神社或大社與「式年遷宮」等等神道教制度,還有經常出現在漫畫動畫電玩小說中的日本歷史題材(如天孫降臨、神武天皇),或想要探討日本天皇的誕生、皇室傳承制度等等內容的讀者來說,本書是最好的原典。
譯者周作人先生,為胡適稱許為「民國第一散文家」,長年從事翻譯,譯作等身。其譯筆樸實而生動,淺顯簡練,不作刻意雕飾、不作絲毫賣弄,精彩還原了神話的古樸與美感。因其畢生熱愛日本文化,深入探究日本文化精髓,筆下用詞簡單可愛,但極具韻味。
本書除原典內容之外,更整理「神明列表」,簡介書中出場諸神的來源、關係與重要事件。另附有「神族圖譜」與「天皇世系圖」,將眾神與歷代天皇的身分、淵源、關係,以跨頁或彩色拉頁等圖表方式呈現,讓讀者在閱讀本書之餘,能透過圖表,對內容人物、神明的從屬與上下關係、淵源,一目了然,清楚掌握。
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副教授 藍弘岳 精彩導讀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創辦人、《大人的日本史》作者 涂豐恩
中國文化大學外國語文學院院長 徐興慶 誠摯推薦
作者簡介:
太安萬侶
(?-723.08.15)日本奈良時代官員。奉元明天皇之命,編纂由稗田阿禮口述的《帝紀》、《舊辭》,寫成《古事記》一書。養老七年過世,官拜民部卿、從四位下。
譯者簡介:
周作人
(1885.01.16-1967.05.06)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
曾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學習《說文解字》,後留學日本,攻讀外國語言,研究希臘文,並曾任教東京利教大學希臘文課程。另外學習俄文、梵文。歷任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
被胡適稱許為「民國第一散文家」,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精研日本文化五十餘年。半生從事翻譯,曾翻譯許多高水準的日本文學與古希臘文學經典之作,如希臘的《希臘神話》、《伊索寓言》,與日本《古事記》、《狂言選》、《枕草子》、《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並校定《今昔物語集》、《源氏物語》(豐子愷版本)等書。
TOP
推薦序
從《古事記》探索日本文化的源頭/國立交通大學社文所副教授 藍弘岳
日本曾是臺灣的殖民母國,即使在殖民統治已結束七十幾年後的今天,臺灣的地理空間、語言中,仍隨處可見日本文化遺留的痕跡,媒體與街頭也充斥著動漫等當代日本流行文化。就此來說,日本文化對臺灣人是熟悉的,但若仔細觀察流行日本動漫中所講述的「怪力亂神」,或在日本旅行時,瀏覽整潔的街道、古老的神社等古蹟,許多人對於日本的觀感,可能不僅止於美麗、新奇,還有著異國的陌生感。
其實,神社中所祭祀的諸神,乃至像《少年陰陽師》那般日本動漫作品中出現的許許多...
日本曾是臺灣的殖民母國,即使在殖民統治已結束七十幾年後的今天,臺灣的地理空間、語言中,仍隨處可見日本文化遺留的痕跡,媒體與街頭也充斥著動漫等當代日本流行文化。就此來說,日本文化對臺灣人是熟悉的,但若仔細觀察流行日本動漫中所講述的「怪力亂神」,或在日本旅行時,瀏覽整潔的街道、古老的神社等古蹟,許多人對於日本的觀感,可能不僅止於美麗、新奇,還有著異國的陌生感。
其實,神社中所祭祀的諸神,乃至像《少年陰陽師》那般日本動漫作品中出現的許許多...
»看全部
TOP
目錄
導讀
引言
序
卷上
一、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
天地始分
諸島之生成
諸神之生成
黃泉之國
祓除
二、天照大御神與建速須佐之男命
誓約
天之岩戶
三、建速須佐之男命
穀物的種子
八岐的大蛇
世系
四、大國主神
兔與鱷魚
蚶貝比賣與蛤貝比賣
根之堅洲國
八千矛神的歌話
世系
少名毗古那神
御諸山之神
大年神的世系
五、天照大御神與大國主神
天若日子
讓國
六、邇邇藝命
天...
引言
序
卷上
一、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
天地始分
諸島之生成
諸神之生成
黃泉之國
祓除
二、天照大御神與建速須佐之男命
誓約
天之岩戶
三、建速須佐之男命
穀物的種子
八岐的大蛇
世系
四、大國主神
兔與鱷魚
蚶貝比賣與蛤貝比賣
根之堅洲國
八千矛神的歌話
世系
少名毗古那神
御諸山之神
大年神的世系
五、天照大御神與大國主神
天若日子
讓國
六、邇邇藝命
天...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太安萬侶 譯者: 周作人
-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8-11-01 ISBN/ISSN:978986477538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世界國別史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