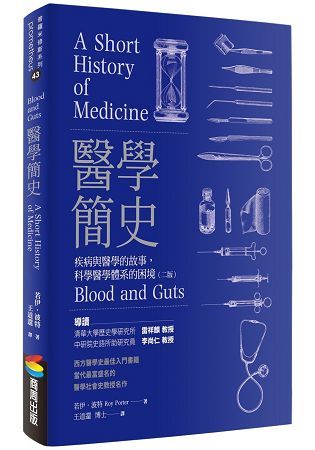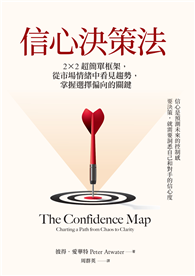細數疾病與醫學的歷史糾葛,
由鮮血與膽識所編織的動人故事
數千年來,人類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對抗疾病,
有的巧妙、有的古怪、有的可怕。
從放血療法到X光攝影,從簡陋的肢體割鋸到器官移植,
都是編織本書《醫學簡史》的線索。
全書題材應有盡有,強調出西方醫學的古今之變。
包括:疾病(第一章);各種治療疾病的人(第二章);對身體的研究(第三章);
發源於實驗室的現代生物醫學與疾病的生物醫學模型(第四章);
治療疾病的手段,特別是科學醫學(第五章);
外科醫學(第六章);醫院--關鍵的醫療機構(第七章)。
在最後一章(第八章),則會評估現代醫學的社會與政治影響。
在西方知名度最高的醫學史學者若伊.波特的帶領下,
本書探討了人、病、醫之間的歷史互動,
以社會與社會中流行的信念為鋪陳脈絡,
說的是疾病與醫學的故事,字裡行間隱含的卻是病人的痛苦歷程,
內容綱舉目張,是最佳的西方醫學史入門書。
【名家導讀】
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雷祥麟教授
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李尚仁教授
【國際推薦】
「文字流利,妙趣橫生,從希波克拉底斯與古埃及醫師,一直到南丁格爾……你該知道的醫學史這兒全有……一趟輕快的過去之旅。」──科學史家盧索(George Sebastian Rousseau),(英國)文學評論
「醫學影響所有的人,對這麼一個大題材,本書是想像力豐富、文筆又卓越的導論。」──醫學史家山古塔(Chandak Sengoopta),(英國)獨立報
「解析歷史潮流、恢復歷史真相、戳破教條、針砭知識份子的浮誇氣息,沒有人比得上波特。」──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主編霍頓醫師(Richard Horton),(英國)倫敦時報
| FindBook |
有 15 項符合
醫學簡史:疾病與醫學的故事,科學醫學體系的困境(二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醫學簡史:疾病與醫學的故事,科學醫學體系的困境(二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若伊.波特Roy Potter
波特是國際知名的英國學者,2001年9月自倫敦衛康(Wellcome)醫學史學院(2000年併入倫敦大學大學院〔UCL〕)退休,在英國社會史、科學史、醫學史等領域都有精彩專著,撰寫與編輯的書超過一百本。他退休後不滿九個月就因心臟病發去世,學界同聲惋惜。
1997年,波特的《人類醫學史》出版,佳評如潮。《人類醫學史》正文超過七百頁,譯成中文將超過五十萬字。本書源自波特上課的講稿,以八章概述西方醫學史的主要面相,綱舉目張,簡明扼要,是最佳的西方醫學史入門書。
譯者簡介
王道還
台北市出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著有《天人之際》(三民書局),譯作包括《達爾文作品選讀》(誠品書店)、《第三種黑猩猩》(時報文化)、《好小子貝尼特》(允晨出版公司)、《盲眼鐘錶匠》(天下遠見出版公司)、《達爾文與基本教義派》(果實出版社)等。
若伊.波特Roy Potter
波特是國際知名的英國學者,2001年9月自倫敦衛康(Wellcome)醫學史學院(2000年併入倫敦大學大學院〔UCL〕)退休,在英國社會史、科學史、醫學史等領域都有精彩專著,撰寫與編輯的書超過一百本。他退休後不滿九個月就因心臟病發去世,學界同聲惋惜。
1997年,波特的《人類醫學史》出版,佳評如潮。《人類醫學史》正文超過七百頁,譯成中文將超過五十萬字。本書源自波特上課的講稿,以八章概述西方醫學史的主要面相,綱舉目張,簡明扼要,是最佳的西方醫學史入門書。
譯者簡介
王道還
台北市出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著有《天人之際》(三民書局),譯作包括《達爾文作品選讀》(誠品書店)、《第三種黑猩猩》(時報文化)、《好小子貝尼特》(允晨出版公司)、《盲眼鐘錶匠》(天下遠見出版公司)、《達爾文與基本教義派》(果實出版社)等。
目錄
導讀/若伊.波特:歷史學家與老師
導讀/醫學簡史》中一個有趣的留白
序言
第一章 疾病
第二章 醫生
第三章 身體
第四章 實驗室
第五章 治療
第六章 外科醫學
第七章 醫院
第八章 醫學與現代社會
進階書目
索引
導讀/醫學簡史》中一個有趣的留白
序言
第一章 疾病
第二章 醫生
第三章 身體
第四章 實驗室
第五章 治療
第六章 外科醫學
第七章 醫院
第八章 醫學與現代社會
進階書目
索引
序
若伊.波特:歷史學家與老師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若伊.波特(1946-2002)大概是英語世界這二十多年來知名度最高的醫學史學者。他的聲明除了來自幾本提出重大歷史創見而深受學術界推崇的著作之外,也因為他發願為一般讀者寫作,長期投入歷史研究的普及推廣工作。這本《醫學簡史》以及去年中譯出版的《瘋狂簡史》,就是他晚年在這方面持續努力的部份成果。
1994年我前往倫敦大學攻讀醫學史學位,除了研修碩士課程外並旁聽幾門大學部課程,其中包括若伊講授的「醫病關係史」。若伊的課在所內總是大受歡迎,修課同學以醫科學生居多。每年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評分,他向來是所內老師第一名。他講課擅長以有趣甚至匪夷所思的軼事來引發學生興趣,然後透過分析這些故事的歷史脈絡帶入課程主題。例如十八世紀歐洲醫界掀起一股反手淫運動,許多書籍與小冊都嚴厲警告手淫對身體的各種重大危害。若伊講授這段西方醫學史的著名插曲時,以當時英國一個醜聞案例開場:有位學校教師最大的嗜好就是在星期天下午,和另一位朋友帶著反手淫書籍手冊到當地教堂墓園,趁著四下無人,坐在墓碑上一邊大聲朗誦一邊手淫。若伊藉這個例子告訴學生,不要不假思索地相信任何出版品的內容能反映社會的普遍心態與實況。宣導反手淫的書籍,由於對手淫有繪聲繪影的描述,有時甚至引起某些人把它們當作色情書刊來閱讀的興(性)趣。若伊進而透過這個例子來討論書籍與讀者、醫生意見和病人行為之間的複雜關係。
我初到英國時,對自己的英文口語表達能力尚乏自信,在課堂上沒能和若伊有任何互動、對話。第一次有機會和他聊天,是在我的指導教授勞倫斯(Christopher Lawrence)家中舉行的耶誕派對上。若伊告訴我他很高興我去旁聽他的課,我提到打算研究英國熱帶醫學史,還說最近讀的法國史家德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的《黃熱病史》(The History of Yellow Fever)很精彩。若伊則建議我讀美國史家科曼(William Coleman)所寫的《北方的黃熱病》(Yellow Fever in the North)。雖然他沒有批評德拉波特的書,但從他的口氣隱約可以感受到他欣賞的是科曼詳細的歷史敘述和步步為營的歷史討論,而對德拉波特好藉個別史事做哲學斷言的風格有所保留。當然,我也知道德拉波特是傅科(Michel Foucault)的學生,而若伊向來不喜歡傅科的史學風格。
若伊畢業於劍橋大學,隨後在母校擔任研究員。1977年,他以博士論文改寫的《地質學的形成》(The Making of Geology)出版了。他這本成名作是一部紮實的社會史著作,研究英國早期地質學家的出身、他們的研究活動,和這兩個因素在地質學成為一門學科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1979年,若伊由劍橋轉往倫敦大學倫敦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維康醫學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研究主題從地質學史移轉到醫學史,尤其是醫病關係史、瘋狂史與精神醫學史。他倡議「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把史學研究焦點從醫師轉移到病人身上。在瘋狂史領域,若伊最著名的論點是在《心囚》(Mind-Forgd Manacles, 1987)一書中,以紮實的經驗研究反駁傅科關於古典時代(約在1650-1800年這段期間)歐洲普遍出現對瘋人的「大監禁」的說法。但他更實質的貢獻或許是對十八世紀英國精神醫學的社會史研究,以及透過病人的一手史料來呈現瘋狂的聲音。
若伊以學術生產力知名。他出身倫敦南部工人階級家庭,靠獎學金進入劍橋,學生時代就以大量的閱讀為樂。他暑假通常不回家,就待在劍橋圖書館中閱讀藏書。有人付錢請他在劍橋看書,他覺得這是難以想像的好差事!我也聽過許多關於他驚人記憶力、專注能力以及寫作能力的傳聞。例如他從美國開完學術會議回來,通常就由機場直奔辦公室繼續寫作。他擔任期刊論文審查人常一天內就會交出審查報告。他常利用週末寫書評,上午騎腳踏車把書帶到倫敦攝政公園(Regent Park)閱讀,下午回來時四、五百頁已經讀完,重點頁都折起並寫下評注,晚上就完稿寄出了。他每年一兩本專書外加多篇論文的寫作速度,是現在絕大多數歷史學者望塵莫及的。有些人認為他的早逝和這種拚命工作的作風脫不了關係,但若伊向來樂在閱讀寫作,從不覺得研究工作是負擔。我後來知道他的家族有心臟病的歷史,而且他每年都做健康檢查,卻沒查出他的冠狀動脈已有阻塞。
若說有哪種學術工作曾讓若伊疲倦的話,那就是學術行政工作。他退休前一年正值維康醫學史研究所改制,在行政上由直接隸屬維康基金會改為正式隸屬倫敦大學學院。若伊在此動盪時刻接中心主任,期間他盡心盡力諮詢每個成員的意見,甚至像我這種一兩年後就會走路的博士後研究員,他也請吃午餐、一對一討論中心的發展事宜。不過主管職真的不適合若伊,我還記得那段期間經常在下午看到他的倦容。退休前他接受訪問,表示他一向熱愛學術研究,多年來從不倦煩,但近年英國學術界的行政和評鑑事務日益沈重繁瑣,他發現他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出席委員會接受評鑑或評鑑別人,真正做研究的時間越來越少。於是他決定乾脆提早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
若伊退休後的寫作數量仍遠超過絕大多數史學研究者,並更加投入歷史普及事業。我有一位老師曾說:若伊為一般讀者寫作的興致,遠高於專為幾十個聰明的同行專家而寫。若伊雖以醫學史家的身份知名,研究興趣卻不僅止於此。我的英國老師如勞倫斯以及曾經來台訪問的艾傑頓(David Edgerton)都強調,醫學史與科技史學者對一般史(general history)一定要下功夫,才能真正做出好的研究。若伊則更進一步。他在醫學史「本業」之外,一般史的研究寫作也沒中輟,舉凡啟蒙運動、倫敦社會史、十八世紀英國社會、語言與社會等主題都有專門著作。退休後他打算全心投入一般史的研究,研究領域也有朝思想史前進的趨勢。可惜天不假年,若伊學術事業的新階段根本來不及開展,不只是史學界的遺憾,更是廣大讀者的損失。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若伊.波特(1946-2002)大概是英語世界這二十多年來知名度最高的醫學史學者。他的聲明除了來自幾本提出重大歷史創見而深受學術界推崇的著作之外,也因為他發願為一般讀者寫作,長期投入歷史研究的普及推廣工作。這本《醫學簡史》以及去年中譯出版的《瘋狂簡史》,就是他晚年在這方面持續努力的部份成果。
1994年我前往倫敦大學攻讀醫學史學位,除了研修碩士課程外並旁聽幾門大學部課程,其中包括若伊講授的「醫病關係史」。若伊的課在所內總是大受歡迎,修課同學以醫科學生居多。每年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評分,他向來是所內老師第一名。他講課擅長以有趣甚至匪夷所思的軼事來引發學生興趣,然後透過分析這些故事的歷史脈絡帶入課程主題。例如十八世紀歐洲醫界掀起一股反手淫運動,許多書籍與小冊都嚴厲警告手淫對身體的各種重大危害。若伊講授這段西方醫學史的著名插曲時,以當時英國一個醜聞案例開場:有位學校教師最大的嗜好就是在星期天下午,和另一位朋友帶著反手淫書籍手冊到當地教堂墓園,趁著四下無人,坐在墓碑上一邊大聲朗誦一邊手淫。若伊藉這個例子告訴學生,不要不假思索地相信任何出版品的內容能反映社會的普遍心態與實況。宣導反手淫的書籍,由於對手淫有繪聲繪影的描述,有時甚至引起某些人把它們當作色情書刊來閱讀的興(性)趣。若伊進而透過這個例子來討論書籍與讀者、醫生意見和病人行為之間的複雜關係。
我初到英國時,對自己的英文口語表達能力尚乏自信,在課堂上沒能和若伊有任何互動、對話。第一次有機會和他聊天,是在我的指導教授勞倫斯(Christopher Lawrence)家中舉行的耶誕派對上。若伊告訴我他很高興我去旁聽他的課,我提到打算研究英國熱帶醫學史,還說最近讀的法國史家德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的《黃熱病史》(The History of Yellow Fever)很精彩。若伊則建議我讀美國史家科曼(William Coleman)所寫的《北方的黃熱病》(Yellow Fever in the North)。雖然他沒有批評德拉波特的書,但從他的口氣隱約可以感受到他欣賞的是科曼詳細的歷史敘述和步步為營的歷史討論,而對德拉波特好藉個別史事做哲學斷言的風格有所保留。當然,我也知道德拉波特是傅科(Michel Foucault)的學生,而若伊向來不喜歡傅科的史學風格。
若伊畢業於劍橋大學,隨後在母校擔任研究員。1977年,他以博士論文改寫的《地質學的形成》(The Making of Geology)出版了。他這本成名作是一部紮實的社會史著作,研究英國早期地質學家的出身、他們的研究活動,和這兩個因素在地質學成為一門學科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1979年,若伊由劍橋轉往倫敦大學倫敦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維康醫學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研究主題從地質學史移轉到醫學史,尤其是醫病關係史、瘋狂史與精神醫學史。他倡議「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把史學研究焦點從醫師轉移到病人身上。在瘋狂史領域,若伊最著名的論點是在《心囚》(Mind-Forgd Manacles, 1987)一書中,以紮實的經驗研究反駁傅科關於古典時代(約在1650-1800年這段期間)歐洲普遍出現對瘋人的「大監禁」的說法。但他更實質的貢獻或許是對十八世紀英國精神醫學的社會史研究,以及透過病人的一手史料來呈現瘋狂的聲音。
若伊以學術生產力知名。他出身倫敦南部工人階級家庭,靠獎學金進入劍橋,學生時代就以大量的閱讀為樂。他暑假通常不回家,就待在劍橋圖書館中閱讀藏書。有人付錢請他在劍橋看書,他覺得這是難以想像的好差事!我也聽過許多關於他驚人記憶力、專注能力以及寫作能力的傳聞。例如他從美國開完學術會議回來,通常就由機場直奔辦公室繼續寫作。他擔任期刊論文審查人常一天內就會交出審查報告。他常利用週末寫書評,上午騎腳踏車把書帶到倫敦攝政公園(Regent Park)閱讀,下午回來時四、五百頁已經讀完,重點頁都折起並寫下評注,晚上就完稿寄出了。他每年一兩本專書外加多篇論文的寫作速度,是現在絕大多數歷史學者望塵莫及的。有些人認為他的早逝和這種拚命工作的作風脫不了關係,但若伊向來樂在閱讀寫作,從不覺得研究工作是負擔。我後來知道他的家族有心臟病的歷史,而且他每年都做健康檢查,卻沒查出他的冠狀動脈已有阻塞。
若說有哪種學術工作曾讓若伊疲倦的話,那就是學術行政工作。他退休前一年正值維康醫學史研究所改制,在行政上由直接隸屬維康基金會改為正式隸屬倫敦大學學院。若伊在此動盪時刻接中心主任,期間他盡心盡力諮詢每個成員的意見,甚至像我這種一兩年後就會走路的博士後研究員,他也請吃午餐、一對一討論中心的發展事宜。不過主管職真的不適合若伊,我還記得那段期間經常在下午看到他的倦容。退休前他接受訪問,表示他一向熱愛學術研究,多年來從不倦煩,但近年英國學術界的行政和評鑑事務日益沈重繁瑣,他發現他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出席委員會接受評鑑或評鑑別人,真正做研究的時間越來越少。於是他決定乾脆提早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
若伊退休後的寫作數量仍遠超過絕大多數史學研究者,並更加投入歷史普及事業。我有一位老師曾說:若伊為一般讀者寫作的興致,遠高於專為幾十個聰明的同行專家而寫。若伊雖以醫學史家的身份知名,研究興趣卻不僅止於此。我的英國老師如勞倫斯以及曾經來台訪問的艾傑頓(David Edgerton)都強調,醫學史與科技史學者對一般史(general history)一定要下功夫,才能真正做出好的研究。若伊則更進一步。他在醫學史「本業」之外,一般史的研究寫作也沒中輟,舉凡啟蒙運動、倫敦社會史、十八世紀英國社會、語言與社會等主題都有專門著作。退休後他打算全心投入一般史的研究,研究領域也有朝思想史前進的趨勢。可惜天不假年,若伊學術事業的新階段根本來不及開展,不只是史學界的遺憾,更是廣大讀者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