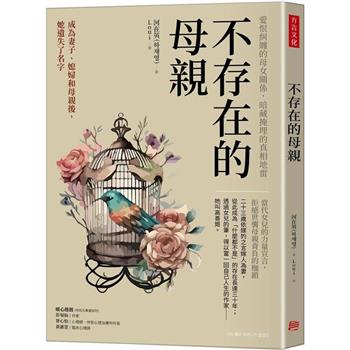圖書名稱: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
「如果學校的歷史課這麼有趣,就不會打瞌睡了!」
宮布利希以生動的口吻,像在為自己孫子講述歷史故事般,
以深入淺出的語言帶領讀者展開一場涵蓋人類浩浩蕩蕩、風起雲湧發展的世界歷史之旅。
從高空眺望,你會看見遠方的金字塔聳立,希臘衛城閃閃發光;
前面有蜿蜒的萬里長城、羅馬的凱旋門、山丘上的騎士城堡、宏偉莊嚴的大教堂;
再近一些,無敵艦隊航行在大海中,戰爭廢墟的濃煙不散,花園裡是豪華的凡爾賽宮,街道上傳來呼喊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聲音。
更近處,工廠煙囪在冒煙,火車汽笛在鳴響,摩天大樓高聳入雲霄……。
讀者可以看到過往人物、文明發展的軌跡、時代的精神與轉變、重大世界的前因後果,藉此一探遠古到現代歷史的面貌。宮布利希的孫女也將告訴你,這本風靡二十一個不同國家讀者的作品,背後有著怎麼樣的故事。
就在翻頁的瞬間,你將與世界各地的讀者一同潛入歷史的波濤中,彷彿在眼前重新看見這些歷史的畫面與場景!
作者簡介
恩斯特.宮布利希Ernst H. Gombrich
出生於維也納,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於維也納大學攻讀藝術史與考古學,博士論文以藝術家兼建築師的羅馬諾(Giulio Romano)為題,曾任職於維也納國立藝術歷史博物館。一九三六年前往英國,受聘於倫敦的瓦爾堡(Warburg)研究中心,對藝術史巨擘瓦爾堡(Aby Warburg)的遺作進行整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宮布利希為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進行監聽工作,負責將德文譯為英文,長達六年之久。戰後,即重返已併入倫敦大學的瓦爾堡研究中心,直至於一九七六年秋退休為止,長年貢獻於此。一九五九至一九七六擔任古典史教授,在這段期間並客座於英、美多所知名大學。一生榮獲多項獎章與榮譽。宮布利希一生著作豐富,其經典作品《藝術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縱橫半個世紀仍不墜,銷售超過兩百萬本,在藝術史入門書籍中的地位無人能出其右,已譯為十八國語言。與房龍、韋爾斯等作家並列。其他著作有:《藝術與幻覺》(Art and Illusion)、《文化史的危機》(Die Krise der Kulturgeschichte)、《規範與形式》(Norm und Form)等等。
譯者簡介
張榮昌
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教授,著各翻譯家。主要譯著有《沒有個性的人》、《諾貝爾獎獲得者與兒童對話》、《致父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