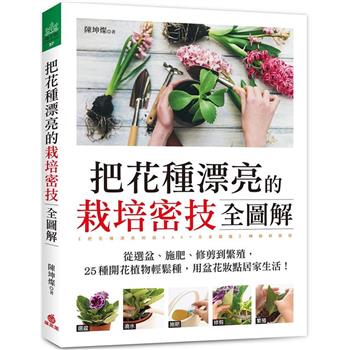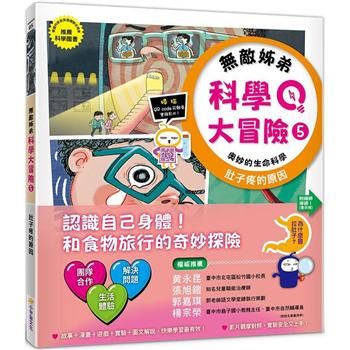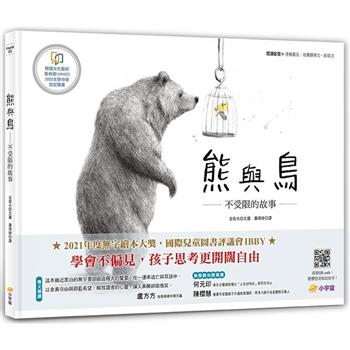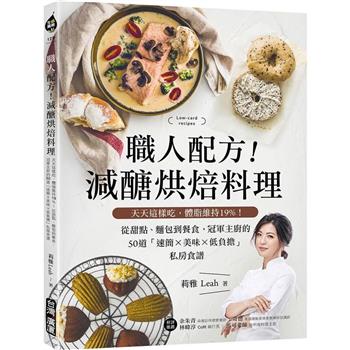第一章 大開眼界
我的當事人里奇•傑克遜(Ricky Jackson)當初遭判的刑罰,用他的話來說,是「放上電椅處死」。雖然他在一九七○年代九死一生地逃過那張電椅,但仍然為了一樁他不曾犯下的謀殺罪,在牢裡度過了將近四十年──這項全國紀錄至今還沒有被人打破。二○一四年十一月,克里夫蘭(Cleveland)冷颼颼的早晨,我陪伴五十七歲的里奇步出監獄,準備踏入一個與他過往所知相差甚遠的世界。一九七五年,俄亥俄州首次試圖入他死罪時,他才剛滿十八歲。
我也曾與雷蒙•托勒(Raymond Towler)一起坐在法庭裡,他同樣為了一宗他不曾犯下的強姦案,在牢裡待了二十九年。雷蒙性格文靜又富哲理,還是傑出的藝術家和音樂家,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我坐在那裡,看著法官敲下手中法槌,向當時已在牢裡受折磨數十載的雷蒙說:「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語畢,法官走下法官席與雷蒙擁抱,她的眼裡噙著淚水,朗誦了一首愛爾蘭的祝福詩歌:
願你前方的道路寬廣,
願風兒永遠輕拂你的背。
願陽光溫暖你的臉;
願雨水滋潤你的田地,
直到我們再相會的日子,
願上帝輕捧你於祂的掌心。
在我為「俄亥俄州無辜計畫」(Ohio Innocence Project, OIP)擔任冤案救援律師的生涯間,至今已協助二十五名像里奇和雷蒙這樣的當事人重獲自由,加總起來,他們為自己沒有犯過的罪在監獄裡被關了四百七十年。在他們之中,有些人和我的當事人南希•史密斯(Nancy Smith)一樣,環抱孩子的手曾被硬生生拉開,等到終能以自由之身擁抱孩子時,他們皆已成年。也有些人和里奇一樣,再次回到這個世界時,已經找不到任何曾與他們有緊密連結的家人或朋友。
為什麼他們不承認自己犯了錯?
我與已故友人洛伊絲•羅森塔爾(Lois Rosenthal)會結識,正是因為她原本就關注冤案的議題。洛伊絲不是律師,而是一位慈善家和社會正義的倡議者。她和她先生迪克以慷慨和博愛的精神改變了我的故鄉辛辛那堤(Cincinnati),因此城裡許多事物皆以他們為名,包括當代藝術中心(Contemporary Arts Center)。在洛伊絲的協助下,我於二○○三年共同創立、經營至今的「俄亥俄州無辜計畫」(Ohio Innocence Project),才得以站穩腳步與發展。該組織的主要使命是讓像里奇、雷蒙和南希這樣的無辜者能離開監牢。
在這十幾年間,每當我向洛伊絲描述新的案例,告訴她我們最近調查了哪個受刑人的案件,以及發現了能夠證明其清白的新證據時,她總是會問:「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多年來,她一次又一次地問:「這個人在一開始怎麼會被判有罪呢?」
過了幾個月之後,我難免又要告訴洛伊絲,雖然我們找到許多強力的證據可以證明當事人無罪,但檢察官強硬回擊,不願承認自己犯錯。她會問說:「怎麼會這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為什麼他們不承認自己犯了錯?他們怎麼能夠讓一個無辜的人關在牢裡?怎麼可以這樣子?」洛伊絲永遠無法理解為何這個體制會如此反應;為何它會扭曲法律與事實,好讓這些不義見不得光;為何它會如此抗拒改革;為何它會用這種方式犯下令人痛心的錯誤,還固執地拒絕改變與改善。
洛伊絲並不是唯一會這麼問的人,聽聞冤獄狀況的人都會這麼問。事實上,我經常以冤案為題進行座談,每當演講結束,我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總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為什麼檢察官要把替這些可憐人爭取正義這件事搞得這麼複雜?」「為什麼不改變制度以減少這些問題?」
由於反覆被問到這些問題,所以我寫了這本書,試圖加以回答。我決定寫下來,是因為我特殊的職涯帶給我獨特的視角,讓我能夠用多數人做不到的方式來回答這些問題。作為一個從事冤案救援的律師與行動者,我經常目睹警察、檢察官、法官和辯護律師的不義之舉,以及數以千計的無辜者如何因為這些行為與制度而深受折磨。換句話說,我見證過讓洛伊絲和其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這些問題。
不過在成為一名無辜運動的倡議者之前,有多年時間我也是個頑固的檢察官。兼具這兩種對比強烈的經驗,回頭看過去擔任檢察官的歲月,我發現自己也做了同樣的行為,同時抱持我現在知道將造成不正義悲劇的心態。當時我周遭其他人亦然。所以本書也算是一種自白與回憶錄,我的個人經驗提供了幕後視角,協助我們檢視造成冤案的心理和政治因素,這是過往其他書籍所沒有的。這本書同時是我個人演變的故事,一段覺悟與發現的故事。
在本書中,我會解釋人類的心理缺陷和政治壓力為何會讓刑事司法中的行動者,包括警察、檢察官、法官和辯護律師,做出異乎尋常且令人難以置信的不正義行動,甚且還渾然不自覺。我會談到何以我們會對這些問題如此盲目,不論是個人或社會整體。我們拒絕承認。事實上,我們的制度充滿盲目所造成的不正義。
最後我會闡釋改善現況、確實認識到問題所在、打開心胸所需要採取的行動,如此一來,才能夠建立一個更正義也更準確的制度。
檢察官轉戰冤案救援律師
早年我曾在紐約市擔任了多年的聯邦檢察官,我所起訴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常常躍上地方新聞,有時候甚至成為全國性新聞,包括組織性犯罪、綁架勒贖、恐怖行動、重大詐騙,以及涉及高階政治人物的貪汙案。我曾經因為「積極對抗犯罪」而獲頒地方的執法獎,也曾經從美國司法部長珍妮特•雷諾(Janet Reno)手中拿到「表現卓越」的國家獎項,全國僅有少數幾名檢察官獲此殊榮。我是檢察官中的檢察官。
二○○一年我回到故鄉辛辛那堤,在北肯塔基大學(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蔡斯法學院(Chase Law School)擔任刑法學教授。蔡斯法學院底下有個名為「肯塔基州無辜計畫」(Kentucky Innocence Project, KIP)的組織。各地的無辜計畫組成一個全國性的網絡,而其組織一般多設在法學院底下,讓法律系學生參與營救遭錯誤定罪的人。原本指導肯塔基州無辜計畫的教授在我任教的第一年剛好輪休,所以我這個新手刑法教授就被要求填補這個位置,負責在那一年指導學生。但身為一個前檢察官,我心中其實充滿懷疑。我並不相信這個國家有哪個被關進監牢的人是無辜的。我根本不想擔起這份差事。可是做為一個希望討新老闆們歡心的菜鳥教授,我實在無法拒絕,只好勉為其難地接手。
在我與肯塔基州無辜計畫的學生們所開的第一場會議中,兩名學生報告說他們剛到監獄裡探視因強姦案入獄的赫爾曼•馬伊(Herman May)。他們帶著滿溢的情感和熱情,談論著他們「看著馬伊的雙眼」、感受到他的真誠與痛苦,他們「知道」他是無辜的。我坐在那裡聽他們描述,內心不斷翻白眼。「實在太天真了,」我心想。「真是一群好騙又同情心氾濫的法律系學子。」
我問他們一開始是什麼證據定了馬伊的罪。原來馬伊會成為嫌疑犯,是因為他打算典當的一把吉他,恰巧是在案發當晚、自案發社區的一輛車裡被偷走的。這樣的巧合讓警察決定把馬伊的照片放入序列,拿給被害人指認。被害人指認了馬伊,接著在法庭上作證說,馬伊就是強姦她的人。
案發後,醫院從被害人身上採到犯案者的精液。被害人供稱她當時沒有其他性行為,所以精液一定是犯案者留下來的。在馬伊進行審判的當時,尚無法對精液進行DNA鑑定。於是馬伊遭判有罪,被送入監獄。
既然被害人指證歷歷,我相信馬伊是有罪的。應該說,我知道他有罪。我覺得學生們根本是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被害人都已經做出如此確實的指認了,他們竟然還相信這傢伙是無辜的。
然而後來肯塔基州無辜計畫促使法院採用新的科學技術對精液進行了DNA鑑定,結果發現犯案者的精液與馬伊的DNA序列不符。在為一場自己並未犯下的罪行坐了十三年的牢以後,馬伊獲釋,走出監獄。
不用說,這個經驗當然讓我這個檢察官的檢察官大開眼界。我大受衝擊。學生們訴說案發時還是青少年的馬伊如何從高中的社會課堂上,一邊哭著、一邊被警察帶至警局,只為了從他的鼠蹊部扯下陰毛送去做鑑識分析。這些故事突然間對我有了新的意義。想到自己幾個月前還在嘲笑這些故事、暗自覺得他根本就是活該,讓我很不好受。我不明白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
不久之後,我參加了全國性的「無辜網絡」(Innocence Network)會議。在那裡我遇到了從各地前來的男男女女,他們都曾經為自己沒有犯過的罪坐了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五年的牢。我聽了幾名學者和律師的演講,彷彿發現新大陸一般,看到刑事司法制度的缺點在我面前一一被揭露。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無辜運動。它讓我開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儘管進程緩慢但確實改變了。我逐漸明白發生的事遠比我過往看到的還要多,而且這些制度問題在我檢察官任內就應該要能夠看到,我卻一直視而未見。
隔年,我在辛辛那提大學法學院謀得教職。當時俄亥俄州是全美國還未成立無辜組織的幾個大州之一。在約翰•克蘭利(John Cranley,本書寫作之際為辛辛那提市市長)等人的幫助下,二○○三年我於新任教的法學院創立了俄亥俄州無辜計畫。至此我對這個運動已經堅信無疑。
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我的無辜計畫已經調查過數千名喊冤的俄亥俄州囚犯。我們的調查證實其中許多人確實有罪,但是如同前文所述,我們營救了二十五人,因為他們的確是無辜的。
一九八九年至今,全美已有超過兩千人被證實是冤錯案件的受害者。這個數字每週持續增長。這些案件詳情皆可在「美國平反案件登錄中心」(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的網頁上找到,該網站是由幾個知名大學和法學院合力經營。我知道這個數字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只有少數案件可以取得DNA和其他新證據。還有許多囚犯因為沒有可著力的證據,就是無法證明自身清白。
促使我寫這本書的原因,不只是因為我們的制度有時會錯判一些無辜的人。事實上,這個國家真的很常把無辜的人送進監獄,這在過去或許是驚天動地的消息,但現在已經無甚了了。
真正的動力來自我個人經歷。在我從檢察官轉戰冤案救援律師的過程中,見過千奇百怪的人類行為,有趣也讓我訝異。我曾看過分明搞錯的證人卻堅信自己是對的。還有證人的說詞如何被檢警扭曲、重塑,但他們渾然不覺,甚至連檢警也沒察覺自己改變了證人的供述,只為了使其符合自己對案件的假設。檢察官、警察、法官和辯護律師也會因隧道視野而對個案做出不合理的判斷,只因為他們不願意質疑自己最初的直覺,甚至無視證據。政治和內部壓力也會讓體制內的人做出不公不義的舉動,還不願承認其真正動機;他們變得頑固而傲慢,認為自己可以分辨真假,拒絕承認自己作為人類有其侷限。我曾看到這些人性的弱點如何帶來悲劇的、讓人撕心裂肺的不正義。
長遠來看,無辜運動最持久也最重要的結果並不是讓無辜者獲釋。我認為這場運動的重點毋寧在於,它讓我們對人類心理有了新的理解,進而帶來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無辜運動促使社會科學家以嶄新的活力,投入對於人類認知、記憶和錯誤的相關研究,進而更加理解人類的心智運作。心理學家開始問:「如果DNA證明某人並未犯案,那麼當初為何會有十個證人出庭作證,相信他就是真凶?」「如果DNA證明凶手另有其人,為什麼一個智商高於平均的人當初會自白殺人,甚至堅信自己確實犯案?」「為什麼一個理應中立的鑑識專家當初會站上證人席,認定被告指紋符合沾血凶刀上的指紋,結果後來我們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答案會令人驚訝。而它們不僅有助我們解釋為何眾多冤案會發生,也讓我們對刑事司法制度的許多基本假設產生懷疑,甚至讓我們開始檢討應該如何理解日常生活中的「真實」。
我有幸能同時從學術觀點和冤案救援律師/前檢察官的身分深入探討這些發展。學術觀點是指我所研究和教授的心理學臨床發展;而身為一個冤案救援律師/前檢察官,我更可以從第一線觀察到這些心理學原則如何在真實世界中展現。因此本書就是要同時從學術和真實世界的觀點解析這些原則。每一章都會探討一種存在於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人性心理弱點,例如確認偏誤、記憶的可塑性、目擊者錯誤認知、隧道視野、可信性判斷錯誤、行政之惡(administrative evil)、官僚的否認、去人格化(dehumanization),以及體制內部的政治壓力。我會以學術和實證的心理學研究來討論這些議題,輔以我擔任檢察官和冤案救援律師時所遇到的案件,由此顯示上述這些弱點從何扭曲了真相,又從何造成重大的不正義。這些心理學問題不只和刑事司法制度有關,所以我也會試著說明在日常生活中,不論工作或家庭,它們如何讓我們看不見真實。
我也將解釋,造成冤錯案件的心理缺失是所謂的「三重打擊」。它們不只在一開始造成錯誤定罪,也讓我們無法看見或理解發生了什麼錯誤。換句話說,它們讓我們看不見它們所造成的影響。即使錯誤定罪的主張是在二十、三十、甚或四十年之後才提出,同樣的心理問題仍然讓我們在事後繼續否認錯誤。也就是說,這些心理問題不僅製造問題、阻礙我們看到問題所在,甚至將問題隔開,令我們事後也無法發現和反思。結果就是,我們的社會集體否認我們的偏見、錯誤認知與記憶的問題。檢察官、法官、警察、陪審員、證人、辯護律師、媒體記者,每個人都陷入了制度的迷思,如常地繼續從事他們的工作,未曾察覺他們已履薄冰,處於陷落的邊緣。雖然科學和心理學上的各種突破正快速打破過去的迷思,但是總體來說體制中的行動者並未重視這些突破,他們抗拒「創新」,堅持己見,即使他們的根據極度薄弱。
我要先標註一些警語。第一,我並不是心理學家,而是一名律師。然而從檢察官轉換到冤案救援律師的角色,這樣獨特的職涯讓我可以「實地」察覺到心理學教授或許只能想像的不可思議的人類行為。加入無辜運動之後,我對於所見的人類心理深感著迷,於是開始研究各種心理學學說,希望能夠更加理解每天在法庭上看到的那些令人不安的人類行為,以及過去我身為檢察官時的表現。因此,雖然本書是由一位法律人所寫的關於心理學的書,但我相信它有助於闡釋重要心理學原則在真實情境中的運用。
第二,本書不會討論制度性的種族歧視。種族歧視無疑是重要的心理現象,也會汙染刑事司法制度的結果。即便如此,這個問題已在別處做過許多討論,且因過於複雜且普遍,此處篇幅無法處理。本書目的是要揭露其他沒有那麼廣泛被討論過的議題。
第三,有時我會大力批判刑事司法體制中的行動者,尤其是警察、檢察官、法官和辯護律師。但我提出批評並非因為我認為這些專業上充斥著不好的人。正好相反。我對執法者充滿敬意,也自認很支持他們。我對辯護律師滿懷尊敬,他們的工作吃力不討好卻極其重要;法官的工作亦然。本書雖然描述了專業人士的不公行為,但原因正是在於他們也是人。換作是我們,在沒有適當的指引和訓練下,大概也會做出類似的事。我擔任檢察官的時候,的確也曾經做過這類不公的行動,稍後將再詳述。我相信唯有承認和理解我們身為人類的侷限,也就是我們的心理缺陷,以及我們的制度在結構和政治上的缺陷,如此才能以足夠的謙遜,將刑事司法制度打造成真正符合正義的體制。
第四,我會多次論及我擔任檢察官時所做的事,還有「我們」在我的檢察官辦公室裡所做的事,這裡的「我們」是指我和檢察官同僚。我會根據我所學到和觀察的內容,提出我認為的習慣和常規。然而,我提及的大部分作法並非經過正式訓練而來;大多數菜鳥檢察官都是從上級和前輩那裡知道這些習慣和常規。因此,如果我說「我們在檢察官辦公室的作法是X」,意思是我認為這是一般的習慣和常規,但是我無法確定辦公室裡的每位檢察官都這麼做。
最後,這並不是一本末日之書。在本書末尾,我提供了一些解決方案,希望它們有助於減少制度的問題。雖然任何由人所運作的制度必然會出現人所犯的錯誤,但我們還是可以採取一些行動,讓刑事司法制度變得更為正確。我們有責任要探索、學習和採取這些行動。如同許多人生問題,能夠意識並承認我們的弱點,就成功了一半。我也會提出一些刑事司法制度的程序建議,以減少每一次調查中對真相勢必造成的人為扭曲。
| FindBook |
有 14 項符合
審判的人性弱點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審判的人性弱點
揭露人性的弱點如何帶來悲劇的、讓人撕心裂肺的不正義結局
「本書的寫作是為了解釋人類缺陷,亦即人類心理上的弱點,如何導致錯誤的有罪判決,而今日,這個問題無論是在台灣、在阿根廷,還是在美國,都一樣無法避免。」
從一個不相信冤獄存在的聯邦檢察官,到創辦旨在平冤的「無辜計畫」。馬克•戈希藉由本書分享他所看到與經歷的美國司法真實面貌:人的心理特質與政治壓力,導致司法體系內的行動者,包括警察、檢察官、法官、辯護人,往往在無知亦未察覺到的情況下,表現出難以置信的不正義行動。
馬克•戈希提出他所看到的美國司法一股重要的發展趨勢:以心理學的角度來解讀冤案,改革刑事司法系統。
造成司法盲目的心理學解讀,包括幾個主要概念:認知失調、確認偏誤及記憶汙染等等。馬克•戈希從許多冤案中,都看到了這三種心理問題,從而導致冤案難反,以及不願面對錯誤承認冤案,或者縱然平冤後仍然否認這些案件有問題。
作者特別提到,刑事司法制度不是自動運轉的機器,歷經了多年的校準後,它仍然無法達到完美的正義。我們必須承認這個制度是由人類組成的,所以它充滿了人類心理上的缺陷。我們應該要擁抱人性,不要害怕承認跟降低人類錯誤的出現。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謙卑,並且接受人是有侷限的。
作者簡介:
馬克.戈希Mark Godsey
辛辛那提法學院教授,俄亥俄無辜計畫(Ohio Innocence Project)發起人,現為該計畫主任,該單位共營救了二十八冤獄犯(合計刑期525年)。
曾擔任紐約市的聯邦檢察官,並獲傑出表揚。持續為People, Newsweek,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NN, Dateline NBC, Forensic Files等媒體擔任評論員與撰寫文章。
譯者簡介:
堯嘉寧
臺灣大學法律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社會人類學碩士。現為英/日文專職譯者,譯有:《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被誤解的犯罪學:從全球數據庫看犯罪心理及行為的十一個常見偏誤》、《從噁心到同理:拒斥人性,還是站穩理性?法哲學泰斗以憲法觀點重探性傾向與同性婚姻》等書。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大開眼界
我的當事人里奇•傑克遜(Ricky Jackson)當初遭判的刑罰,用他的話來說,是「放上電椅處死」。雖然他在一九七○年代九死一生地逃過那張電椅,但仍然為了一樁他不曾犯下的謀殺罪,在牢裡度過了將近四十年──這項全國紀錄至今還沒有被人打破。二○一四年十一月,克里夫蘭(Cleveland)冷颼颼的早晨,我陪伴五十七歲的里奇步出監獄,準備踏入一個與他過往所知相差甚遠的世界。一九七五年,俄亥俄州首次試圖入他死罪時,他才剛滿十八歲。
我也曾與雷蒙•托勒(Raymond Towler)一起坐在法庭裡,他同樣為了一宗他不曾犯下...
我的當事人里奇•傑克遜(Ricky Jackson)當初遭判的刑罰,用他的話來說,是「放上電椅處死」。雖然他在一九七○年代九死一生地逃過那張電椅,但仍然為了一樁他不曾犯下的謀殺罪,在牢裡度過了將近四十年──這項全國紀錄至今還沒有被人打破。二○一四年十一月,克里夫蘭(Cleveland)冷颼颼的早晨,我陪伴五十七歲的里奇步出監獄,準備踏入一個與他過往所知相差甚遠的世界。一九七五年,俄亥俄州首次試圖入他死罪時,他才剛滿十八歲。
我也曾與雷蒙•托勒(Raymond Towler)一起坐在法庭裡,他同樣為了一宗他不曾犯下...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第一章 大開眼界
•為什麼他們不承認自己犯了錯?
•從檢察官轉戰冤案救援律師
第二章 盲目的否認
•好人創造的「邪惡」之果
•認知失調
•行政之惡
•去人格化
•結論
第三章 盲目的野心
•結構上傾向有罪判決的體制
•法官
•警察與檢察官
•辯護律師
•陪審團
第四章 盲目的偏見
•錯誤的科學證詞
•預期中的「正確」答案
•緝凶的壓力扭曲專家對證據的觀察
第五章 盲目的記憶
•人類的記憶有些不可靠
•有關記憶的研究
•記憶與指認錯誤
•編碼、儲存和提取
•汙染與錯誤歸因
•證人錯誤指認...
第一章 大開眼界
•為什麼他們不承認自己犯了錯?
•從檢察官轉戰冤案救援律師
第二章 盲目的否認
•好人創造的「邪惡」之果
•認知失調
•行政之惡
•去人格化
•結論
第三章 盲目的野心
•結構上傾向有罪判決的體制
•法官
•警察與檢察官
•辯護律師
•陪審團
第四章 盲目的偏見
•錯誤的科學證詞
•預期中的「正確」答案
•緝凶的壓力扭曲專家對證據的觀察
第五章 盲目的記憶
•人類的記憶有些不可靠
•有關記憶的研究
•記憶與指認錯誤
•編碼、儲存和提取
•汙染與錯誤歸因
•證人錯誤指認...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