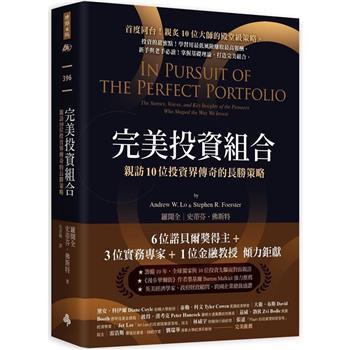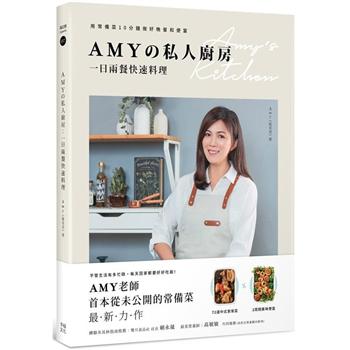圖書名稱:唯一的玫瑰
一場追尋愛與自我、重新體味人生的療癒之旅
紅髮法國女子玫瑰從未見過父親,她鬱鬱寡歡的母親偶爾會提及她父親的事,她的外婆則是絕口不提。對她而言,父親不過是母親捏造出的虛幻人物,從不存在。在母親與外婆相繼離世後,她失去了與這世界的所有連結,過著彷如行屍走肉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一通來自日本的電話:她父親過世了,她必須親身前往日本聽取遺囑。
玫瑰沒有多想便來到京都,並落榻於父親故居,在父親友人的照看下展開為期一週的旅程。溫婉傳統、打理父親生前起居的佐世子對玫瑰呵護備至,滿足她的一切需求,包容她所有孩子氣的舉動。寡言的司機寬渡負責載她參觀京都,雖然他總是保持著距離,卻總能容感受到他的善意與關懷。一再偶遇的英國老太太蓓詩.史考特,總是說著令人費解的話語,她究竟有何用意?謎樣的跛腳比利時男子保羅,與她聊著關於她父親的種種,帶她認識父親的舊識,兩人在朝夕相處之下,逐漸生出情愫……
在禪風庭園的一沙一石、一花一樹的環繞之中,在和食與日本人們的撫慰之下,玫瑰逐漸卸下渾身的尖刺,拋卻遭過往禁錮的自我,重新感受到愛與生命的喜悅,蛻變、綻放。
內容特色:
1.《刺蝟的優雅》作者最新作品,一則關於體驗生活的療癒故事。書末收錄繁中版作譯者對談。
2.透過京都風景的細緻描繪與庭園漫步、品茶、美食等等,書中細膩描寫女主角感受生活氣息、進而體驗世界,曾是哲學教授的作者在毫不長篇大論的纖細文字中,以細膩的五感(庭園風景之視覺與聽覺、品嚐日本料理與清酒之嗅覺與味覺、光線照耀肌膚的觸覺)描述女主角在生活的細節中體現「存有」、「臨在」與「活在當下」的實踐,並在一朵花之間看見世界的美好,透過一棵樹感受生命的氣息,從中成長、治癒心靈。
3.書中的氛圍與心靈療癒之旅或許會使人聯想到吉本芭娜娜的《蜜月旅行》或其他作品;異國自我追尋的情節或許有點像是哀愁版的《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但書中又充滿深刻的哲思,化為細膩觀察世界的優美文字;女主角在日式庭園出神漫走的橋段讓人想到電影《愛情不用翻譯》的某些片段。
4.本書亦會使人聯想一些闡述日式庭園與生活美學的書籍,但並非說理,而是透過故事主角的雙眼來觀看、透過她的體驗來演繹她所感受到的日式美學。
作者簡介
妙莉葉.芭貝里Muriel Barbery
1969年生,父母皆為法文教授。專攻哲學,後成為哲學教授,目前全心投入寫作。
2000年出版處女作《終極美味》,獲得不少讀者青睞,並榮獲2001年最佳美食文學類書籍獎,被譯為14國文字。
2006年出版《刺蝟的優雅》,沒有大力宣傳,卻藉由讀者的口耳相傳及眾多書商的支持,先後席捲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德國、韓國、美國等地,獲得高度支持及迴響,締造出版佳績。已翻譯的版本高達40種,全球銷售超過600萬冊。榮獲法國各項大獎,包括2006年Georges Brassens文學獎、2007年法國書商獎、2007年國際扶輪社獎,及2007年法國全民文化與圖書獎。
曾旅居日本、阿姆斯特丹,目前居住於法國羅亞爾河鄉間。
另著有《精靈少女》、《奇幻國度》(皆為商周出版)。
譯者簡介
周桂音
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博士。文字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九歌兩百萬長篇小說獎決選入圍、拍台北電影劇本徵選首獎等。譯有《少女與夜》等書。

 2021/05/08
2021/05/08 2021/04/18
2021/04/18 2021/02/24
2021/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