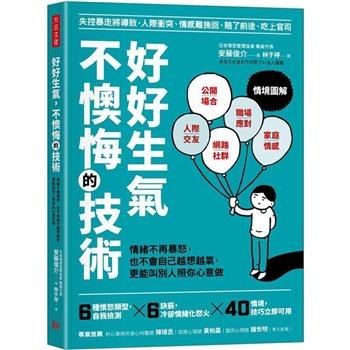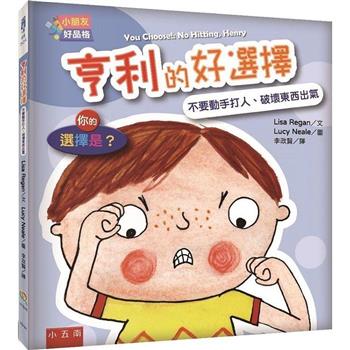目次
自序 紅萼有情春未老 I
導言 從他律到自律:《現代文學》在臺灣文學場域的歷史坐標 1
上 篇 情感結構與張力──冷戰時代臺灣社會場域
第一章 擱置「殖民」與「五四」爭議,文學開始「戰鬥」 17
第二章 現代主義思潮全球化與美援文化的象徵權力 35
第三章 知識分子的情感結構:在現代與傳統之間 59
中 篇 文學現代主義──場域實踐與再生產
第四章 精英場域的革命 73
第五章 學院行動者:從夏濟安到白先勇 97
第六章 都市裡的外來者:存在主義式的《臺北人》 111
下 篇 文學公共領域與現代藝術機制──「明星」咖啡館與臺北「文學界」
第七章 咖啡館作為「文學公共領域」的雛形與背景 127
第八章 「明星」咖啡館與六○年代臺北「文學界」 143
第九章 《現代文學》的審美現代性與自律創作 171
結語 文學自律的「想像」 185
參考文獻 189
索引 199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想像的文學共同體──文學現代主義在臺灣及其全球旅行的圖書 |
 |
想像的文學共同體──文學現代主義在臺灣及其全球旅行 作者:陳嬿文 出版社: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1-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華文文學研究 |
$ 288 |
華文文學研究 |
$ 288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想像的文學共同體──文學現代主義在臺灣及其全球旅行
本書從現代性的角度,試圖為臺灣文學場域釐清一段複雜的「文學現代主義時期」。前資本主義時期的臺灣,由於社會階層與專業領域的細化與分工,使現代性逐步躍入我們的視野,有關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話語,在時空的碰撞下產生了充滿張力的關係。而戰後,因應全球生產型態的變遷,現代主義思潮迎來了它在文化領域的全新實踐,新的表現形式改變了人類的文化與生活,其影響力迄今仍在延續。藉社會學家布赫迪厄之眼,我們不僅洞悉文化與權力之間糾葛的關係,在層層剝離政治與文學間「不當的沾粘」後,透過理論視角和歷史文本的梳理,提供一幅可供描摹、想像的,關於建構臺灣文學的未來圖像。
作者簡介:
陳嬿文
文藝學博士,籍貫臺南,生於臺北,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新加坡ISS INTERNATIONAL SCHOOL。旅居新加坡、南京、上海多年,現居臺灣。長期觀察多元文化在城市空間中的匯融與碰撞,兼具本土與國際視野。現為中學國文專任教師,專注研究與寫作。以中西方美學、現代主義思潮、臺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為研究專長。主要研究方向聚焦在戰後全球現代主義思潮,包括後現代、後殖民以及文化社會學發展迄今,仍存在矛盾且「未完成」的現代性問題。曾任職天下文化、聯合文學、印刻文學、e周刊等媒體及出版公司,擔任企劃、主編、記者。曾參與企畫多項重要藝文活動,包括「兩岸媒體新聞出版業圓桌論壇」、「臺北國際藝術節」、「臺北生活工藝大展」、「臺北國際書展」等。編輯心理勵志、社會人文叢書數十種,並主編《悠悠家園》、《蟬》、《何日君再來》(印刻)等文學叢書。文章見於兩岸雜誌刊物,包括產業報導、人物專訪、散文等,學術研究曾發表於《藝術百家》、《文藝報》、《南京大學報》等。
目錄
目次
自序 紅萼有情春未老 I
導言 從他律到自律:《現代文學》在臺灣文學場域的歷史坐標 1
上 篇 情感結構與張力──冷戰時代臺灣社會場域
第一章 擱置「殖民」與「五四」爭議,文學開始「戰鬥」 17
第二章 現代主義思潮全球化與美援文化的象徵權力 35
第三章 知識分子的情感結構:在現代與傳統之間 59
中 篇 文學現代主義──場域實踐與再生產
第四章 精英場域的革命 73
第五章 學院行動者:從夏濟安到白先勇 97
第六章 都市裡的外來者:存在主義式的《臺北人》 111
下 篇 文學公共領域與現代藝術機制──「明星」...
自序 紅萼有情春未老 I
導言 從他律到自律:《現代文學》在臺灣文學場域的歷史坐標 1
上 篇 情感結構與張力──冷戰時代臺灣社會場域
第一章 擱置「殖民」與「五四」爭議,文學開始「戰鬥」 17
第二章 現代主義思潮全球化與美援文化的象徵權力 35
第三章 知識分子的情感結構:在現代與傳統之間 59
中 篇 文學現代主義──場域實踐與再生產
第四章 精英場域的革命 73
第五章 學院行動者:從夏濟安到白先勇 97
第六章 都市裡的外來者:存在主義式的《臺北人》 111
下 篇 文學公共領域與現代藝術機制──「明星」...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