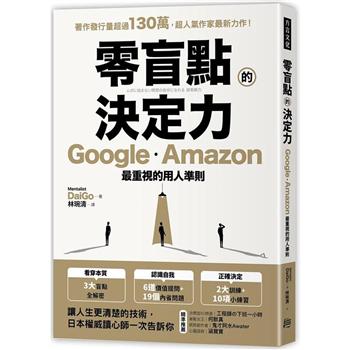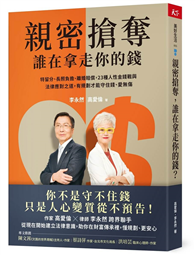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瘟疫與人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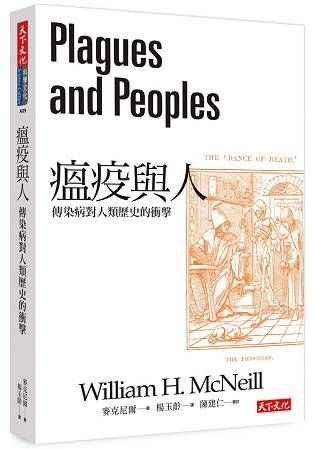 |
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作者:麥克尼爾 / 譯者:楊玉齡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10-2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316 |
微生物 |
$ 352 |
中文書 |
$ 352 |
西方歷史 |
$ 360 |
公共衛生 |
$ 383 |
健康醫療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人類實踐了太空旅行 卻擺脫不了傳染病的威脅
全球化消弭了疾病散播的界線 社群加深了恐懼
歷史不斷證明 政經情勢極有可能一夕劇變 人性面對更嚴格的試煉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SARS、伊波拉、流感病毒、H1N1……
瞭解 是處理恐懼最好的方式
「瘧疾」的兇暴,使莊嚴的朝聖之旅,化成疫病的溫床;
「霍亂」的版圖,藉交通便利的無國界化,再展新勢力;
「禽流感」的威脅,迫使高密度畜養的經濟方式,面臨挑戰;
生活在樹上的靈長類遠祖,因跳蚤和體蝨而搔癢不已;初踏上地面的人類祖先,由於大草原瀰漫的昏睡症而病懨懨;開始農耕的文明社群,遭血吸蟲症削弱了整體生產力;歐亞間的經濟貿易,致使天花悄悄跟著商旅隊伍進入新地域;蒙古大軍勢如破竹,將鼠疫散布歐亞大陸;西方帝國靠著無心傳染的天花,達成了殖民野心;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躍進,更是讓全球成為疾病大鎔爐。
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瘟疫與人》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析、鉅細靡遺的傳染病與文明交融史。
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是否能靠著現代公共衛生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瘟疫與人》一書中有最好的解答!
健康的社會來自於健康的個人,每一個人都是傳染病流行網上的一個節點。愈多人擁有來自自然感染或預防接種的免疫力,社會暴發傳染病流行的可能性就愈低。既然健康是權利而保健是義務,防疫工作自然是人人有責。了解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有助於體會防疫保健的己任。
——【審訂者】陳建仁,中華民國第14屆副總統、中研院院士(摘錄自本書導讀)
作者簡介
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
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40年,1987年退休。麥克尼爾教授史學著作豐富,超過三十冊,包括《世界史》(A World History)、《西方文明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人類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權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等。他所著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曾於1964年榮獲美國國家書獎,在歷史理論領域有顯赫的影響力。
審定者簡介
陳建仁
出生於香蕉王國的高雄縣旗山鎮,在家排行老七,個性爽朗、樂觀,喜歡大自然。 畢業於台灣大學動物學系、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班,專攻人類遺傳學及遺傳流行病學。 歷任台灣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所長、院長,以及中央研究院合聘研究員,借調出任國科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國科會副主任委員,現任行政院衛生署長。 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五次、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獎、教育部學術獎及國家講座、衛生署衛生獎章、台灣癌症基金會防癌研究傑出獎、台灣經典引文獎。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兩百餘篇,著有《流行病學》及《環境與健康》等書。 1989年獲選為美國流行病學學院海外院士、1993年獲選為院士。1998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譯者簡介
楊玉齡
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專事科學書籍翻譯、寫作。
著作《肝炎聖戰》(與羅時成合著)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台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合著)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
譯作《生物圈的未來》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消失的湯匙》獲第六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銀籤獎、《大自然的獵人》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小提琴家的大姆指》獲第七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雁鵝與勞倫茲》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另著有《一代醫人杜聰明》;譯有《基因聖戰》、《大腦開竅手冊》、《幻覺》等數十冊(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
| |||
|
|

 2017/05/21
2017/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