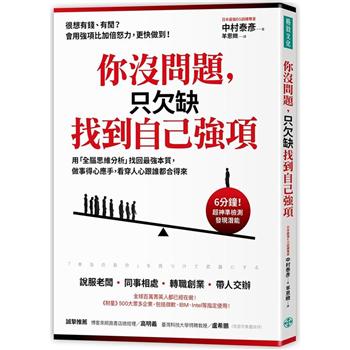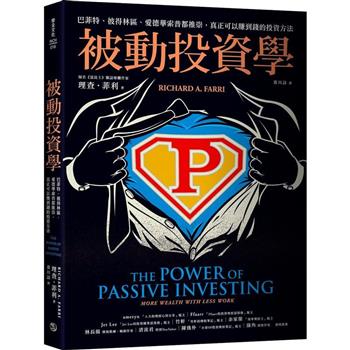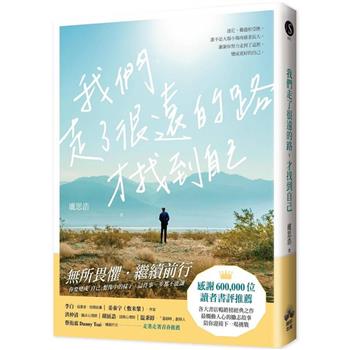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霧起霧散之際的圖書 |
 |
霧起霧散之際:文學卷冊 作者:齊邦媛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8-1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9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30 |
華文文學研究 |
電子書 |
$ 330 |
華文文學研究 |
電子書 |
$ 375 |
自然書寫 |
$ 395 |
現代散文 |
$ 395 |
文學 |
$ 425 |
文學小說 |
$ 425 |
文學小說 |
$ 425 |
小說/文學 |
$ 440 |
中文書 |
$ 440 |
華文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霧起霧散之際
本書是齊邦媛教授自一九四九年起,六十年來對臺灣文學重要作品的研究、整理、歸納及評論集成,兼及在國內外文學研討會宣讀的論文。
書中談到的幾十位寫者、評者、譯者,許多已在時間遷流中消失,或在現實世界的霧起霧散間只看見模糊的背影。
作者感悟到:不能任由書中這些人被遺忘,應該把他們帶到陽光照臨的地方,至少在他們二度漂流前,給世人看看他們活過的悲欣世界,和他們所創造的有血有肉的文學。
作者簡介
齊邦媛
一九二四年生,遼寧鐵嶺人,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一九四七年來臺灣。
一九六八年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
一九六九年出任中興大學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
一九八八年從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
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專刊(The Chinese Pen)總編輯十年。
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與文學評論多種,
引介西方文學到臺灣,
將臺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