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13 項符合
門孔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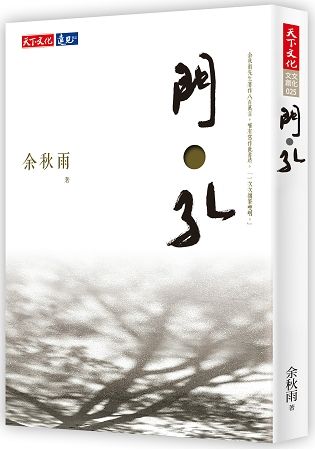 |
門孔 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1-1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8 |
二手中文書 |
$ 294 |
歷年誠品選書 |
電子書 |
$ 315 |
散文 |
電子書 |
$ 315 |
散文 |
$ 331 |
散文 |
$ 332 |
現代散文 |
$ 357 |
文學小說 |
$ 357 |
文學小說 |
$ 357 |
社會人文 |
$ 370 |
中文書 |
$ 370 |
現代散文 |
$ 378 |
現代散文 |
$ 37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此外,余秋雨先生亦將自己的母親與妻子寫入本書,文字雖簡單,讀起來情真意摯,格外令人動容。他說,不管走多遠,不管寫多少東西,重點還是一個小小的家庭,一個安靜的生活,一個被安頓住的自我靈魂。
余光中:「比梁實秋、錢鍾書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舉重若輕。」
白先勇:「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嚴又一次喚醒了。或者說,他重鑄了唐宋八大家詩化地思索天下的靈魂。」
作者簡介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
在中國大陸的文革災難時期,以戲劇為起點,針對當時的文化極端主義,建立了《世界戲劇學》的宏大構架,于文革後出版,至今三十餘年仍是這一領域唯一的權威教材,獲中國大陸「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同時,又以文化人類學的高度完成《中國戲劇史》,以美學的高度完成了中國首部《觀眾心理學》,並創建了自成體系的《藝術創造學》,皆獲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推舉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並出任上海市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曾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
二十多年前毅然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孤身一人尋訪中華文明被埋沒的重要遺址,之後冒著生命危險貼地穿越數萬公里考察了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克裡特文明、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遺跡,是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現場抵達的人文學者。在考察過程中寫出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書籍,開創「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獲得兩岸三地諸多文學大獎,並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籍暢銷排行榜前列。
近十年來,他憑藉著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資源,投入對中國文脈、中國美學、中國人格的系統著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雜誌等機構讚譽不斷,表彰他「把深入研究、親臨考察、有效傳播三方面合於一體」,是「文采、學問、哲思、演講皆臻高位的當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聯合國中國書會講授「中華宏觀文化史」、「世界座標下的中國文化」等課題,每次都掀起極大反響。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秋雨書院」院長、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