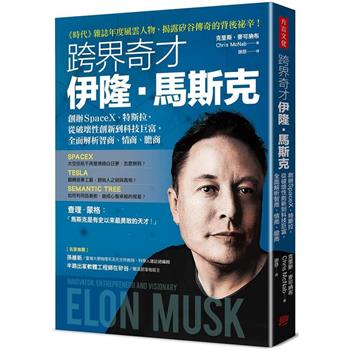希望每一位醫學院的學生,除了領到白袍、聽診器……
還能領到歐迪許醫師寫的這本書。
——《紐約時報書評》
作者用獨特的視角,揭露醫療的勝利與失誤。
此書真誠、有力,是我讀過最勇敢的一本書。
作者描寫自己如何從醫師變成病人,甚至瀕臨死亡……
精采至極,讓人想一口氣讀完。
—— 李奧納德.貝瑞(Leonard L. Berry),
醫療照護改善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資深研究員
蕾娜.歐迪許醫師懷孕七個月,因劇烈腹痛被家人送去急診,
沒想到就此踏上一條瀕死之路──身上的血幾乎流光、
肚子裡的寶寶沒能存活、
先後歷經三種休克:失血性休克、敗血性休克、過敏性休克。
她在鬼門關前轉了幾圈,奮力求生,終於走向康復之路。
她從醫師變成病人之後,才發現醫護人員往往用冷漠的眼神、疏離的態度,
來看待病人所承受的痛苦與折磨。
她察覺這種孤傲、自我保護的心態,已是醫學訓練的一部分。
歐迪許醫師歷經九死一生之後,用獨到的視角、詩意的文筆,
與讀者分享她的真實經歷。除了暴露醫療體系的失誤與弱點,
也提出一個新方向:醫師應如何發揮同理心,與病人溝通,
如何與病人建立真誠、互相信賴的關係。
歐迪許的醫師的故事不只扣人心弦,也呼籲我們一起行動,
發動醫療革命,建立富有同理心的醫療文化。
—— 萊特.拉瑟特三世(Wright Lassiter III),亨利福特醫療體系總裁兼執行長
本書是令人驚嘆之作……文字優美,以智慧之眼洞視疾病,
告訴我們如何與病人溝通,並建立情感連結。
歐迪許醫師的勇氣、韌力與熱情,令人動容。
—— 傑佛瑞.米爾斯坦(Jeffrey Millstein),賓州大學醫療體系(Penn Medicine)醫師
非常重要的一本書。
這本書完全改變了我,讓我變成不同的醫師。
—— 韋斯頓(Gabriel Weston)醫師,《血紅:一個外科醫師的故事》(Direct Red: A Surgeon's Story)作者
歐迪許醫師的故事,讀來就像醫療版的《奧迪賽》。
她洞視醫療的本質,並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 湯姆.李(Tom Lee),普瑞斯甘尼醫療服務顧問公司(Press Ganey Associates, Inc.)醫務長
這是一本讓人心痛、同時又對生命充滿信心的書。
—— 琳恩.費林(Lynn E. Fiellin)醫師,耶魯大學醫學院兒童研究中心副教授
作者簡介:
蕾娜.歐迪許Rana Awdish
美國亨利福特醫療體系(Henry Ford Health System)加護病房主治醫師,內科、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專科醫師、肺動脈高壓治療中心主任,也是該體系的照護經驗計畫醫務主任。獲選2016年度最佳加護照顧指導老師,曾入圍2017年史瓦茲中心(Schwartz Center)年度仁心獎。她的文章見於《新英格蘭醫學期刊》、《學術醫學》(Academic Medicine)期刊等。目前與丈夫和兒子住在密西根北村(Northville)。家裡還有一隻很老的虎斑貓。
譯者簡介:
廖月娟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曾獲誠品好讀報告2006年度最佳翻譯人、2007年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2008年吳大猷科普翻譯銀籤獎。翻譯生涯逾二十年,作品近百冊,期許自己畢生以「科學的熱情和詩之精確」來翻譯。近期醫學譯作包括《凝視死亡》、《臨終習題》、《外科大歷史》、《端粒效應》、《無麩質飲食》等書。
章節試閱
病醫應共享醫療決策
長久以來,醫師皆預設怎麼做對病人是好的,但這點已經有了改變。到了我上醫學院的時候,醫療範式已從父權式的「醫師最了解該怎麼做」轉移到共享決策。但這個新架構仍偏向醫師的建議。身為年輕醫師,我們學到的是,我們擁有的知識使我們得以為病人描繪可能的路徑,但病人最後仍需自己做決定。言外之意是,仍有一個「最佳選擇」,如果病人不這麼選擇,或許是因為你沒盡力說服病人。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最知道,必然會有所主張。
我們傾聽的訓練還不夠。
我們所受的訓練是問問題,藉由問題引導病人到某個目的地。但我們不知道「自己怎麼問,病人就會怎麼答」,我們沒能洞視問問題的盲點,我們只是把問題當成圍欄,把答案像牲畜圈養起來,使之成為可管理的牧場。於是我們得到的答案,剛好符合某種病症的勾選框。
「最近,我常覺得胸口不舒服,」病人說。
「這種不舒服是重物壓迫的感覺,還是刺痛?」住院醫師問。
「我想,比較像重物壓迫感……」
「這樣有多久了?」
「看情況。如果休息,就覺得好多了……」
「這種感覺會持續多久?幾秒或者幾分鐘?」
「嗯,有時候持續幾分鐘。」
之後,我們就能向主治醫師報告。我們很公式化的陳述:「病人主述胸口有重物壓迫感,常持續幾分鐘,如果休息,症狀就會減輕。」我們很快就蒐集好這些乏味的資料,不需要語境。我們知道,萬萬不可從好奇的角度提出開放性的問題。我們的訓練崇尚效率,而非透過信賴和坦誠建立關係。我們的訓練不要求我們重視病人的故事。
如果病人的講話不被打斷、語境豐富,這樣的敘述能告訴我們什麼?「最近,我覺得胸口不舒服。我先生得了帕金森氏症,自從他的病情惡化以來,我更常這樣。現在,他很多事情都做不到,都要依賴我,像是洗澡、穿衣服、下車。他實在很重。我必須扶著他的時候,就會覺得胸口有重物壓迫的感覺。我很擔心,萬一我出了什麼問題,他怎麼辦?我們沒有孩子。我害怕自己心臟病發,一時沒扶好,差點讓他摔跤。」
好好聆聽病人述說,意謂願意放棄掌控,讓病人暢所欲言。醫師失去控制權可能帶來風險,而風險本身代表某種程度的脆弱。可是本來,提出問題就是允許自己不知道答案。如果我們不去掌控訊息的流動,就能讓真實的歷史浮現。虛心聆聽就是放棄自己的假設,為真相挪出空間。真相也許比較複雜,但能使我們更深入了解病人,知道他們的價值觀、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只有在重視答案的文化中,我們才知道問題的價值。
其實,如果提出值得思索的好問題,由此得到誠實的答案,醫師也能鬆一口氣。想像你的病人剛得知自己得了癌症,你必須提供選擇方案,看是建議病人接受化療、放射線治療、或者安寧緩和醫療。你知道每一種選擇都有其優點、風險、副作用、以及可能出現的併發症。例如,你知道化療會讓病人很痛苦,難以忍受,在最好的情況下,只能讓生命延長三個月;你知道放射線治療比較不會那麼痛苦,但是頂多只能讓病人多活一個月;你知道病人最後可能死於呼吸衰竭,如不好好因應及處置,將是緩慢的折磨。你也許心中出現衝突,不知道該給病人什麼樣的建議才好。身為醫師,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以實際的知識做為根據,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重大病症,你是否想要討論可供選擇的治療方案,看如何能延長生命?」不管病人的價值觀為何,聽到的都是接受化療,存活機率最大。
但如果醫師這樣跟病人討論:「很遺憾,這就是診斷結果。我知道我們已經談過預後的情況,那必然是一場硬仗。我們是否可以談談,從現在起,到生命結束之前,不管能再活多久,你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病人甲可能會說:「我希望我的家人知道,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設法戰勝癌症。如果某個臨床試驗能使我的存活率增加百分之一,拜託,請讓我加入。再怎麼辛苦,我都願意。」病人乙或許這麼說:「我看著我母親死於癌症。治療讓她痛苦不堪,我常常希望她能放棄。對我而言,平靜安心過日子最重要,我不希望家人看我受苦。」如果提出恰當的問題,你給病人的建議就能符合他們的價值觀。由於這樣的提問和建議,建立在同理心和以病人為中心的敘述之上,因此可能使人獲得心靈上的療癒。
同心圓理論:情緒垃圾應向外丟
在我住院期間,不斷有人跟我說那晚(就是我幾乎死掉的那個晚上)有多糟——這就像重複出現的噩夜主題曲。
某天,產科住院醫師走進來的時候,一開始我沒認出是他。我上次看到他,是一個星期以前的事。他右眼淤青,變成貓熊眼,半邊臉扭曲了。我想起我開刀那晚,他被點滴架撞個正著。
就是那個「你能告訴我,你是怎麼看出來寶寶沒心跳的嗎?」的住院醫師。
他坐在角落。
「嗯,對我來說……那晚真的很糟,」他斷斷續續說。我看著他。我發現他停頓下來是為了努力讓淚水不流出來。他咬嘴唇,抽噎了一下。那麼多人在這裡進進出出,唯獨他一人在我面前強忍淚水。為什麼是他?
「我本來在神經內科接受訓練,後來轉到產科,因為覺得產科一天到晚在接生,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喜悅,」他說。
我覺得沮喪。我想,接下來的談話會讓我痛苦。我嘆了一口氣,按了一下自控止痛器的按鈕,給自己一劑嗎啡。頭幾天,其實我不覺得自己很可憐。對我來說,能逃過一劫,大難不死,已是天大的幸運。從那時起,我想像全世界的不幸和苦痛,都從醫院大門流出了,相形之下,我個人的痛苦已微不足道。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運。然而,我也有一顆靈敏、很會精算的腦袋,可以計算我眼前每一個人的痛苦。我不免發現,跟我比,他們差得遠了。
我還發現他們違反了同心圓理論。我最初是在《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看到這個理論。作者是席爾克(Susan Silk)和高德曼(Barry Goldman)。這個理論旨在說明碰到危機時,對人訴苦的規則。想像一個同心圓,最中間的那個圓代表病人,我就是一個例子。再大一點的圓則是家屬,他們也會被疾病和喪親影響,例如蘭迪和我媽。再往外一個圓則是其他親戚、朋友等。最外一個圓則是點頭之交。在中心那個人最不幸、也最脆弱,因此可以隨時隨地向任何人抱怨、哭訴、甚至詛咒上天。這是被困在中心那個圓唯一的好處。此人可以向外圈的人抱怨,但外圈的人不能對內圈的人訴苦。每一個人都能說出自己的感受,如何受到創傷的影響,但只能對外圈的人訴說。規則很簡單:安慰往內送,情緒垃圾向外丟。
例如,我可以自憐自艾,像是說:「大家都在期待寶寶的到來,我卻讓每一個人失望了。」
家人不能對我說:「我們都很期待寶寶的到來。這真是個噩耗。」
但那時,似乎每個人都把情緒垃圾丟給我。
「不只是你,」住院醫師解釋說:「前一晚也很糟,有孕婦死亡。你算幸運了。」
我看著蘭迪。我因為打了麻醉止痛藥昏昏的。
蘭迪可不像我,他隨時準備出拳的樣子。蘭迪後來說,他沒出手是因為那個住院醫師眼睛淤青,看起來就像被人揍了。
「不會一直這樣的。不幸的只是少數,大多數還是有好的結局。」我沒辦法,只能這樣安慰這個住院醫師。不是因為我無私,只是我看著他,好像看到一頭鹿不知怎麼跑到馬路上,嚇得無法動彈。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撞上去。他神情沮喪。身為醫師,我也有類似的經驗,像被剖心挖肺。當然,我當時也把情緒垃圾往內倒。我記得我曾跟病人說:「你昨晚真的嚇死我了。」現在回想起來,自我中心就像一塊布,在我眼前撕裂開來。
你真的嚇死我了。
對我來說,那晚實在很糟。
我再也不會說這種話了。
住院醫師點點頭,走出去,肩膀挺直了一點,不像方才進來那樣垂頭喪氣。蘭迪氣沖沖,說道:「他好意思向我們訴苦?」我聳聳肩、搖搖頭。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才能真正同情他。但在那時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跟他的主治醫師約了時間,抱怨他的白目。那位主治醫師就是當初為我檢傷那位。他是個中年人,人很親切,目光炯炯有神。他認真聽我訴說,點點頭。因為他點頭,我認為他同意我說的,了解那位住院醫師犯的錯。可是接下來,他卻滔滔不絕論述醫療體系的問題,如何讓醫師受到屈辱,也幫年輕醫師說話,說他們的負擔多大。我們給他們極大的壓力,期待他們像超人一樣。我想,我們就像雞同鴨講。我希望看到憤怒,想聽到他說他會好好指導那位住院醫師。但他卻表示他對那位住院醫師深表同情,也鼓勵我這麼做。結果,我走出他的辦公室時,手上多了幾本有關正念和感恩力量的書。當時,我不了解他的立場。當然,醫療職場是高壓工作環境,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被塑造出來的。能在壓力底下存活、茁壯的人,才適合這樣的環境;會對病人哭訴、自憐自艾的醫師,恐怕不適合幹這行。我們不能脆弱、不能在病人面前崩潰,病人需要的是剛強的我們。那時,我的信念約莫如此。
我們攻擊別人的地方,通常也是自己最糟的部分。我們對別人的過失或缺點,經常反應激烈,因為那正是最讓我們羞愧的事。那個產科住院醫師允許自己感受悲傷,我卻不讓自己這麼做。他會來到我的病房,在我面前哭泣,也許是因為他沒有適當的管道可以發洩悲傷,最後才這麼做。他覺得很難過,也坦承自己有多麼沮喪;我則一段時間之後,才允許自己這麼做。那時,我沒能透過他洞視自己。大概是命運安排,我不時遇見他,最後我才了解我們其實比較相像。我該同情他,也該憐憫自己。
病醫應共享醫療決策
長久以來,醫師皆預設怎麼做對病人是好的,但這點已經有了改變。到了我上醫學院的時候,醫療範式已從父權式的「醫師最了解該怎麼做」轉移到共享決策。但這個新架構仍偏向醫師的建議。身為年輕醫師,我們學到的是,我們擁有的知識使我們得以為病人描繪可能的路徑,但病人最後仍需自己做決定。言外之意是,仍有一個「最佳選擇」,如果病人不這麼選擇,或許是因為你沒盡力說服病人。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最知道,必然會有所主張。
我們傾聽的訓練還不夠。
我們所受的訓練是問問題,藉由問題引導病人到某個目的地。但我們不知...
作者序
【前言】
在我貼近死亡之後
我們走進她的病房。病房黑黑的。她在睡覺,經歷恐怖的一夜,她的身體還在設法恢復,因此我們不敢開燈吵醒她。即使她醒了,因為肺部疾病嚴重,她說話氣若游絲,斷斷續續,一次也只能說一、兩個字。
一早,我已來看過她,感覺得到她因呼吸愈來愈困難,心中充滿恐懼。最近,她就連坐著,都很吃力。她清醒的時候,幾乎都在禱告。我靜靜坐在她身邊陪她。我知道她的日子不多了,想跟她討論這個現實。每天,比起成功移植,「萬一」的情況似乎比較可能發生。我想,是該跟她好好談談了。她與我四目相接,露出微笑。這個月新來的住院醫師還沒寫好卡片,讓她覺得失望。她說:「我只是想要知道,他們與我一起懷抱希望。」我低下頭,不敢看她。我想,我心有愧疚,因為我預期她能存活的時日所剩無幾。
她把護貝、裱框的彩色照片,掛在牆上,讓病房有家的味道。照片上的她,很驕傲的和家人站在一起。這些照片就是這位病人給醫療團隊的第一印象,告訴大家她的身分與生活——這才是真正的我,不是現在躺在病床上的我。
我轉向深藍色的牆面,上面貼了許多寫了鼓勵話語的白色卡片。我靜靜的讀。
佩服你的決定、力量和信仰。謝謝你讓我陪你踏上這條希望之路。
在我認識的人當中,你是最勇敢的。
我希望我能在另一邊看到你,看你恢復健康,自由呼吸。
我們走出病房,思索那些卡片上的字。如果病人已瀕臨死亡,我們還是該滿懷希望、全力支持嗎?我們是否該把希望放在首位,提供病人生存所需的高科技醫療照護?我相信,我們該這麼做。這些卡片讓她看到,我們每一個人都認同、支持她的想法。我們看到她的痛苦,也知道她的恐懼。我們寫下希望的話語,是為了與她一起想像未來的種種可能:不只是可能的結果,而是盡可能去擴展可能性。
一位住院醫師認為,幫她寫卡片一事,可能是一種交換。「我想到了,所以我們給她需要的東西,反過來——」
他在這裡打住,那位剛值完班的住院醫師接著說:「不是,她要我們看到真正的她,一個正在接受治療的人,而非只是生病的她。」我覺得他的描述很棒。他接著說:「這些卡片可以讓人看見希望。」
「哇!」這樣的話讓我驚奇。「想想看,我們今天做的,就是讓人看見希望……」我不知怎麼把話說完。
護理師點點頭,接嘴道:「那就是成功了。」
「嗯,是的,還有及時接受肺臟移植啊!」另一位住院醫師冷冷的說。
其他人呵呵笑,像一群惡作劇的小孩。我了解他們的不安。
我知道,我們重視治療、重視目標,我們希望得勝。處於痛苦的灰暗地帶,令我們難受。我們擅長複雜而精確的治療,因為這是我們拿手的,做來似乎很輕鬆。至於同理心的表現,反倒比較困難。我記得有一次,一位病人淚流滿面問我:「為什麼會這樣?」我向她解釋,她的末期病情應該是源於遺傳、環境、行為、體質複雜的交互作用。受過訓練的我相信,要回答所有的問題都得看數據。因為這種傾向,我忽視了恐懼和存在的問題。多年以後,我才了解問題沒那麼簡單,後面還有更深層的問題。儘管我知道這是和病人建立信賴關係的機會,我仍不相信只是陪伴、只是見證病人的痛苦,就能有療癒的力量。我太不重視無形的東西及互相了解的時刻了。
我依照醫學院的指導,與病人保持距離,就像團隊現在做的。我遵循老師立下的典範去做,給自己空間,保護自己。老師說,跟病人太親近,如果病人情況不好或不幸死亡,就會難受,甚至有希望幻滅、油盡燈枯之感。依照這樣的說法,我像是可量化的東西製成的,一旦拿出什麼給別人,自己就會變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相信那種模式,但在我從醫師變成病人之前,我不允許自己毫無保護,也不願大方掏出自己給別人。我不了解開放的溝通管道可為我補充不足。我不明白同理心其實是一種互惠的關係。
在我貼近死亡之後,我才了悟這樣的道理。
【前言】
在我貼近死亡之後
我們走進她的病房。病房黑黑的。她在睡覺,經歷恐怖的一夜,她的身體還在設法恢復,因此我們不敢開燈吵醒她。即使她醒了,因為肺部疾病嚴重,她說話氣若游絲,斷斷續續,一次也只能說一、兩個字。
一早,我已來看過她,感覺得到她因呼吸愈來愈困難,心中充滿恐懼。最近,她就連坐著,都很吃力。她清醒的時候,幾乎都在禱告。我靜靜坐在她身邊陪她。我知道她的日子不多了,想跟她討論這個現實。每天,比起成功移植,「萬一」的情況似乎比較可能發生。我想,是該跟她好好談談了。她與我四目相接,露出微笑。這個...
目錄
合作出版總序 樹立典範 黃達夫
前 言 在我貼近死亡之後
第 一 章 惡寒
第 二 章 虛空
第 三 章 烏雲
第 四 章 無語
第 五 章 阻礙
第 六 章 巧
第 七 章 拆彈
第 八 章 暗影
第 九 章 蛻變
第 十 章 新生
第十一章 復發
第十二章 迴響
附錄 病醫溝通技巧——病醫關係可以做得更好
誌謝
合作出版總序 樹立典範 黃達夫
前 言 在我貼近死亡之後
第 一 章 惡寒
第 二 章 虛空
第 三 章 烏雲
第 四 章 無語
第 五 章 阻礙
第 六 章 巧
第 七 章 拆彈
第 八 章 暗影
第 九 章 蛻變
第 十 章 新生
第十一章 復發
第十二章 迴響
附錄 病醫溝通技巧——病醫關係可以做得更好
誌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