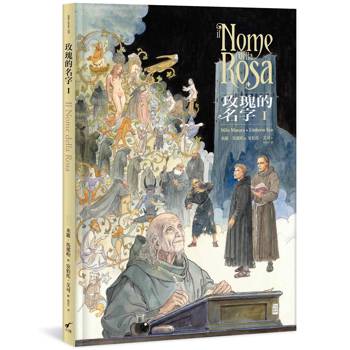川普掀起的反民主風潮,讓世界秩序搖搖欲墜;
當強權大國跨越道德的界線,我們未來的路該怎麼走?
在國家利益與全球公益之間,強國領導者如何抉擇?
「情緒智商」和「情境智商」是極大關鍵!
在好萊塢電影裡總能看見美國以強權者的角色維護世界正義,展現獨有的美國精神。而美國人民也經常針對總統及其外交決策做出道德評斷,不幸的是,許多評估都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奈伊在《強權者的道德》中,針對1945年以來14位總統的外交政策進行精闢分析,透過意向、手段、結果這三個面向來評估道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根據奈伊的計分卡來評斷歷屆美國總統在外交政策上,道德與有效性的表現,評斷如下:
前段班:小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老布希
中段班:雷根、甘迺迪、福特、卡特、柯林頓、歐巴馬
後段班:詹森、尼克森、小布希、川普(任期未完觀察中)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總統始終具有領導才能和影響力。但川普上任後,將民粹主義運用到外交政策上,隨著中國崛起,以及其他國家民族主義式的民粹主義興起,自由國際秩序已經結束。
對未來的美國總統來說,領導力所涉及的道德抉擇勢必變得更加重要,也攸關世界局勢的平穩與動盪。而臺灣在未來以合作為主軸的全球秩序中,也必須從道德面向認真思考我們的外交政策。
專業推薦
奈伊的著作常常有發人深省的地方。《強權者的道德》不僅帶領讀者回顧過去七十幾年來,美國外交政策的利弊得失,更重要的是透過歷史故事,讓我們確認「道德思考」才是決定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因素。凡是欠缺道德勇氣,或是魯莽躁進,不知如何審慎選擇手段、不知如何達成崇高目標的政治人物,都無法贏得後人的尊重與懷念。──江宜樺,前行政院長,國立中正大學紫荊講座教授
在現今這樣的時代,理解道德推理在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在民主國家尤其是如此,畢竟在民主國家中,持續參與全球事務,是需要公民支持的。奈伊是分析美國外交的重量級學者之一,在這本書中,他提供了清晰的指引,讓我們得以重新校正道德指南針。──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阿斯彭研究所前執行長,杜蘭大學歷史學教授
從美國外交政策思想家泰斗的視角,對國內民粹主義政治提出強烈警告,民粹主義不僅窄化了我們的道德視野,並且破壞了美國在全世界的領導地位。──文安立(O. A. Westad),耶魯大學教授
憑藉獨特的洞察力與精確性,奈伊提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道德應該如何形塑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他完整回顧歷任總統如何接受或拒絕道德上的要求,並建構有效的計分卡來評斷未來的總統。隨著愈來愈多以美國為首的國家赤裸裸的將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使得本書具有更重大的意義。──葛根(David Gergen),CNN高級政治分析師,哈佛大學甘迺迪管理學院公共領導中心創始主任
在《強權者的道德》中,奈伊極具說服力的指出,在外交政策中,良好的意圖必須伴隨著適當的手段,才能產生有益的結果。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歷任總統的巧妙分析,顯示「情境智商」是道德原則能否產生良好結果的關鍵因素。──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對於道德在美國總統制定外交政策時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清晰、周到、有創意的檢視。奈伊教授在這本可讀性極高的書中令人信服的揭示,領導者與公民做出的假設、決定和判斷,都反映出他們自身對於是非善惡的看法。他再次為我們能更深入理解國際關係做出了重大貢獻。──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牛津大學國際歷史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