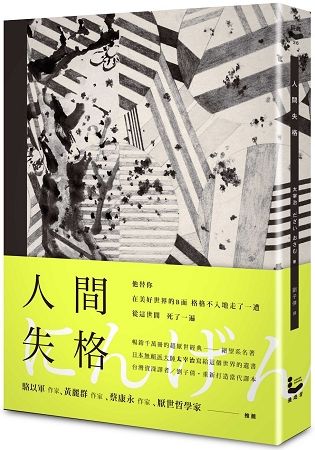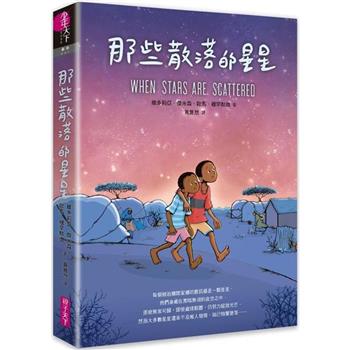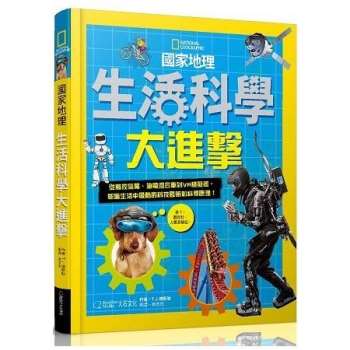厭世文豪太宰治寫給這個世界的遺書
日本無賴派大師暢銷千萬冊的代表作
台灣資深文學小說譯者劉子倩重新打造新世代譯本
絕美陰鬱的無聲吶喊 逃離他人眼光的向下沉淪
他帶你行經痛苦折磨 肆意放縱墮落 掩蓋無聲吶喊
在他人目光下赤身裸體般艱難邁步 不服卻也無力抵抗
他替你 在美好世界的B面 格格不入地走了一遭
從這世間 死了一遍
#Goodbye那些所謂的日常正軌
1948年6月13日深夜,就在完成《人間失格》的數月後,在東京近郊三鷹、當時依舊湍急的玉川上水,太宰治跟情婦山崎富榮在身上緊緊繫上紅繩,投水自殺。太宰治放棄了短暫絢爛的文豪生涯,完成了一開始對富榮所說的「談一場到死為止的戀愛」,結束了長期沉溺女人、酗酒的心理紊亂跟久病纏身的痛苦折磨,拒絕走上《人間失格》裡那個白髮蒼蒼、面目模糊的人生終途。
#寫給難以明瞭的世界的遺書
太宰治短短一生中創作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帶著自身經驗的痕跡。像是描寫沒落貴族、大受歡迎的《斜陽》就是以青森望族津島家為背景,書中主人公也以情婦太田靜子為本。而《人間失格》更是截取太宰治人生多處段落,在大家族裡服從規矩、符合旁人想像的成長經歷,到東京參加共產黨團體,跟女學生一起殉情卻獨自活下來,或是沉溺菸酒、女人、濫用藥物的自我放逐。他藉主角葉藏之口,反覆著自我剖析、自我批判,然後自我厭惡的過程,到最後失去身而為人的資格(人間失格日文原意)。無論對這世間再怎麼恐懼,再怎麼格格不入,在最後一刻仍想向眾人剖白。
#膽小鬼變成了小丑
在殉情、混亂的女人關係、酗酒、藥物上癮等看似激烈的劇情轉折下,瀰漫《人間失格》全書的其實是葉藏幾乎無可救藥的人際關係過敏症。身為大家族中的一份子,凡事都得照規矩,違背他人期待就會招來責難,葉藏從小就對人懷抱極深的恐懼,害怕人在盛怒之下偶爾流露出的真面目,為了掩飾自己,他搞怪又搞笑,用丑角包裝自己,但心裡又責備自己滿口謊言,裝模作樣。即使到成年後,這種模式還是不斷重複、延續,他無法信任他人,連那些因為他外貌俊秀願意付出一切的女人們也不例外,「膽小鬼連幸福都害怕」,他打從心底認為自己是「見不了光的人」。
#前方若有擋路的石頭,蟾蜍會繞路而行
就算對人抱持著巨大的恐懼,卻無法真正死心,這是葉藏的悲劇可說源自於此。他用名為搞笑的殼包覆住自己,又忍不住偷偷伸出觸角,卻被無情斬斷。「酒、香煙、妓女,那都是能夠緩解我對人的恐懼(哪怕只是一時片刻),暫時轉移注意力的好手段。為了尋求那些手段,我甚至覺得就算叫我變賣全部家當也無怨無悔。」家人跟他斷絕關係、唯一的朋友在他沒錢後的鄙視、同居女人的孩子說的無心之言,妻子被侵犯⋯⋯都讓他的敏感纖細終究不堪負荷,一再走向了逃避。
#通往封閉心靈的縫隙
三島由紀夫曾批評太宰治說,他性格上的缺點起碼有一半可以用冷水擦澡、做體操跟規律生活治好。但太宰治的內心細膩脆弱,又飽受身體上的苦痛折磨(二十多歲就因腹膜炎開刀,術後數月不能動彈,後來又藥物上癮,死前肺結核日益嚴重),《人間失格》像是他對自己的最後懺悔,更帶著無數的疑惑不解。讓人不禁想問,那些習以為常、有時用謊言跟面具包覆的人情世故都該配合演出嗎?敏感、懦弱、逃避這些特質真那麼負面到只能捨棄嗎?或許這些問題永遠都找不到標準答案,但跟著《人間失格》終能窺探封閉心靈的一二。
名人推薦
作家駱以軍、作家黃麗群、作家蔡康永、厭世哲學家 推薦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人間失格【精裝典藏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人間失格【精裝典藏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太宰治(1909-1948)
本名津島修治,日本無賴派文學大師。出生於日本青森縣津輕郡的大地主津島家,父親源右衛門入贅津島家後,投入政治生涯,官至貴族院議員。太宰治手足眾多,共有十一人,他在家中排行倒數第二。十四歲時父親因肺癌去世,進入中學後成績優秀,喜愛芥川龍之介、菊池寬等作家,讀了井伏鱒二的短篇小說〈幽閉〉(後改寫為山椒魚)更是興奮不已。十八歲,得知芥川龍之介自殺消息倍受衝擊。十九歲時編輯發行同人誌《細胞文藝》,受普羅文學影響,發表〈無限奈落〉。二十歲服藥自殺未遂。
二十一歲時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系,並拜入心儀許久的小說家井伏鱒二門下。後因欲與藝妓結婚以及參與共產黨活動,被分家除籍,同年與咖啡廳女服務生服藥自殺。二十六歲發表短篇〈逆行〉,於鐮倉上吊自殺未遂,後因腹膜炎入院開刀。同年入圍第一屆芥川賞,最終落選。二十九歲出版短篇小說集《晚年》,後以《女學生》獲第四屆北村透谷獎。他四次自殺未遂,最後於三十九歲,和情婦於玉川上水投水自盡。
太宰治短短一生中創作了三十多部小說,早期包括《晚年》、《虛構的徬徨》、《二十世紀旗手》等深受注目。在他戰後的作品中,《維榮之妻》、《斜陽》、《人間失格》等被視為是代表作,引起無數年輕人共鳴,其中的《斜陽》與《人間失格》更堪稱是日本戰後文學頂尖作品。
繪者簡介
劉文瑄
台灣視覺藝術家,目前於台北創作、生活。
2007年於美國舊金山藝術學院畢業後,進入紐約市立大學杭特學院藝術研究所。2016年,入圍香港Sovereign傑出亞洲藝術獎決選。作品於各大美術館及藝術空間展出,包括澳洲雪梨白兔美術館,北京中國美術館、布達佩斯德維格當代美術館、荷蘭CODA美術館、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台灣美術館、臺北伊通公園(IT PARK)及亞洲雙年展等。藏家遍及歐美、亞洲各地。
創作形式涵蓋空間裝置、平面、攝影、錄像、植栽等,以探索塗畫(Drawing)在日常生活中找尋其開放性與自由,嘗試透過不同的手法建構再重構。
本書收錄作品出自「對畫」系列,以京都傳統水墨畫為基底,其上用鉛筆在既有的圖畫空間中恣意漫遊,揉和東西不同的筆觸與意趣,在畫紙上展開一場傳統書畫與當代的對話。
譯者簡介
劉子倩
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有小說、勵志、實用、藝術等多種書籍,包括谷崎潤一郎《陰翳禮讚》、太宰治《女生徒》、江戶川亂步《兩分銅幣》、夏目漱石《我是貓》、吉本芭娜娜《廚房》、《馬戲團之夜》、又吉直樹《火花》等日本文學作品。
太宰治(1909-1948)
本名津島修治,日本無賴派文學大師。出生於日本青森縣津輕郡的大地主津島家,父親源右衛門入贅津島家後,投入政治生涯,官至貴族院議員。太宰治手足眾多,共有十一人,他在家中排行倒數第二。十四歲時父親因肺癌去世,進入中學後成績優秀,喜愛芥川龍之介、菊池寬等作家,讀了井伏鱒二的短篇小說〈幽閉〉(後改寫為山椒魚)更是興奮不已。十八歲,得知芥川龍之介自殺消息倍受衝擊。十九歲時編輯發行同人誌《細胞文藝》,受普羅文學影響,發表〈無限奈落〉。二十歲服藥自殺未遂。
二十一歲時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系,並拜入心儀許久的小說家井伏鱒二門下。後因欲與藝妓結婚以及參與共產黨活動,被分家除籍,同年與咖啡廳女服務生服藥自殺。二十六歲發表短篇〈逆行〉,於鐮倉上吊自殺未遂,後因腹膜炎入院開刀。同年入圍第一屆芥川賞,最終落選。二十九歲出版短篇小說集《晚年》,後以《女學生》獲第四屆北村透谷獎。他四次自殺未遂,最後於三十九歲,和情婦於玉川上水投水自盡。
太宰治短短一生中創作了三十多部小說,早期包括《晚年》、《虛構的徬徨》、《二十世紀旗手》等深受注目。在他戰後的作品中,《維榮之妻》、《斜陽》、《人間失格》等被視為是代表作,引起無數年輕人共鳴,其中的《斜陽》與《人間失格》更堪稱是日本戰後文學頂尖作品。
繪者簡介
劉文瑄
台灣視覺藝術家,目前於台北創作、生活。
2007年於美國舊金山藝術學院畢業後,進入紐約市立大學杭特學院藝術研究所。2016年,入圍香港Sovereign傑出亞洲藝術獎決選。作品於各大美術館及藝術空間展出,包括澳洲雪梨白兔美術館,北京中國美術館、布達佩斯德維格當代美術館、荷蘭CODA美術館、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台灣美術館、臺北伊通公園(IT PARK)及亞洲雙年展等。藏家遍及歐美、亞洲各地。
創作形式涵蓋空間裝置、平面、攝影、錄像、植栽等,以探索塗畫(Drawing)在日常生活中找尋其開放性與自由,嘗試透過不同的手法建構再重構。
本書收錄作品出自「對畫」系列,以京都傳統水墨畫為基底,其上用鉛筆在既有的圖畫空間中恣意漫遊,揉和東西不同的筆觸與意趣,在畫紙上展開一場傳統書畫與當代的對話。
譯者簡介
劉子倩
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有小說、勵志、實用、藝術等多種書籍,包括谷崎潤一郎《陰翳禮讚》、太宰治《女生徒》、江戶川亂步《兩分銅幣》、夏目漱石《我是貓》、吉本芭娜娜《廚房》、《馬戲團之夜》、又吉直樹《火花》等日本文學作品。
序
前言
那個男人的照片,我見過三張。
一張,或許該稱為那個男人的幼年時代,估計是他十歲左右的照片,只見小孩被一大群女子圍繞(可以想像得到,他們是小孩的姐姐妹妹,以及堂姐妹們),站在庭園的池畔,身穿粗條紋日式裙褲,頭朝左邊傾斜三十度,是笑得很醜的照片。很醜?然而,遲鈍的人們(換言之,是對美醜漠不關心的人),一臉索然無趣地隨口講出客套話:
「是個可愛的小弟弟。」
這倒也不全然只是恭維,至少在小孩的笑臉上的確還是有一般人所謂「可愛」的影子,但是,哪怕是一丁點,只要是受過美醜訓練的人,只看一眼,立刻就會極為不快地嘀咕:
「怎麼有這麼討厭的小孩。」
說不定還會以拍開毛毛蟲的動作扔掉那張照片。
的確,小孩的笑臉,越看越令人感到一種不明所以、詭異的陰森感。終究,那並非笑臉。這個小孩,一點也沒笑。最好的證據,就是他握緊兩隻小拳頭站立。人不可能一邊握緊拳頭一邊笑。那是猴子。是猴子的笑臉。他只是在臉上擠出醜陋的皺紋罷了。甚至令人想稱為「皺巴巴的小老頭」,表情非常奇妙,而且,有點猥瑣,是令人莫名反胃的照片。過去,表情這麼不可思議的小孩,我從來沒見過。
第二張照片中的臉孔,又是令人大吃一驚的徹底變貌。是學生的裝扮。雖不確定是高中時還是大學時的照片,總之是個美貌驚人的學生。然而,這張照片同樣很不可思議地完全感覺不出是個活人。只見他身穿學生服,自胸前口袋露出白色手帕,坐在籐椅上蹺著二郎腿,並且,還是一樣在笑。這次的笑臉,不是皺巴巴的猴子笑臉,已變成相當有技巧的微笑,但那和人類的笑,好像還是有點不同。絲毫沒有可稱為血肉的重量、或者生命的苦澀那種充實感,看起來不像鳥,倒像羽毛一樣輕盈,只是一張白紙,而且,他正在笑。換言之,從頭到腳都像是人造品。說他做作也不是。說他輕浮也不是。說他皮笑肉不笑也不是。說他瀟灑帥氣,當然也嫌不夠貼切。而且,仔細一看,這個俊美的學生,同樣讓人感到有點靈異怪談的陰森詭異。過去,如此不可思議的俊美青年,我從來沒見過。
還有一張照片,是最古怪的。完全看不出他的年紀。頭髮好像有點花白。而且是在非常破舊的房間(照片清楚地拍出,房間牆壁有三個地方都崩塌了)角落,兩手高舉小火盆,這次他沒有笑。沒有任何表情。說穿了,彷彿坐著雙手高舉火盆就這麼自然死去,是一張帶有極端不祥氣息的照片。古怪的地方,不僅如此。那張照片中,臉算是拍得很大,因此我可以仔細檢查那張臉孔的構造,額頭很平凡,額頭的皺紋也很平凡,眉也平凡,眼也平凡,鼻子嘴巴下顎皆平凡,唉,這張臉不僅沒有表情,甚至無法令人留下印象。根本沒有特徵。比方說,我看了這張照片之後閉上眼。立刻就會忘記這張臉。我可以想起房間的牆壁與小火盆,對那個房間主人的印象卻已煙消霧散,無論如何,怎麼想就是想不起來。那是無法入畫的臉孔。是無法畫成漫畫的臉孔。我睜開眼。也沒有那種「啊!原來是這樣的一張臉,我想起來了!」的喜悅。說得極端一點,縱使睜開眼再次看到那張照片,我還是想不起來。而且,只覺得不愉快,很反感,忍不住想撇開眼。
即使是所謂的「死者遺容」,想必也比他更有表情與印象,如果在人的身體安上劣馬的腦袋,或許就會是這種感覺?總而言之,說不上來哪裡不對,就是有種讓觀者毛骨悚然的不快之感。過去,這麼不可思議的男人面孔,同樣地,我一次也沒見過。
那個男人的照片,我見過三張。
一張,或許該稱為那個男人的幼年時代,估計是他十歲左右的照片,只見小孩被一大群女子圍繞(可以想像得到,他們是小孩的姐姐妹妹,以及堂姐妹們),站在庭園的池畔,身穿粗條紋日式裙褲,頭朝左邊傾斜三十度,是笑得很醜的照片。很醜?然而,遲鈍的人們(換言之,是對美醜漠不關心的人),一臉索然無趣地隨口講出客套話:
「是個可愛的小弟弟。」
這倒也不全然只是恭維,至少在小孩的笑臉上的確還是有一般人所謂「可愛」的影子,但是,哪怕是一丁點,只要是受過美醜訓練的人,只看一眼,立刻就會極為不快地嘀咕:
「怎麼有這麼討厭的小孩。」
說不定還會以拍開毛毛蟲的動作扔掉那張照片。
的確,小孩的笑臉,越看越令人感到一種不明所以、詭異的陰森感。終究,那並非笑臉。這個小孩,一點也沒笑。最好的證據,就是他握緊兩隻小拳頭站立。人不可能一邊握緊拳頭一邊笑。那是猴子。是猴子的笑臉。他只是在臉上擠出醜陋的皺紋罷了。甚至令人想稱為「皺巴巴的小老頭」,表情非常奇妙,而且,有點猥瑣,是令人莫名反胃的照片。過去,表情這麼不可思議的小孩,我從來沒見過。
第二張照片中的臉孔,又是令人大吃一驚的徹底變貌。是學生的裝扮。雖不確定是高中時還是大學時的照片,總之是個美貌驚人的學生。然而,這張照片同樣很不可思議地完全感覺不出是個活人。只見他身穿學生服,自胸前口袋露出白色手帕,坐在籐椅上蹺著二郎腿,並且,還是一樣在笑。這次的笑臉,不是皺巴巴的猴子笑臉,已變成相當有技巧的微笑,但那和人類的笑,好像還是有點不同。絲毫沒有可稱為血肉的重量、或者生命的苦澀那種充實感,看起來不像鳥,倒像羽毛一樣輕盈,只是一張白紙,而且,他正在笑。換言之,從頭到腳都像是人造品。說他做作也不是。說他輕浮也不是。說他皮笑肉不笑也不是。說他瀟灑帥氣,當然也嫌不夠貼切。而且,仔細一看,這個俊美的學生,同樣讓人感到有點靈異怪談的陰森詭異。過去,如此不可思議的俊美青年,我從來沒見過。
還有一張照片,是最古怪的。完全看不出他的年紀。頭髮好像有點花白。而且是在非常破舊的房間(照片清楚地拍出,房間牆壁有三個地方都崩塌了)角落,兩手高舉小火盆,這次他沒有笑。沒有任何表情。說穿了,彷彿坐著雙手高舉火盆就這麼自然死去,是一張帶有極端不祥氣息的照片。古怪的地方,不僅如此。那張照片中,臉算是拍得很大,因此我可以仔細檢查那張臉孔的構造,額頭很平凡,額頭的皺紋也很平凡,眉也平凡,眼也平凡,鼻子嘴巴下顎皆平凡,唉,這張臉不僅沒有表情,甚至無法令人留下印象。根本沒有特徵。比方說,我看了這張照片之後閉上眼。立刻就會忘記這張臉。我可以想起房間的牆壁與小火盆,對那個房間主人的印象卻已煙消霧散,無論如何,怎麼想就是想不起來。那是無法入畫的臉孔。是無法畫成漫畫的臉孔。我睜開眼。也沒有那種「啊!原來是這樣的一張臉,我想起來了!」的喜悅。說得極端一點,縱使睜開眼再次看到那張照片,我還是想不起來。而且,只覺得不愉快,很反感,忍不住想撇開眼。
即使是所謂的「死者遺容」,想必也比他更有表情與印象,如果在人的身體安上劣馬的腦袋,或許就會是這種感覺?總而言之,說不上來哪裡不對,就是有種讓觀者毛骨悚然的不快之感。過去,這麼不可思議的男人面孔,同樣地,我一次也沒見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