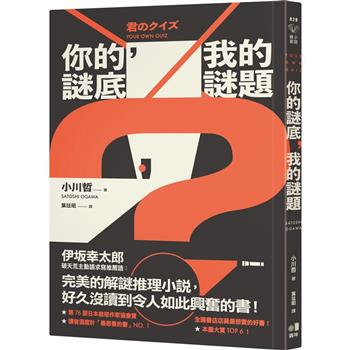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史詩與英雄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0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413 |
世界經典文學 |
$ 466 |
文學 |
$ 502 |
小說/文學 |
$ 519 |
中文書 |
$ 519 |
世界文學總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致文學裡不朽的「超級英雄」,
那些作家或角色,
他們豪壯的鍥而不捨
自我詰問、畢生追尋、反抗至死
「豪壯」定義了史詩。——哈洛.卜倫
哈洛.卜倫擁有百科全書般的智識,也是與眾不同的文學熱愛者。他不僅閱讀量驚人,閱讀的深度、廣度及筆下的人文厚度,也幾乎無人能出其右,有「當代最具天賦的文學評論者」之譽。
他和其他評論家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重視文本細讀,少談文化理論。在本書中,他評比偉大經典作品之異同,打破傳統分類方式,提出他心目中「史詩」應具備的共同特徵:豪壯(heroism)。
因此,除了荷馬《伊里亞德》與《奧德賽》、維吉爾《伊尼亞德》(《埃涅阿斯紀》)、《貝奧武夫》、但丁《神曲》等經典中的經典史詩,本書也收入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彌爾頓《失樂園》、柯立芝《老水手行》、 T.S.艾略特《荒原》等長詩經典,以及宗教文本的原型《創世紀》與《出谷紀》(《出埃及記》)、梅爾維爾《白鯨記》、惠特曼《我自己的歌》、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湯瑪斯曼《魔山》、喬伊斯《尤里西斯》等立意宏大的作品,甚至收錄了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語》。
在卜倫的筆下:
.荷馬的奧德修斯是非常危險的角色。他求生的本領舉世無雙,全船的人都滅頂了,唯獨他還能漂流海上。你不會想跟這樣的人同上一艘船,但你也不會想去讀、去聽別人的故事,因為求生就是最精采的故事。
.紫式部筆下的獵艷聖手光源氏,是「思慕眷戀」的化身,而眷戀是永遠可望而不可及的嚮往,是永遠未能止息的欲求,他纏綿不捨的眷戀一樣稱得上豪壯。
.再也沒有任何作家像普魯斯特這樣,以深情繾綣又光采耀人的創造性文筆,如此遼闊壯麗地演示「嫉妒」此一情感……
看鑽研經典數十年的文評大家哈洛.卜倫在他信手捻來的片段裡,以「卜倫式」觀點深入這些大部頭經典的核心,了解它們如何在文學的宇宙裡轟然而生、成為後世仰望的恆星,而這些大師在創作的銀河裡如何繼承文學的命脈,像行星一樣交會,像流星一樣碰撞,帶領你踏上這趟即興奔放並充滿個人風格、穿梭文學浩瀚星際的「奧德賽之旅」。
本書特色
1. 讓《西方正典》文學評論大師 哈洛.卜倫:
帶領你用你從沒想過的閱讀角度,征服一直沒能讀完的大部頭經典
告訴你經典巨作背後的創作者如何思考→打造角色和故事→開創新局
◆ 縱貫3000年、10000公里時空的文學閱讀地圖
◆ 突破文體與形式,收錄20部史詩級經典詩作、散文、小說
◆ 橫跨數十年的文評叢書精選,濃縮卜倫數十年閱讀與評論精華
2. 知名資深譯者宋偉航出手,「用卜倫解釋卜倫」!
◆ 擅長「以龐大譯注完全解釋原作」的宋偉航花費兩年時間翻譯、做註
◆ 援引卜倫自己的文字來說明,幫助讀者讀懂卜倫廣博深刻的思想脈絡
作者簡介
哈洛.卜倫(Harold Bloom)
1930年出生,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也是美國學術院院士,至今出版四十多本著作,包括文學研究巨著《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如何讀西方正典》(How to Read and Why)、《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莎士比亞:人的創造》(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等,得獎無數,有「當代最具天賦的文學評論者」、「世界最偉大的文評家」等美譽。
譯者簡介
宋偉航
知名資深譯者,台大歷史系、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譯作舉隅:《放客企業》、《智慧資本》、《企業蛻變》、《共謀》、《阿波羅的天使》、《大銀幕後》、《我在DK的出版歲月》、《聖徒叔叔》、《午夜知音》、《溫柔酒吧》、《迷》、《禿鷹律師》、《閱讀日誌》、《酷男的異想世界》、《留聲中國》、《補綴的星球》、《我的動物天堂》、《靈魂考》、《有關品味》、《全腦革命》、《綠色企業》等,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續寫一千零一夜故事集《千夜之夜》、吳爾芙(Virginia Woolf)經典《自己的房間》等文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