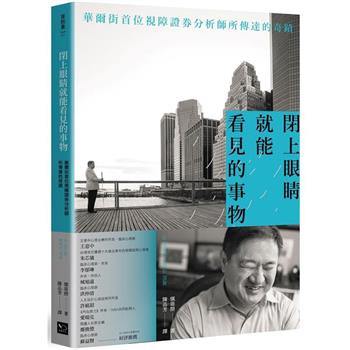韓江繼榮獲 國際曼布克文學獎 的《素食者》後
引發全世界讀者共鳴,最殘酷的美麗傑作
◆
那些鼓起勇氣迎向軍隊的少年,
是在光州事件裡決定留下來的少年,
也是母親在518那夜帶不走的少年;
是那些代替我們赴義的少年,
也是至今仍像影子般穿梭在你我身邊的少年。
引發全世界讀者共鳴,最殘酷的美麗傑作
◆
那些鼓起勇氣迎向軍隊的少年,
是在光州事件裡決定留下來的少年,
也是母親在518那夜帶不走的少年;
是那些代替我們赴義的少年,
也是至今仍像影子般穿梭在你我身邊的少年。
「在尊嚴與暴力共存的世界,每個角落、每個世代,都很有可能出現下一個光州。」──韓江
■「BTS防彈少年團」金南俊感動推薦!
◎2017年美國Amazon書店百大選書
◎2017年榮獲義大利「馬拉帕蒂文學獎」(Malaparte Prize)
◎2016年英國衛報年度選書、愛爾蘭時報年度最佳小說
◎2014年榮獲韓國「萬海文學獎」
◎感動全世界讀者,韓國銷售400,000冊!
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房慧真(作家、記者)、黃子佼(多媒體跨界王)、陳又津(小說家)、陳雪(小說家)、陳慶德(韓國社會文化專家、《再寫韓國》作者)、劉梓潔(作家)◎一致推薦(依姓名筆畫序)
◆
◆很荒謬吧,拳頭怎麼可能贏得過槍呢?
1980年5月,韓國光州市民與學生組織示威遊行反抗全斗煥政權。15歲的少年東浩和朋友正戴,也一起參加了示威活動。當政府派軍隊進駐光州冷血鎮壓,軍人開始開槍射殺市民的時候,東浩害怕地逃走躲了起來,並且親眼目睹正戴被當街射殺。
東浩愧疚之餘,來道廳的尚武館找尋正戴屍體,遇到了負責處理遺體入殮的女高中生恩淑,以及年輕的女裁縫師善珠,受她們請求留下來幫忙,也因此認識了館內負責調配人力與物資的男大學生振秀。
在協助無名屍體登記的工作時,東浩不時對自己的懦弱感到自責。幾天後,軍方即將攻入道廳的那晚,東浩下定決心要堅守到最後……
◆到底為什麼他死了,我卻還活著?
因為處理過屍體、從此無法再吃肉的恩淑;在拘留所遭遇非人對待的大學生振秀;背負著入獄汙點、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善珠;未能即時勸說兒子東浩回家的母親,他們剩餘的人生從此都懷抱愧疚,懷念著那名鼓起勇氣迎向軍隊的少年……
【作者的話】
「我無法逃避這本小說」
「我帶著受罰的心情坐在書桌前」
「如果我不把它寫出來,就到不了任何地方。」
這本書不是為我個人而寫,我想將這本書獻給我的感覺、存在,以及在光州民眾抗爭中不幸身亡者、倖存者,還有罹難者家屬。……最終,不是我幫了他們,而是他們幫了我。我什麼事也沒做,只是寫了一本書而已。 ────韓江,義大利「馬拉帕蒂文學獎」得獎感言
本書特色
● 作家韓江出身光州,以父親的學生東浩為主角,蒐集資料、訪問生還者寫下的小說。
● 用小說家的眼光詮釋光州事件,探討當事者心理動機。透過不同的角色發聲,呈現出事件的殘忍、倖存者的無力與愧疚,人類內心的黑暗與暴力,以及良心、勇氣與希望。
媒體評論
● 《少年來了》確實站在小說的位置,把光州事件帶到讀者眼前⋯⋯這些角色代替沉默的生者和死者,說出他們的憤怒、悲傷、無力與尊嚴。在我們尚未能說出真話之前,先讀小說吧。當這些微小的聲音都被聽見了,那小說就自由了,才能回報我們更多的現實。──陳又津(小說家)
● 韓江的《少年來了》,一字一句如整座光州碎裂的玻璃,尖銳地點醒小說家的另一重使命:我們拿著的筆,是槍是劍,只為正義而鳴響,只為光亮而揮拔。我們拿著的筆,也是針是線,縫合那些被遺忘的模糊血肉,在歷史的傷口上繡出一朵燦爛奇花。寫下,只為被記得。──劉梓潔(作家)
● 韓江以穿越生與死的魔幻筆法,透過七人的目光、回憶、言語、疼痛與離別,全稱式地拼湊出1980年5月18日的『光州事件』。當代韓國人在韓江的筆下,尋找過往的記憶,抹平當今的傷痛,只為了走向未來的光明之途。」 ──陳慶德(韓國社會文化專家、《再寫韓國》作者)
● 作者將身處在黑暗與暴力世界裡,遭受折磨、歷經傷痛的人們刻畫得淋漓盡致,帶領讀者直視當年的光州,宛如身歷其境般見證那場血腥暴力的大屠殺。文中敘事者的證詞和閱讀者的想像結合出難以忘懷的懇切告白,讓我們重新切身體會那座城市的十天漫長煎熬。從水滴折射出的陽光碎片中,依舊找尋純潔雛鳥的這本小說,對我們訴說著真正需要好好擁抱的歷史記憶究竟是什麼。──文學評論家白智蓮(백지연)
● 有些題材,只要選擇了,就等於是把作者的說故事功力搬上檯面準備接受考驗,在韓國歷史中,尤其以1980年5月光州事件這個題材最為典型。只是我們迫切想知道的,不再是根據歷史事實的嚴懲與復權,而是關於傷害結構的透視與探究。這是一本唯有韓江才能超越韓江的小說。──文學評論家申亨哲(신형철)
● 情感熾烈的作品!韓江的《少年來了》捕捉人性的自相矛盾:開頭章節屍橫遍野的畫面,告訴讀者嗜血獸性是如何泯滅人性,但我們能展現博愛精神,為原則信念受苦犧牲,又讓我們成為真正的人。作者總結這種弔詭的手法很出色,本書希望將個人經歷與政治事件連結在一起,它在刻劃前者時竟有如此強大的渲染力,例如作者細膩又具體地描述一位母親對逝去兒子的思念,就跟她鋪陳這起舉世悲痛的事件一樣,充分展現駕馭文字的功力。──英國《獨立報》
● 韓江的文字清澈且含蓄內斂,她以極其溫暖的筆觸,處理令人震撼的慘烈題材。──《泰晤士報》
● 韓江以獨特的敘事風格,訴說南韓1980年歷時10天的光州事件,及其在韓國心理、精神、政治面掀起的陣陣漣漪,讓我洞悉光州年輕人當年受到的殘酷暴行。她的文筆質樸卻情感濃烈。──《衛報》2016年推薦書單
● 韓江這位說故事的人不可思議,她對人類的目的提出質疑,透過她筆下人物令人心碎的經歷,看到善與惡不斷緊張對立,也讓人心裡冒出很多問號。她如詩的語言,行雲流水般在不同觀點之間游移,但她也會大膽用不加修飾的樸素措辭,模擬重現歷史上那場嚴酷的衝突,和當時瀰漫的激昂情緒。以如此令人不快的方式描摹光州民主化運動,竟將讀者吸引到故事結束。──《書單》
● 美麗又殘酷……大膽檢視人性狀態,診斷結果不忍卒睹,這本看似冷酷無情的小說卻直搗讀者內心。──《愛爾蘭時報》2016年推薦書單
● 非看不可的作品,具普世性,能引起深刻的共鳴……它讓我們撕心裂肺,悸動縈繞心頭久久不去,它讓我們時而懷抱夢想,時而悲痛哀鳴……。──《紐約時報書評》
● 令人心痛……韓江的小說試圖將難以啟齒的事情用言語表達,她特別著墨於平凡面,將可怕的暴力鎮壓事件人性化,好比書中角色幫忙照料和運送受難者遺體,在事發多年後努力回歸一般生活。韓江讓讀者從東浩的家人和朋友口中,追憶東浩的點點滴滴,她賦予那些失落者發聲的權利。──《出版人週刊》
● 引人入勝……結果很折磨人但扣人心弦,冷酷地描繪死亡與痛苦,卻讓你目不轉睛……韓江她彷彿施了催眠術,將你拉進光州事件的恐怖場景,對人性提出質疑,人人都不能倖免被捲入其中,這部作品令人膽寒,直接了當到令人痛苦。──《洛杉磯時報》
● 清新質樸,鋪陳巧妙,令人肝腸寸斷……《少年來了》努力處理光州大屠殺的歷史餘波,它要問的是,人類會為何而死?倖存下來的人接著又會有什麼遭遇?韓江秉持原創且大無畏的精神,處理這些難題與無情的疑問,讓《少年來了》成了2017年必讀好書。──《芝加哥書評》
● 韓江在這部作品探討殘暴政治帶來形形色色的創傷,透過讓人難忘的細節與穿透人心的感性事實,交織出一部精采小說……一部書寫強烈、帶來衝擊與完全貼近人性的作品。──《科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 韓江在這部作品探討殘暴政治帶來形形色色的創傷,透過讓人難忘的細節與穿透人心的感性事實,交織出一部精采小說……一部書寫強烈、帶來衝擊與完全貼近人性的作品。──《科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 韓江這部小說最突出的是對於死亡毫不退縮、不帶情緒的描述。很難想出還有什麼作品如此生動、有說服力地處理了肉體衰敗的不同階段。韓江的文字不是讓人輕鬆讀完,而是帶著對於生命最終段的洞察,這部分的描述呈現非常出色。──《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 這部故事的題材儘管駭人,文字卻十分優美,其中細緻刻劃的意象讓人無從迴避,也無法別過頭去……《少年來了》篇幅不長,卻深刻提出哲學性和精神性的探問,也沒有提供任何撫慰。故事始終是緊扣著以下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到底能忍受多少、我們能對別人造成什麼樣的傷害……──《聖路易郵訊報》(St. Louis Post-Dispatch)
● 啟發人心……故事毫無冷場……小說家最終重建出來的,不僅是優秀地記錄韓國歷史格外波動爭議的那一段,期間所發生的人民受難事件,更是用文字證明了人們願意甘冒受苦、被捕、甚至用自身性命交換,只為了信念去反抗,或在他人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 這部小說針對各種艱難問題提供了深刻與人性的回答,也是對暴行受難者致敬的一部動人故事。──《書頁》(Book Page)
● 引人入勝……韓江以說書人特有的細膩和力量,將這場衝突跳脫「歷史」的時間距離,進入每一個無可取代的獨立之人的親密空間。──《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論壇報》(Minneapolis Star-Trib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