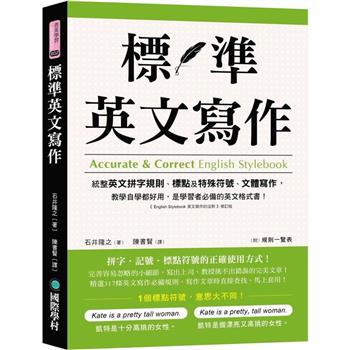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只有兩個人【金英夏人間劇場.短篇小說集】(附作者語音問候QRcode與印簽扉頁)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2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94 |
小說 |
$ 332 |
其他各國文學 |
$ 332 |
韓國文學 |
$ 370 |
中文書 |
$ 378 |
韓國現代文學 |
$ 37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韓國國民作家」金英夏最短小鋒利的故事集
從「失去」看人生有多荒謬、
人可以有多少選擇
「失去」可能讓我們成為自己人生的邊緣人——是命運還是我們自己,不給選擇的餘地?
金英夏的筆下沒有對或錯,當他挖掘我們身而為人最幽微的心緒,
我們明白,這世上還有個人理解這樣的自己。
◆
本書收錄金英夏7個中短篇故事,每一篇都在描寫「失去了」什麽的人,以及這些人「失去之後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這些人不只是外在發生變化,連內在也遭到破壞,小說敘述他們設法求生的每一天,如何填補或承受那份空缺,在世上生存下去。
爸爸和「我」就像全世界使用某種稀有語言的最後兩個人。當其中一人先離世,被留下的人所在的世界,會是孑然的孤獨,還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只有兩個人〉(缺失)
失蹤11年的孩子回家了,他們夫妻倆的生命再次被丟到另一個軌道上。已經習慣不幸的丈夫,以及已經拋棄痛苦現實的妻子,茫茫然被迫面對這份上天的禮物:「失而復得」的枷鎖。 ——〈尋找孩子〉(遺失)
小說家「我」喪失創作的喜悅,半推半就下接受出版社老闆的建議來到紐約閉關寫作,情況卻有如好萊塢黑幫電影的劇情般急轉直下……「我知道我不是玉米,但那些雞不知道!」 ——〈玉米與我〉(喪失)
在〈人生的原點〉(迷失)中,醫療器材店老闆與初戀情人重逢後又驀地分道揚鑣:在〈西裝〉(錯失)中,出版社編輯沒有找回父親,而是穿著一套高級訂製西裝回來;在〈崔恩知與朴仁樹〉(散失)中,總編輯送別了人生落幕的老朋友;在〈神的惡作劇〉(奪失)中,四名參加公司新人研修營的年輕人莫名其妙成了「密室逃脫遊戲」的參賽者……當人生在世各種日常的光明與黑暗陷入失衡狀態,他們有人演戲來安慰自己,有人放棄自我安慰、拚命過著「那之後」的日子。
金英夏以社會邊緣人極端設定的長篇小說著稱,這一次在短篇小說中從日常生活場景切入,讓讀者看到「失去」如何可能使我們成為「自己人生的邊緣人」,也讓讀者領略他以輕寫重、隨心所欲遊走人生悲喜曖昧界線的寫作功力。
短篇小說集《只有兩個人》有如一艘試探金英夏深邃宇宙的探索小艇,書中不論是顛覆「理所當然」的想像力,或是精準呈現對於人生的幽默反諷,無一不能令人感受到百分之百的「金英夏風格」。透過多樣的情境、人物設定,他將個人内在的複雜感情、各式各樣關係的矛盾,乃至於我們處於所謂「命運」之下的苦惱,金英夏全都寫入故事了。
名人推薦
「小說家透過理想主義的激發,以鋒銳的透徹,描繪人們的夢想與生活;金英夏在洞察人類普世問題上,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深度與憐憫。」――作家暨知名節目主持人謝哲青
「……藝術要不是能使陌生的變熟悉,就是能讓熟悉的變陌生。我們看到有人同時做到這兩者。」――《忽然一陣敲門聲》艾加.凱磊(Etgar Keret)論金英夏作品
作者簡介
金英夏(김영하)
1968年11月11日生,是韓國進軍國際文壇的先鋒作家,不少作品已經在美國、法國、日本、德國、義大利、荷蘭、土耳其等十餘個國家翻譯出版。
他畢業於延世大學企業管理系,1995年在季刊《批評》上發表〈關於鏡子的冥想〉,登上文壇。同年八月,金英夏以長篇小說《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與趙京蘭(《烤麵包的時間》)同獲第一屆文學村新人作家獎,受到文壇和讀者的廣泛關注。1998年,《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在法國翻譯出版,隨後又推出了德語版,1999年,金英夏憑藉短篇小說〈你的樹木〉獲得著名的現代文學獎(第44屆)。
2004年,韓國文壇颳起了強勁的「金英夏旋風」。他以短篇小說〈哥哥回來了〉、〈珍寶船〉及長篇小說《黑色花》在一年內勇奪黃順元文學獎、怡山文學獎,以及韓國三大文學獎之一的東仁文學獎。一年之內集三個著名文學獎項於一身,不僅成為年度文壇的一道亮麗風景,也是韓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罕見傳奇。
金英夏給人的印象帶有特立獨行的感覺,他不畏世俗眼光,曾戴著耳環領取文學獎,原本學商的他,後來卻在韓國國立藝術大學教寫作,也寫影評、客串電影、主持廣播節目等等,以電影《腦海中的橡皮擦》獲得「大鐘獎」最佳改編劇本獎,2017年、2019年還擔任韓國tvN電視台《懂也沒用的神祕雜學詞典》固定來賓。他不只擅長運用媒體推廣文學,也關懷社會議題,並且勇於發聲。
他擅長描寫都市生活的冷冽、無奈,現代人的黑暗面是他關注的主題,性愛與死亡更是他直接大膽的著力點。評論家將他比喻為「韓國的卡夫卡」,足見他的作品為讀者帶來的省思與衝擊,有其重要的代表性。
著有長篇小說《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1996)、《阿郎,為什麼》(2001)、《黑色花》(2003)、《光之帝國》(2006)、《猜謎秀》(2007)、《聽見你的聲音》(2012)、《殺人者的記憶法》(2013),短篇小說集有《傳呼》(1997)、《夾進電梯裡的那個男人怎麼樣了》(1999)、《哥哥回來了》(2007)、《無論發生什麼事》(2010)、《只有兩個人》(2017),譯作有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等。
漫遊者已出版:
◎長篇小說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殺人者的記憶法》、《光之帝國》、《猜謎秀》、《黑色花》、《我聽見你的聲音》
◎散文集
《懂也沒用的神祕旅行:小說家金英夏旅行的理由》、《見》、《言》、《讀》
譯者簡介
胡椒筒| hoochootong
專職譯者,帶著「為什麼韓劇那麼紅,韓國小說卻沒人看」的好奇心,闖進翻譯的世界。譯有《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那些美好的人啊》、《蟋蟀之歌:韓國王牌主播孫石熙唯一親筆自述》、《信號Signal:原著劇本》、《您已登入N號房:韓國史上最大宗數位性暴力犯罪吹哨者「追蹤團火花」直擊實錄》、《最後一個人:韓國第一部以「慰安婦」受害者證言為藍本的小說》、《朴贊郁的蒙太奇:韓國電影大師朴贊郁首部親筆著作》等。
●作品賜教:hoochootong@gmail.com ●Instagram @hoochootong.transla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