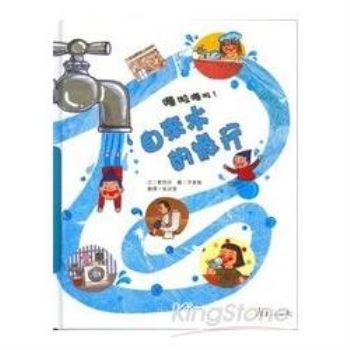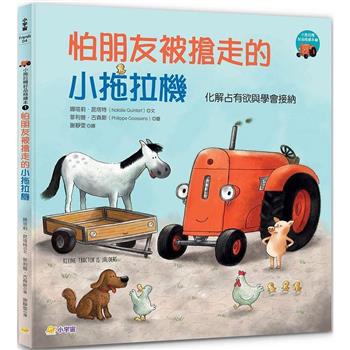2005年美國自然文學最高榮譽「約翰・巴勒斯」文學獎(John Burroughs Medal)
2020年Openbook好書獎.年度生活書
★古老、微小,卻支撐一整座森林的植物
苔蘚是最古老的植物,也是最早離開水域,征服陸地的植物。身形僅有雨林的三千分之一,苔蘚卻能蘊養樹木、保護土壤、涵養水分,為昆蟲遮風擋雨,也讓鳥類與熊取用築巢……在許多我們意想不到的地方,細細密密地支持起了一座森林的運行。
★長在城市縫隙之間的植物
長在城市裡的苔蘚,和人類有許多共通點:多元、適應力強、抗壓性高,在擁擠的環境也能活得很好,而且還經常旅行!苔蘚的葉片構造和人的肺泡有很多相似點,當它們減少消失,正是向我們示警了空汙;還有苔蘚的抑菌以及吸收能力,都曾在一戰被廣泛當作棉花的替代品以及傷口敷料……
★在印第安傳統裡向苔蘚禮敬
傳統的印第安人採集苔蘚,好擦去鮭魚皮上的黏液毒素,也在手套與靴子裡塞進苔蘚,隔絕冬日凜冽的寒氣;在沒有幫寶適的年代,寶寶的搖籃板裡會塞滿舒適的乾苔蘚;還有,在女性的月事隔離小屋裡,會有一籃一籃精挑細選過的苔蘚,好陪伴她們度過這段印第安人認為的靈性高峰;印第安人也將灰苔做成枕頭,據說,那會讓人做上特別的夢……
「我們被教導過,
運用植物就是在向它身處的自然表達敬意,
使用植物的方式要讓它的天賦能夠繼續滋長。」
《三千分之一的森林》收錄了基默爾的十九篇散文,她以科普知識為經,生命經驗與部落傳統為緯,揉合生命故事與研究苔類多年的心得。在這系列散文中,有描寫她與女兒、鄰居的日常互動;有在野外採集的刺激冒險;還有超級富豪假借復育之名,邀請她為深山密林裡一座精美絕倫的仿古青苔花園擔任顧問——但她發現,復育是為了遮掩一場遊走灰色地帶、盜取自然的犯行,而自始至終,她都無從得知富豪的真實身分。
《三千分之一的森林》有流暢優美的自然書寫,也有清晰洗鍊的科學語言,基默爾試著用不同的知識系統,讓我們突破尺度的限制,理解苔類這種微小植物帶來的啟發,和森林同樣弘大。作者筆調有時像哲學家的座右銘,有時也像生態科學家的提醒警示,但更多時候,是像部落長老或母親的教誨,悠遠綿長,溫柔纏繞出人類、苔蘚與自然三者密不可分的關係。
★亞馬遜網站五星評價
★結合「民族植物學」、「科普知識」、「人文關懷」之自然書寫佳作
★作者為當代最重要青苔研究權威之一
★搭配北美知名苔類專家霍華德·阿爾文·克洛姆(Howard Alvin Crum)9幅手繪插圖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楊嘉棟博士審訂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三千分之一的森林:透過苔蘚的故事,我們得以重新理解這個世界的圖書 |
 |
三千分之一的森林:透過苔蘚的故事,我們得以重新理解這個世界 作者:羅賓・沃爾・基默爾(Robin Wall Kimmerer) / 譯者:賴彥如 出版社:漫遊者文化 出版日期:2024-07-1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77 |
動/植物學史 |
$ 355 |
中文書 |
$ 355 |
動/植物學史 |
$ 356 |
植物概論/百科 |
$ 396 |
自然科學 |
$ 405 |
科學‧科普 |
$ 405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三千分之一的森林:透過苔蘚的故事,我們得以重新理解這個世界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羅賓・沃爾・基默爾 Robin Wall Kimmerer
紐約州立大學(SUNY)環境科學與森林學院轄下的環境與林業生物系副教授。教授內容包含土地和文化、傳統生態知識、民族植物學、苔蘚類植物生態學、干擾生態學(Disturbance Ecology)和植物學總論等課程。她的工作之一是為美洲原住民提供更多的環境科學的研究途徑,以及從更廣泛的實證角度獲益的科學。著有《微觀苔蘚》以及《編織聖草》(Braiding Sweetgrass)。
審訂者簡介
楊嘉棟
臺大森林所碩士、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職於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所長,研究內容以苔蘚植物分類為主,目前工作為野生植物調查、研究、保育,以及生態教育推廣。著作有《桃園縣植物資源導覽手冊》、《陽明山國家公園苔蘚・地衣圖鑑》及臺灣苔蘚誌英文專書三冊、苔蘚相關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譯者簡介
賴彥如
台大外文系、社會系雙學士,台大城鄉所碩士。曾在古蹟、溼地和山林裡工作,夢想是可以徒步環島很多次。自由譯者,作品散見於環境、文化、藝術、城鄉領域,譯有《合作住宅指南:用自決、永續、共居開啟生活新提案》、《如何謀殺一座城市:高房價、居民洗牌與爭取居住權的戰鬥》(合譯)、《城市造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合譯)等等。
羅賓・沃爾・基默爾 Robin Wall Kimmerer
紐約州立大學(SUNY)環境科學與森林學院轄下的環境與林業生物系副教授。教授內容包含土地和文化、傳統生態知識、民族植物學、苔蘚類植物生態學、干擾生態學(Disturbance Ecology)和植物學總論等課程。她的工作之一是為美洲原住民提供更多的環境科學的研究途徑,以及從更廣泛的實證角度獲益的科學。著有《微觀苔蘚》以及《編織聖草》(Braiding Sweetgrass)。
審訂者簡介
楊嘉棟
臺大森林所碩士、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現任職於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所長,研究內容以苔蘚植物分類為主,目前工作為野生植物調查、研究、保育,以及生態教育推廣。著作有《桃園縣植物資源導覽手冊》、《陽明山國家公園苔蘚・地衣圖鑑》及臺灣苔蘚誌英文專書三冊、苔蘚相關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譯者簡介
賴彥如
台大外文系、社會系雙學士,台大城鄉所碩士。曾在古蹟、溼地和山林裡工作,夢想是可以徒步環島很多次。自由譯者,作品散見於環境、文化、藝術、城鄉領域,譯有《合作住宅指南:用自決、永續、共居開啟生活新提案》、《如何謀殺一座城市:高房價、居民洗牌與爭取居住權的戰鬥》(合譯)、《城市造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合譯)等等。
目錄
【致謝】
【前言】在日常感知的邊緣,開始觀看
1.青苔與岩石的古老對話
這些大石比緩慢更緩慢,比強壯更強壯,但它們生出一片像冰川一樣強而有力的柔軟綠蔭,青苔磨耗石頭的表面,一點一點地磨成粒,緩慢地變回沙。
2.聆聽苔蘚
苔蘚不是背景音樂,是交織纏繞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觀察苔蘚的方式,可以像是細細諦聽水流撞擊岩石,這溪流有很多種聲音,令人平靜,苔蘚也有各種綠意,使人舒心。
3.小之所長,活在邊界
無論人行道之間的縫隙、橡樹的枝枒、甲蟲的背部,還是峭壁的暗礁,苔蘚都可以填滿植物之間的空隙,迷你優雅,充分利用小的好處,冒險拓展自己的疆域。
4.復回水塘
苔蘚就是植物界的兩棲動物。它們是第一種從水生過渡到陸生的植物,介於藻類和高等陸生植物之間。苔蘚演化出一些基本的適應能力,能夠在陸地,甚至沙漠中存活。
5.性別不對稱
無論在數量、體積或精力層面,雌體都主導了曲尾苔的生命。男性存在與否,有賴女性的力量。萬一那個孢子掉到長滿同一種曲尾苔的土地上,它會從現存雌體的葉子之間篩落,然後定著在某處,讓雌體來決定它的命運。
6.為水而生
雨水沿著早為它們準備好的路徑奔流而去,淹滿小葉片的渠道,水總能在毛細管裡找到路,深深沁入每寸細胞。不出幾秒鐘,苔蘚所有飢渴的細胞都膨脹起來,扭曲的莖部伸展向天空,葉片也向外伸展來迎接雨水。
7.包紮土地的傷口:苔蘚的生態演替
金髮苔是第一個開始療癒這片土地的植物,其他植物才有機會跟上。在陰影深幽處,當苔蘚完成任務時,很快就會被取代。整個荒漠孤島上的樹木,就是第一批來到礦渣堆上的苔蘚所留下來的禮物。
8.三千分之一的森林
苔蘚地毯的高度大約只有雨林的三千分之一,卻有同樣的結構和功能。苔蘚森林裡的動物跟雨林裡的動物一樣,透過複雜的食物鏈彼此關聯。生態系的各種規矩,在苔蘚森林裡都找得到。
9.基卡普河
岩岸和基卡普河峭壁的研究,後來產生了所謂的「中度干擾假說」,在干擾強度介於兩個極端之間時,物種多樣性最高。生態學家指出,若完全沒有干擾,優勢族群像蛇蘚就會慢慢進逼其他物種,藉由生存優勢排除其他競爭者。
10.選擇
我們發現四齒苔是連續的雌雄同體,只要群落變擠,就會改變性別從雌體變成雄體。這種跟著族群密度改變性別的作法也發生在魚類身上,但之前從來不曾出現在苔蘚上。
11.命運的風景
很快,被風推倒的樹會變身長滿苔蘚的原木,風雨之後,苔蘚在木頭上成為一片織錦,映照出它周圍的森林是如何被同樣的力量塑造成形。白楊樹的種子飛揚在一陣劇烈強風裡,然後長出新的森林。
12.城市裡的苔蘚
樹上的苔蘚是好兆頭,沒了它們便值得擔憂。還有遍地在你腳下的是真苔。在噪音、廢氣和摩肩擦踵的人群裡,總有縫隙之間的苔蘚帶來一點小小慰藉。
13.互惠之網:苔蘚的民族植物學
或許禮敬這些不起眼的小小植物最好的方式,就是尋常的小小方法。溫柔盛托住小嬰兒、接住經血、為傷口止血、保暖——我們不就是這樣在世界裡安身立命的嗎?
14.紅色運動鞋
我舞在泥炭的水鼓上,雙腳透過泥炭的浪傳遞我存在的訊息,在一波波的回憶裡,它們也傳回訊息,告知它們的存在。我們還在。跟泥炭苔還活著的表面一樣,個體轉瞬即逝,集體卻恆久流長。我們還在。或許我的存在最好的證明,就是那隻遺落在某個深處的紅色運動鞋。
15.尋找壺苔
說到棲地,壺苔肯定是最挑剔的,無苔蘚能出其右。壺苔不會長在其他苔蘚常出現的地方,只會生長在沼澤裡。不是在一般形成泥炭圓丘的泥炭苔上,也不是在沼澤的邊緣。大壺苔只會出現在沼澤的唯一一處,在鹿的排遺上。
16.想要擁有自然的人
因為傲慢而摧毀一個野外生物,似乎是征服能力的展現。野生事物一旦被捉起來,就不再是野生的了。其本質在它從原生地脫離的時候就已經消失。透過擁有的舉動,事物變成了一個物品,不再是它本身了。
17.森林向苔蘚說謝謝
苔蘚串起一整個森林,這種互惠的模式讓我們看到一種可能性。它們只取所需的少少部分,卻湧泉以報。
18.採盜者與旁觀者
我想像他們伸出髒手深入苔蘚地墊,把手臂那麼長的苔蘚給成片撕起,想到這就讓我一陣顫抖,像是一個女人在攻擊她的人面前被脫個精光。他們接連剝除每棵樹上的苔蘚,塞進麻布袋,從光明進入黑暗。
19.妖精的黃金
光苔是極簡主義的完美典範,手段簡樸,目的豐富,樸素到你完全不會發現它是苔蘚。有些苔蘚需要全日照,有的喜歡雲隙間的漫射光,光苔則只需要雲朵邊緣透出的絲絲光線就夠了。
【延伸閱讀】
【譯名對照】
【前言】在日常感知的邊緣,開始觀看
1.青苔與岩石的古老對話
這些大石比緩慢更緩慢,比強壯更強壯,但它們生出一片像冰川一樣強而有力的柔軟綠蔭,青苔磨耗石頭的表面,一點一點地磨成粒,緩慢地變回沙。
2.聆聽苔蘚
苔蘚不是背景音樂,是交織纏繞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觀察苔蘚的方式,可以像是細細諦聽水流撞擊岩石,這溪流有很多種聲音,令人平靜,苔蘚也有各種綠意,使人舒心。
3.小之所長,活在邊界
無論人行道之間的縫隙、橡樹的枝枒、甲蟲的背部,還是峭壁的暗礁,苔蘚都可以填滿植物之間的空隙,迷你優雅,充分利用小的好處,冒險拓展自己的疆域。
4.復回水塘
苔蘚就是植物界的兩棲動物。它們是第一種從水生過渡到陸生的植物,介於藻類和高等陸生植物之間。苔蘚演化出一些基本的適應能力,能夠在陸地,甚至沙漠中存活。
5.性別不對稱
無論在數量、體積或精力層面,雌體都主導了曲尾苔的生命。男性存在與否,有賴女性的力量。萬一那個孢子掉到長滿同一種曲尾苔的土地上,它會從現存雌體的葉子之間篩落,然後定著在某處,讓雌體來決定它的命運。
6.為水而生
雨水沿著早為它們準備好的路徑奔流而去,淹滿小葉片的渠道,水總能在毛細管裡找到路,深深沁入每寸細胞。不出幾秒鐘,苔蘚所有飢渴的細胞都膨脹起來,扭曲的莖部伸展向天空,葉片也向外伸展來迎接雨水。
7.包紮土地的傷口:苔蘚的生態演替
金髮苔是第一個開始療癒這片土地的植物,其他植物才有機會跟上。在陰影深幽處,當苔蘚完成任務時,很快就會被取代。整個荒漠孤島上的樹木,就是第一批來到礦渣堆上的苔蘚所留下來的禮物。
8.三千分之一的森林
苔蘚地毯的高度大約只有雨林的三千分之一,卻有同樣的結構和功能。苔蘚森林裡的動物跟雨林裡的動物一樣,透過複雜的食物鏈彼此關聯。生態系的各種規矩,在苔蘚森林裡都找得到。
9.基卡普河
岩岸和基卡普河峭壁的研究,後來產生了所謂的「中度干擾假說」,在干擾強度介於兩個極端之間時,物種多樣性最高。生態學家指出,若完全沒有干擾,優勢族群像蛇蘚就會慢慢進逼其他物種,藉由生存優勢排除其他競爭者。
10.選擇
我們發現四齒苔是連續的雌雄同體,只要群落變擠,就會改變性別從雌體變成雄體。這種跟著族群密度改變性別的作法也發生在魚類身上,但之前從來不曾出現在苔蘚上。
11.命運的風景
很快,被風推倒的樹會變身長滿苔蘚的原木,風雨之後,苔蘚在木頭上成為一片織錦,映照出它周圍的森林是如何被同樣的力量塑造成形。白楊樹的種子飛揚在一陣劇烈強風裡,然後長出新的森林。
12.城市裡的苔蘚
樹上的苔蘚是好兆頭,沒了它們便值得擔憂。還有遍地在你腳下的是真苔。在噪音、廢氣和摩肩擦踵的人群裡,總有縫隙之間的苔蘚帶來一點小小慰藉。
13.互惠之網:苔蘚的民族植物學
或許禮敬這些不起眼的小小植物最好的方式,就是尋常的小小方法。溫柔盛托住小嬰兒、接住經血、為傷口止血、保暖——我們不就是這樣在世界裡安身立命的嗎?
14.紅色運動鞋
我舞在泥炭的水鼓上,雙腳透過泥炭的浪傳遞我存在的訊息,在一波波的回憶裡,它們也傳回訊息,告知它們的存在。我們還在。跟泥炭苔還活著的表面一樣,個體轉瞬即逝,集體卻恆久流長。我們還在。或許我的存在最好的證明,就是那隻遺落在某個深處的紅色運動鞋。
15.尋找壺苔
說到棲地,壺苔肯定是最挑剔的,無苔蘚能出其右。壺苔不會長在其他苔蘚常出現的地方,只會生長在沼澤裡。不是在一般形成泥炭圓丘的泥炭苔上,也不是在沼澤的邊緣。大壺苔只會出現在沼澤的唯一一處,在鹿的排遺上。
16.想要擁有自然的人
因為傲慢而摧毀一個野外生物,似乎是征服能力的展現。野生事物一旦被捉起來,就不再是野生的了。其本質在它從原生地脫離的時候就已經消失。透過擁有的舉動,事物變成了一個物品,不再是它本身了。
17.森林向苔蘚說謝謝
苔蘚串起一整個森林,這種互惠的模式讓我們看到一種可能性。它們只取所需的少少部分,卻湧泉以報。
18.採盜者與旁觀者
我想像他們伸出髒手深入苔蘚地墊,把手臂那麼長的苔蘚給成片撕起,想到這就讓我一陣顫抖,像是一個女人在攻擊她的人面前被脫個精光。他們接連剝除每棵樹上的苔蘚,塞進麻布袋,從光明進入黑暗。
19.妖精的黃金
光苔是極簡主義的完美典範,手段簡樸,目的豐富,樸素到你完全不會發現它是苔蘚。有些苔蘚需要全日照,有的喜歡雲隙間的漫射光,光苔則只需要雲朵邊緣透出的絲絲光線就夠了。
【延伸閱讀】
【譯名對照】
序
前言
在日常感知的邊緣,開始觀看……
我第一次對「科學」(還是宗教呢?)有意識的記憶,發生在幼稚園的課堂,在老舊的格蘭傑禮堂裡。當第一片迷人的雪花翩然落下,我們全都衝去把鼻子貼在結著白霜的窗子上。霍普金斯小姐十分睿智,身為教師,她知道在初雪的時候要遏抑五歲孩童的興奮之情有多困難,所以我們統統都出門了。大夥身著靴子和連指手套,在飄飄迴雪中圍繞在她身旁,她從大衣的深口袋裡摸出一副放大鏡。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第一眼透過鏡片看到的雪花,在她海軍藍大衣的羊毛袖子上閃閃發亮,像是夜空中的點點星光。經過十倍放大,那一片雪花的複雜細節令我驚奇不已。像雪這麼微小又平凡的事物,怎能如此完美無瑕?我情不自禁地看了再看。即使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最初的那一瞥,是如何充滿可能又深不可測。那是第一次,卻不是最後一次,我感覺到這世界的浩繁,不僅限於我們目光所及。於是當我看向輕落在枝頭和屋頂的雪片時,便多了一分新的認知:每一片雪花裡頭,都是星芒狀晶體構成的小小宇宙。雪的這分「秘密」令我讚嘆不已。那把放大鏡和那片雪花,是覺醒的鐘聲,是觀看的開始。從那一刻起,我模模糊糊地感受到,當你越仔細地觀看,這已然繽紛的大千世界將會變得更加動人。
學習看苔蘚這件事,跟我第一次對雪花的印象交疊在一起。就在日常感知的邊緣處,有另一個層面,是關於美、關於極小的葉子怎麼如一片雪花般有著完美的排列、關於肉眼難見的生物是如何複雜而美麗。所需要的,就只有注意力和觀看的方法。我發現苔蘚是深入了解鄉野的媒介,就如同森林的秘密知識。本書就是一份進入新視野的邀請。
初觀苔蘚後的三十年間,我一直都把手持放大鏡掛在脖子上。它的掛繩和我的藥袋的皮繩總纏在一起,這既是隱喻,也是事實。我所擁有的植物知識有很多不同來源,有從植物本身習得的,有作為科學家訓練而得,也有我身為波塔瓦托米族(Potawatomi)後裔,對傳統知識的直覺連結。在上大學學習它們的學名之前,我一直都把植物視為我的老師。學生時代,對植物生命的兩種觀點,主體與客體,精神與物質,就像纏繞在我頸上的兩條繩索。我被教導植物科學的方式,將我對植物的傳統知識推到邊緣。寫作這本書也是一個重新找回那分認知的過程,期望賦予它適當的地位。
古老的傳說說道,畫眉鳥、樹木、苔蘚和人類──所有的生物曾經共享一個語言。但那個語言早已被遺忘,所以我們得透過觀看、觀察彼此的生活方式,才能夠了解彼此。我想要訴說苔蘚的故事,因為它們的聲音很少被聽見,而我們又有這麼多事情要向它們學習。它們帶著重要的訊息亟待被聆聽,也就是有別於你我、屬於物種的觀點。身為科學家那部分的我想了解苔蘚的生命,而科學提供了一個說故事的強有力的方法,但這還不夠,故事還應該談談關係。苔蘚與我,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認識彼此。藉著說出它們的故事,我終於能透過苔蘚來理解這個世界。
在原住民的知識體系裡,我們會說一件事必須被四種面向的存在所認識,才能被真正地了解,那四種存在是:心智、身體、情感、精神。科學的知識則仰賴外在的實證資料,透過身體蒐集而來,再由心智去解讀。要說出這些苔蘚的故事,兩種方法我都需要,一個客觀和一個主觀的。這幾篇短文希望兩種認知的方式都得以發聲,讓物質和精神友善地並肩同行。有時,甚至共舞一曲。
在日常感知的邊緣,開始觀看……
我第一次對「科學」(還是宗教呢?)有意識的記憶,發生在幼稚園的課堂,在老舊的格蘭傑禮堂裡。當第一片迷人的雪花翩然落下,我們全都衝去把鼻子貼在結著白霜的窗子上。霍普金斯小姐十分睿智,身為教師,她知道在初雪的時候要遏抑五歲孩童的興奮之情有多困難,所以我們統統都出門了。大夥身著靴子和連指手套,在飄飄迴雪中圍繞在她身旁,她從大衣的深口袋裡摸出一副放大鏡。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第一眼透過鏡片看到的雪花,在她海軍藍大衣的羊毛袖子上閃閃發亮,像是夜空中的點點星光。經過十倍放大,那一片雪花的複雜細節令我驚奇不已。像雪這麼微小又平凡的事物,怎能如此完美無瑕?我情不自禁地看了再看。即使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最初的那一瞥,是如何充滿可能又深不可測。那是第一次,卻不是最後一次,我感覺到這世界的浩繁,不僅限於我們目光所及。於是當我看向輕落在枝頭和屋頂的雪片時,便多了一分新的認知:每一片雪花裡頭,都是星芒狀晶體構成的小小宇宙。雪的這分「秘密」令我讚嘆不已。那把放大鏡和那片雪花,是覺醒的鐘聲,是觀看的開始。從那一刻起,我模模糊糊地感受到,當你越仔細地觀看,這已然繽紛的大千世界將會變得更加動人。
學習看苔蘚這件事,跟我第一次對雪花的印象交疊在一起。就在日常感知的邊緣處,有另一個層面,是關於美、關於極小的葉子怎麼如一片雪花般有著完美的排列、關於肉眼難見的生物是如何複雜而美麗。所需要的,就只有注意力和觀看的方法。我發現苔蘚是深入了解鄉野的媒介,就如同森林的秘密知識。本書就是一份進入新視野的邀請。
初觀苔蘚後的三十年間,我一直都把手持放大鏡掛在脖子上。它的掛繩和我的藥袋的皮繩總纏在一起,這既是隱喻,也是事實。我所擁有的植物知識有很多不同來源,有從植物本身習得的,有作為科學家訓練而得,也有我身為波塔瓦托米族(Potawatomi)後裔,對傳統知識的直覺連結。在上大學學習它們的學名之前,我一直都把植物視為我的老師。學生時代,對植物生命的兩種觀點,主體與客體,精神與物質,就像纏繞在我頸上的兩條繩索。我被教導植物科學的方式,將我對植物的傳統知識推到邊緣。寫作這本書也是一個重新找回那分認知的過程,期望賦予它適當的地位。
古老的傳說說道,畫眉鳥、樹木、苔蘚和人類──所有的生物曾經共享一個語言。但那個語言早已被遺忘,所以我們得透過觀看、觀察彼此的生活方式,才能夠了解彼此。我想要訴說苔蘚的故事,因為它們的聲音很少被聽見,而我們又有這麼多事情要向它們學習。它們帶著重要的訊息亟待被聆聽,也就是有別於你我、屬於物種的觀點。身為科學家那部分的我想了解苔蘚的生命,而科學提供了一個說故事的強有力的方法,但這還不夠,故事還應該談談關係。苔蘚與我,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認識彼此。藉著說出它們的故事,我終於能透過苔蘚來理解這個世界。
在原住民的知識體系裡,我們會說一件事必須被四種面向的存在所認識,才能被真正地了解,那四種存在是:心智、身體、情感、精神。科學的知識則仰賴外在的實證資料,透過身體蒐集而來,再由心智去解讀。要說出這些苔蘚的故事,兩種方法我都需要,一個客觀和一個主觀的。這幾篇短文希望兩種認知的方式都得以發聲,讓物質和精神友善地並肩同行。有時,甚至共舞一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