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雖為中國傳統學術之主要精神命脈所在,但經過民國以來清算舊傳統的學術思潮洗禮後,蛻去神聖的外衣,轉變成為傳統學術中的某種反映古代歷史文化的原始資料或作為研究歷代受經學發展的詮釋學科。經學之所以不能受到新時代的重視,與其本身所展現出來的守舊本質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雖然經學確實有守舊的特徵,然從歷代的詮釋史來看,學者雖受限在聖賢本義的光環之下,但仍不乏企圖與創新詮釋取得平衡點的嘗試。若過度主張墨守故舊的原則,反而扼殺了經學進化的可能性。是以本文透過考察清儒所建構之經學守舊現象,發現這些現象皆普遍受清儒意識思維影響。
經學的發展至今雖已有江河日下之勢,但作為舊時代學術思想及道德精神支柱的地位,讓吾人絕不能簡單視為無味雞肋。故而作為為新時代的研究者,必須借鑒經學過去遭到批判的經驗,重新思考經學的價值與定位,尋求經學的活路。
本書特色
經學守舊的特性建構在傳統儒者復古的思維之下,儒者認為經為聖賢所傳,其中具有聖賢修身治世的重要義理思想與治世作為,故而即使談論通經致用者,亦必需局限在聖賢的文字之中,往往亦非實用之用,而將之作為正人心之用。
清儒以考據為學術特色,在這種學風下,特別重視經學考據的證據來源,尤其清儒的目的在越宋學而直趨漢學,是以漢唐之前的經學現象得以被挖掘或被強化呈現,亦可算是清代學術必然的發展。傳統對歷史現象之研究者,必需運用史料內容加以說明,有什麼證據,方能建構出相對應的歷史,因此,可以說,歷史的現象是建構在後人的分析歸納中。然新歷史學研究主義者則指出歷史的建構是由論述組成,其中包含著與提出論述者相對應的時代觀念,也就是說,歷史現象的建立,擺脫不了建立者的主觀意念。於是本書由此出發,針對清儒所提出的經學守舊思想進行闡述。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經學守舊考:以清儒所構建之經學守舊現象為探討核心的圖書 |
 |
經學守舊考:以清儒所構建之經學守舊現象為探討核心 作者:姜龍翔 出版社: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11-2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15 |
中國哲學 |
$ 315 |
中國哲學 |
$ 315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33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經學守舊考:以清儒所構建之經學守舊現象為探討核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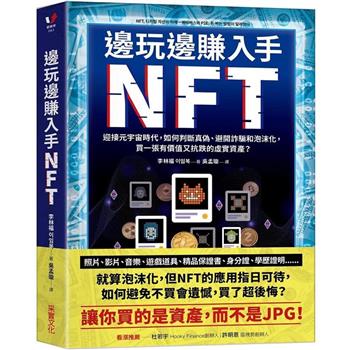

![向大師學繪畫:西方藝術大師名畫復刻版,讓繪畫技巧升級的14堂繪畫課[隨書附贈28支示範影片] 向大師學繪畫:西方藝術大師名畫復刻版,讓繪畫技巧升級的14堂繪畫課[隨書附贈28支示範影片]](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94/2019479578260/2019479578260m.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