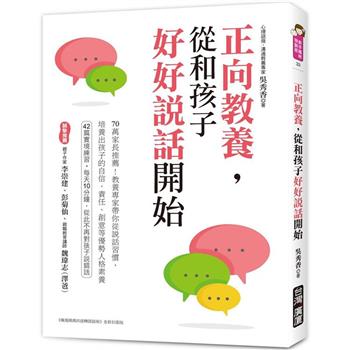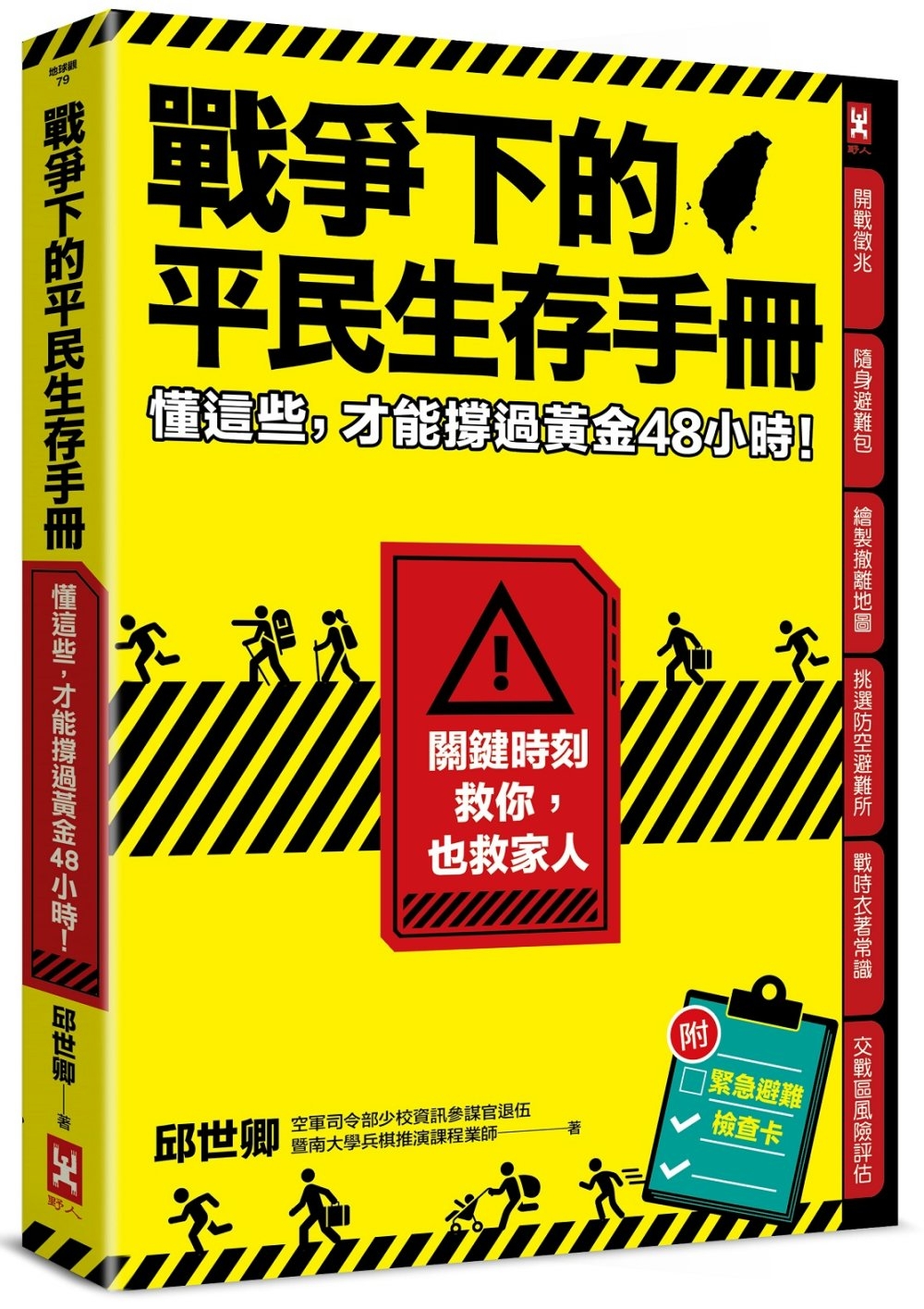Episode 3
「這是什麼新招式?花拳繡腿?」陳百七輕輕鬆鬆單手擋下齊樂人的飛踢,後者因為重心不穩趔趄了一下,差點摔倒。
「我的體術確實就只有這個水準,盡力了。」齊樂人挺委屈地說。
他才訓練多久啊,扎馬步還要被嫌棄下盤不穩,上手一對一更是被陳百七吊著打。
「學著點,不要總覺得學體術很不爽。我跟你說,這對你的性生活和諧很有幫助。」陳百七說道。
「?」齊樂人一臉懵逼,他是不是聽到了什麼奇怪的詞語從他老師的嘴裡冒出來?
「怎麼,不信?」陳百七似笑非笑地看著他。
「咳咳,我都有半領域了,什麼時候換個課程表教教我怎麼用?」齊樂人尷尬地咳嗽了兩聲,右手托起一個緩慢旋轉的光球轉移話題。
自從在地下蟻城突破到半領域後,這個半領域世界就像是一個隨身攜帶的空間一樣,他可以控制它的出現和消失,也可以自由地出入,但是究竟要怎麼使用它,讓它變得強大凝實,卻著實讓齊樂人捉摸不透。
他有想過要不要問問寧舟,可反覆思量後他還是嚥下了這個問題──因為寧舟從來沒有主動提起過自己的半領域,他連看都沒有讓齊樂人看過。
很顯然,這是寧舟心中一個不願意提起的禁忌,他憎惡這種力量。
齊樂人決定,還是找個更合適的時機談談這個問題,例如他們訂婚之後。
訂婚……想到這個,齊樂人忍不住翹起了嘴角。
距離寧舟的生日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他悄悄找呂醫生打聽了買戒指的事情,呂醫生無奈表示他也不太懂行,不過他會幫他留意的。前幾天呂醫生來找他,說幫他向薛盈盈打聽了一下,有一家戒指店很有名,最近帶他去看看。
齊樂人不禁蠢蠢欲動,以至於今天早上的訓練都有點心不在焉。
只可惜,他的美好想像全都被陳百七打破了,她嗤笑了一聲:「你這小破玩意兒也敢叫半領域?樂人小朋友,你還差得遠呢。」
「啊?」齊樂人有點懵逼。
「你的半領域,現在最大直徑是多少?」陳百七問道。
「呃……大概一兩百公尺吧。」齊樂人說。
除了在衝破殺戮魔王的領域投影時爆發了一下,平時它的確就只有這個範圍。
「哦。」陳百七翻了個白眼,冷漠地應了一聲。
齊樂人頓時訥訥地,不敢說話。
「你知道黃昏之鄉的面積有多大嗎?」陳百七問。
齊樂人搖搖頭。
「落日島,連同大陸部分那一角,共計四百七十六平方公里,不算海域面積的那種。」陳百七慢條斯理地說著。
齊樂人心虛地看著腳尖。
「目前住人的幾個領域中,黃昏之鄉是最大的,但就算是最小的『雲渦』領域,也有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面積。」
「雲渦領域,是什麼?」齊樂人在玩《噩夢遊戲》的時候沒有見過這個名詞,不由好奇地問道。
「一個玩家的領域,名叫雲渦,距離黃昏之鄉比較遠,而且在天上。領域持有人很年輕,也很低調,是個中立勢力。這種小領域在噩夢世界不是沒有,但沒有一個可以和黃昏之鄉相比。」陳百七緩緩道。
「畢竟是人類最後的淨土嘛。」齊樂人說。
陳百七沉默了。
夕陽徘徊在地平線附近,她拿出菸給自己點了一根,望著夕陽,滿目惆悵。
「先知他,就像是黃昏之鄉那一輪搖搖欲墜,卻不曾落下的夕陽。可它總會落下的,沒有什麼是不朽的,誰都總有那一天。樂人啊,你……還有你們這些年輕人,不要讓他一生都孤獨地在天上發著光。」
一陣無法抑制的傷感彌漫在了齊樂人的心頭,他有很多事情想問,例如先知的懷錶為什麼會出現在蘇和的身上。可陳百七顯然是不知道的,她連黎明之鄉的真相都不知道。
顯然,關於黎明之鄉和蘇和的一切,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知曉。
也許哪一天該再去見見先知?齊樂人默默心想。
「來吧,我們去海邊走走,順便聊聊。」陳百七對齊樂人勾了勾手,自己轉身就走了。
今天的訓練還沒完成,但竟然提前下課了?忍不住竊喜了幾秒的齊樂人控制住了臉上雀躍的表情,畢恭畢敬地跟在陳百七的身後。
「半領域,很好。其實從實力上來說,你已經勝過我了。」陳百七吐了一口煙圈,那稀薄的煙霧頃刻間就被海風吹得了無痕跡。
齊樂人把頭搖得飛快,長期以來他就一直在被陳百七吊打,這種力量的差距已經讓他快有心理陰影了。
陳百七哈哈一笑,一邊走一邊彈了彈菸頭:「如果是我的半領域還在的時候,我欺負欺負你絲毫沒有問題,可惜那時候我還太年輕了,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人心險惡,總以為自己走到了半領域的這一步,理所應當地要承擔起我的責任,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可有些人,並不值得你的守護,這也是我不理解先知的一點。」
「我很尊敬他,他和寧舟,都是那種具有『神性』的人,我曾經以為我也是這樣的,哪怕經歷欺騙、背叛、挫折,我也不會改變我自己,可最後我明白了,我只是個自私的普通人。我會害怕正義被埋沒,卑劣卻被歌頌,也害怕善行被污蔑,犧牲卻被忘卻。我越來越冷漠世故,時常感覺到當年那個心有熱血的我已經隨著半領域的破碎而死去了。你看,人總是很容易被現實改變,也很容易用冷漠去掩飾自己的害怕與無能。」站在海堤旁的陳百七眺望著海平線附近的落日,那海風吹得她的長捲髮獵獵飛揚。
這是齊樂人第一次聽到她評價她自己。
有太多關於她的事情,他其實並不知道,她也不準備讓他知道。
長久以來,陳百七幾乎不會談論她自己,他對陳百七的一切瞭解都建立在對她言行的印象裡,她表現得很冷酷,卻又有人情味,她其實並不是她自以為的那麼冷漠市儈。
她的生意,也從來不僅僅是生意。
「為了曾經的那份天真熱血,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看著先知,我時常會想,也許只有他這樣的人才能成為『神』吧,而我們都不過是被神所庇護著的芸芸眾生,在搖搖欲墜的黃昏裡苟且偷生。」陳百七的左手撫摸著自己的左腿,看著遠方的神情流露出些許的倦怠和惆悵。
「先知和我談起過一件事。」齊樂人思索片刻後開口道,「他想讓我繼承黃昏之鄉的一部分。」
陳百七挑起了細長的眉,表現出了興趣。
「但我拒絕了。」齊樂人笑了笑。
「那你虧大了。」陳百七也笑。
「妳覺得先知幸福嗎?」齊樂人問她。
陳百七皺了皺眉,用力吸入了一口充滿了尼古丁的空氣,任由它在肺裡盤旋,可控地損害著她的器官,卻給她帶來短暫的平靜,這種感覺令人迷戀。
「我恐怕無法回答,他自己也是。對於他來說,幸福與否已經不再重要了,就像你不會去問一隻螞蟻是否幸福,也不會去問上帝祂是否幸福,因為這是屬於人類的體驗。」陳百七回答道。
這個回答讓齊樂人略感意外,可能是他此刻的表情取悅了陳百七,她背靠在海堤上舒展了後背,緩緩道:「憤怒、悲傷、喜悅、愛情……這些誕生於大腦中的感覺,脫離了人類的這個軀殼和身分,就再也不算什麼了。你看,沙灘裡那兩隻為了地盤打架的螃蟹,對牠們來說,這是生死存亡繁衍存續的大事,可跳出了螃蟹的身分,我們所看到的,不過是兩隻螃蟹在無聊地打架罷了,你有興趣還可以走過去一手一隻地捉走,放在鍋裡蒸了吃。」
齊樂人盯著螃蟹,靜靜地思考了很久。
「……我有點明白妳的意思了。」齊樂人說。
「不,你不明白。讓我猜猜你為什麼拒絕先知,因為你知道,再往前走你也會逐漸被本源力量吞噬,逐漸失去屬於人類的情感,也許還有記憶,而你並不想失去,特別是愛情。」陳百七說。
「嗯……」
「我糾正一點,先知和你的本源力量都不是很極端的那種,你們所受的影響不會像殺戮或者毀滅那麼大。」陳百七說。
齊樂人的眼睛一亮。
「但是,這也不意味著你會沒有影響。先知曾經開過一個玩笑,說他都快忘了自己是男是女,走到廁所的時候能想起來,因為身體記得他站著尿尿。」
「……」齊樂人簡直想求先知不要亂說話了,他這個人一開口真是實力自黑。
「等到踏入領域級之後,人就會逐漸淡忘從前的一切,最執著的東西倒是能銘記下來,只是也容易被扭曲得似是而非,特別是那些極端的力量……」陳百七說道。
齊樂人不禁想到了那位忘記了摯愛的毀滅魔王。他忘了,卻也沒有忘,也許正是那種扭曲的執念讓他不顧一切地撕開通往人間界的縫隙,最後釀成了這樣的悲劇。
「現在你還只是半領域,充實它凝固它,然後尋找契機突破,這個契機也許一生都不會碰到,也可能你明天就碰到了。在那之前,好好保護你的半領域,不要頻繁使用它,也不要用它去和別人的半領域硬碰硬。你如今的力量只能夠在自己的半領域中發揮,例如那個樹墓,能讓你迅速修復重傷。但如果你成就了領域,那就很可怕了,因為領域中的力量甚至可以干涉現實。」陳百七說道。
「干涉現實?」齊樂人喃喃著這個詞語。
「對,假設我有一個領域,我就可以輕輕鬆鬆碾壓你的半領域,讓我領域內的力量外放影響你,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可以用我領域中的重力將你壓趴在地上,甚至碾成一團肉泥。」
這個招式齊樂人見過,在聖修女的夢境中,蘇和就是用這種方式外放了領域的力量,將夢魘魔女制住,他還用領域的力量干涉過視野範圍內怪物,讓它們無法發現他們的存在。
一股寒意從腳底滲了進來,越是往前走,就越是意識到自己曾經和一個多麼可怕的敵人共處,除了後怕就是後怕。
「也許你成就領域的時候,你的領域之中將是一片不死之地,哪怕你死亡,也會回到自己的領域重生,直到你的靈魂力量徹底衰竭。真可怕,和擁有重生本源的人做對手,簡直像是隻打不死的小強。」陳百七感嘆道。
「……老師,能用個好點的比喻嗎?」齊樂人鬱悶道。
陳百七大笑了起來:「你去數數亡靈島的墓碑再來反駁這句話吧。」
難以反駁的齊樂人只好選擇閉嘴。
突然,他突然聽到了一聲清亮的語鷹叫聲,猛地回過頭。
迎著那豔麗的晚霞,世界彷彿被鍍上了一層橙色的光,就在那光的盡頭,有一個人正朝著他走來。
齊樂人笑開了臉,亟不可待地問陳百七:「我能回家了嗎?」
「滾吧!」陳百七沒好氣地說。
齊樂人聞言,都忘了和陳百七道別,他是如此迫不及待地向寧舟跑去。
海風中,夕陽裡,他們交換了一個相隔不到十個小時的擁抱,卻好像已經分別了一個世紀。
◎
「你可算來了,怎麼,今天休息?」呂醫生開門見到一臉萎靡的齊樂人,趕緊把人放了進來,「你來得可真是時候,我買了新鮮出爐的小蛋糕當下午茶,哈哈。」
「我請了半天假來的,你不是說那家店晚上很早關門嗎?而且我也找不出其他時間,晚上的時候我都是和寧舟在一起的。」齊樂人說。他誠實地告訴陳百七他要去給寧舟買個訂婚戒指,讓她瞞著寧舟,陳百七嘖了嘖嘴,很不爽地批假了。
「懂了,你們這是一分鐘都不想分開,所以寧可請假逃訓,是吧?」呂醫生搓了搓胳膊,一副被情侶傷害了的單身狗的樣子。
齊樂人呵了一聲:「是啊,羨慕嫉妒恨啦?」
呂醫生捂著胸口往沙發上一倒,生無可戀地說:「脫團狗,別想吃我的小蛋糕了!」
「還走不走?」齊樂人催促道。
「先吃了再走吧,不急。」呂醫生說。
齊樂人也有點餓了,高強度的訓練總是很快耗盡了他的體能。這幾天的訓練內容是潛入刺殺,陳百七不知道怎麼請來了幻術師,幻術師大方地用上了自己的技能卡,那張技能卡能輕易改變周圍環境,塑造成截然不同的景象,模擬不同的場景。齊樂人如同被貓欺負的老鼠一樣,在兩人的聯合訓練下奄奄一息。
不能再想訓練的事情了,他得休息一下,齊樂人心想。
吃著蛋糕,喝著茶,齊樂人整理了一下心緒。
「我記得你是博士,學過心理學嗎?」齊樂人問呂醫生。
「啊,多少選修過一些,不過不是很專業啦,你想問什麼?」呂醫生問。
「其實我有點擔心寧舟的心理狀態。他和我們的成長環境差別太大了,他所信仰的宗教和受到的教育造成他忽視自我,或者說他覺得犧牲和奉獻就是自己應該做的,因為每個人身負原罪,生來就是要贖罪。除了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他這輩子沒做過什麼違背信仰的事情。」齊樂人靠在沙發上,喝了一口紅茶,緩緩對呂醫生道來。
長久以來壓抑在他心中的,關於寧舟的一些事,他找不到任何人來傾訴,他也不知道要怎麼幫助寧舟,只好向呂醫生求助。
「原罪論,我知道。不過寧舟所受到的影響比一般人要深得多,所以他選擇離開教廷所要承受的自我譴責非常強烈。」呂醫生說。
「是的,而且他離開教廷,並不代表他背棄了信仰,他依舊是相信的,他只是在深思熟慮後明知故犯了。所以他相信自己死後會墜入地獄,永生永世在火湖中受刑。在我們看來這只是虛無縹緲的死後世界,可是對他來說,那是真實的存在。只是因為愛情,他願意。」齊樂人哽咽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氣才緩過來,「他無法消除這種絕望感,這太痛苦了。哪怕我陪伴在他身邊,這種痛苦仍然會永遠伴隨著他,可我卻不知道要怎麼幫助他,所以才難過。」
對寧舟來說,這並不是一份帶來幸福的愛情,可以說它帶來的苦難比甜蜜多上千萬倍。
可它已經誕生,就再無法割捨。
它已然是靈魂的一部分。
「現在我死而復生,固然是一件好事,但……真的有太多問題了。有很多事我們至今不敢攤在檯面上說開,哪怕我們都知道這幾乎是必然會發生的,對此寧舟有他的想法,我也有我的選擇,一旦開口,就……就再也不會有現在這樣幸福甜蜜的時光了。」齊樂人說道。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失去控制的寧舟犯下不可原諒之罪,他是要選擇殺了寧舟,以維護寧舟愛著的世界,還是選擇放任,看著他走向面目全非,將這個世界毀滅殆盡?
夜深人靜的時候,每每想到這個問題,他就再也難以入眠。
他偷偷地祈禱著這一天不要到來,或者在這一天來臨之前,他們離開這裡,去一個沒有人的地方,例如他凝實後的半領域中,在開滿白玫瑰的花園中不問世事地度過餘生。
呂醫生迷茫地看著他,他對領域和本源力量都懵懵懂懂,這不是他能夠接觸到的層次了,所以他不清楚齊樂人此刻在糾結什麼。
迎著呂醫生疑惑的眼神,齊樂人說道:「我還擔心一點,寧舟現在過分重視我,重視到根本不能接受我受傷,更別說死亡。所以現在我很怕死,如果我死了,寧舟要怎麼辦呢?」
這份執念支撐著他熬過了那麼多艱難的任務,哪怕在殺戮魔王的領域投影之中,他都撐了過來,甚至凝結了半領域。可人的意志和信念也不能抵抗絕對的力量,如果當時的殺戮魔王不是一個小小的傀儡分身,他恐怕連突破都來不及就已經永遠死亡。
「你們兩個……嗯,太為對方著想了。簡直就是處處為別人著想不求回報,默默奉獻的暖男型人設,幸好是搞基了,不然簡直活活一輩子備胎男二啊。」呂醫生思維跳脫地感慨了起來,「要是戀愛的人都像你們這樣瞻前顧後死命為對方著想,誰還敢輕易談戀愛結婚啊。像你們這種談法,扯了證就是一輩子『已婚』,除非哪天『喪偶』,反正絕不可能『離婚』。」
「……能說點吉利的話嗎?」齊樂人無語。
「啊啊啊啊啊,我錯了我錯了!不可能喪偶!你們百年好合!」呂醫生反應過來立刻捂住了嘴,「來來來,我教你折紙玫瑰花,別打我!」
「下次再來學,先去買戒指吧。」齊樂人還是心急戒指。
「成吧,走!」呂醫生從沙發上跳了起來,一溜煙地跑出了門──被自己的鞋子絆了一下,摔倒在了大門口。看來他的自我訓練並沒有幫助他擺脫平地摔。
齊樂人慣例想要吐槽一下小夥伴,可是看到呂醫生委屈巴巴的表情,還是把話嚥了回去,轉而將人扶了起來:「你也小心點。」
「嘿,這也沒辦法啊,天生的。」呂醫生摸了摸後腦勺,有點遺憾地說,「可能是為了平衡一下我的智商,所以上帝在創造我的時候就把我的運動神經給削弱了。」
「你確定不是為了平衡你的幸運值?」齊樂人反問。
呂醫生摸了摸下巴:「有道理哦。」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歡迎來到噩夢遊戲II(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61 |
科幻/奇幻小說 |
$ 297 |
中文書 |
$ 297 |
華文 |
$ 297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歡迎來到噩夢遊戲II(下)
兩人從地下蟻城回到黃昏之鄉後,
再度攜手一起進入新的任務副本:黑幫帝國。
這是一個一九二○年代美國愛爾蘭與義大利黑幫爭鬥的時代,
玩家將取代其中的NPC角色,並兩人一組,在副本中獵殺其他玩家。
演技高超的齊樂人順利成為一個文青風格的冷漠殺手,
而寧舟,卻變成一個七歲金髮小正太……
齊樂人人生第一次體會到了萌到暈厥是什麼體驗。
生活與戀情似乎都漸漸穩定下來。
齊樂人決定要在寧舟的生日,也是黃昏之鄉的建立日那天,
對他提出求婚。
然而來自欺詐魔王與權力魔王的陰影,
仍籠罩著他們晦暗不明的混沌未來……
本書收錄番外〈漫長的思念〉。
作者簡介:
薄暮冰輪:前銀河外星系腦洞第一、批發、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唯一員工,現已被喵星人哈尼捕獲並淪為貓奴,沉迷給主子寫貓段子和甜文,著有《歡迎來到噩夢遊戲》、《彩蛋遊戲》、《鳥語專家》等作品。微博@薄暮冰輪
章節試閱
Episode 3
「這是什麼新招式?花拳繡腿?」陳百七輕輕鬆鬆單手擋下齊樂人的飛踢,後者因為重心不穩趔趄了一下,差點摔倒。
「我的體術確實就只有這個水準,盡力了。」齊樂人挺委屈地說。
他才訓練多久啊,扎馬步還要被嫌棄下盤不穩,上手一對一更是被陳百七吊著打。
「學著點,不要總覺得學體術很不爽。我跟你說,這對你的性生活和諧很有幫助。」陳百七說道。
「?」齊樂人一臉懵逼,他是不是聽到了什麼奇怪的詞語從他老師的嘴裡冒出來?
「怎麼,不信?」陳百七似笑非笑地看著他。
「咳咳,我都有半領域了,什麼時候換個課程表教...
「這是什麼新招式?花拳繡腿?」陳百七輕輕鬆鬆單手擋下齊樂人的飛踢,後者因為重心不穩趔趄了一下,差點摔倒。
「我的體術確實就只有這個水準,盡力了。」齊樂人挺委屈地說。
他才訓練多久啊,扎馬步還要被嫌棄下盤不穩,上手一對一更是被陳百七吊著打。
「學著點,不要總覺得學體術很不爽。我跟你說,這對你的性生活和諧很有幫助。」陳百七說道。
「?」齊樂人一臉懵逼,他是不是聽到了什麼奇怪的詞語從他老師的嘴裡冒出來?
「怎麼,不信?」陳百七似笑非笑地看著他。
「咳咳,我都有半領域了,什麼時候換個課程表教...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