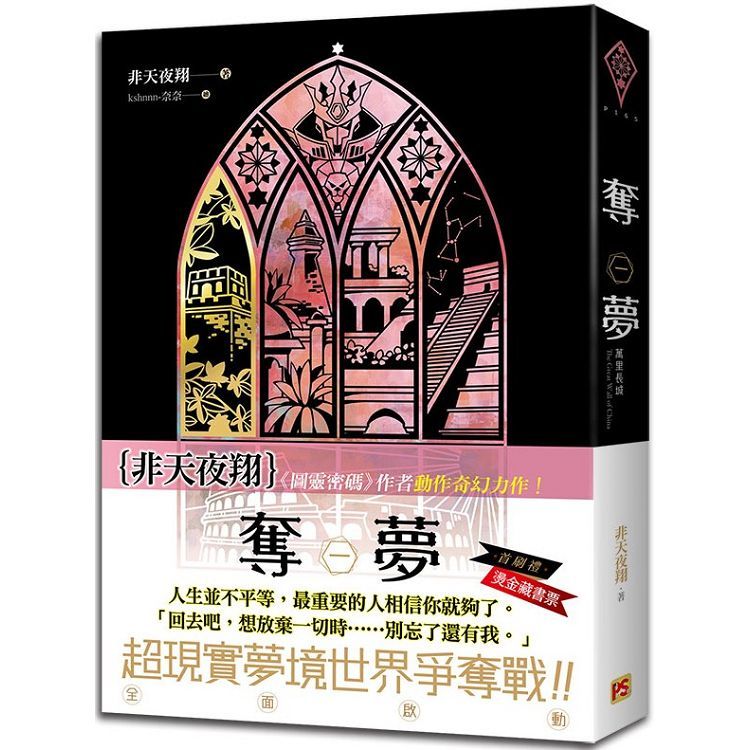一樁故意誣陷的竊盜指控,面臨校方冷漠施壓,
成了壓垮余皓十八年不幸人生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沒有親人、朋友,還是個同性戀,
赤貧彷彿成了一種原罪,窮人就該墮落。
既然身不由己,至少他能選擇何時結束。
燒炭自殺後,他站在夢過無數次的長城邊緣,
滿心絕望,即將跌下眼前深淵之際,
一名身穿鐵鎧的男人伸手拉住他──
「我是將軍,你的夢境守護者。」
將軍給了余皓信任與希望,在對方的幫助下,
余皓成功奪回自身夢境的主宰權,打敗內心的黑暗。
臨別時刻,他將夢境圖騰捻下一塊送給對方;
是將軍點燃他新生的勇氣,余皓也希望能守護他!
不再封閉內心,余皓獲得了新朋友、新生活,
然而新的疑問同時開始不斷浮上──
將軍到底是誰?會是自己身邊的某個人嗎?!
本書特色
《圖靈密碼》作者非天夜翔老師動作奇幻力作!
人生並不平等,最重要的人相信你就夠了。
「回去吧,想放棄一切時……別忘了還有我。」
超現實夢境世界爭奪戰全面啟動!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奪夢 一 萬里長城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 261 |
科幻/奇幻小說 |
$ 281 |
華文 |
$ 281 |
小說/文學 |
$ 297 |
中文書 |
$ 297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奪夢 一 萬里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