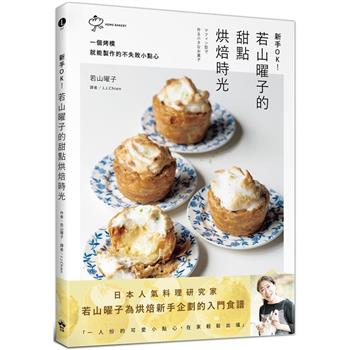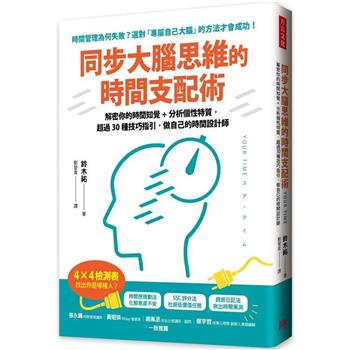第二十一章
趙肅有生以來第一次碰到這種完全不知該如何解決的難題。
素來冷靜自持的他連外衣也忘了披上,就這麼坐在床榻上發呆。
直到日上三竿,外頭傳來敲門聲。
「大人?大人!」趙吉連喚了數聲不見應答,連舊日的稱呼也出來了。「少爺!」
趙肅略略回過神。「什麼事?」
「您起身了嗎,小的端水來給您洗漱吧?」趙肅的作息很規律,每日必然早早起來鍛鍊,但今天居然睡到這個時辰,也難怪趙吉詫異。
「等一會兒。」趙肅起身穿好衣服,又整理了一下,轉頭瞥見床上的凌亂,又頭疼了。
「進來吧。」
趙吉推門而入,看到趙肅穿得整整齊齊坐在桌旁,不由一愣。
「大人,您早就起了?」
「陛下呢?」
「陛下天剛亮就回宮了,臨走前還吩咐我們不要喊醒您,讓您睡個夠。」
趙肅沉默片刻,「我要進宮一趟,你把屋裡拾掇一下。」頓了頓,加了一句,「被褥都燒了吧,你親自動手,對外不可隨意亂傳。」
這麼些年歷練下來,趙吉已不復少年的毛躁,跟在趙肅身邊,看過聽過許多事情,也明白守口如瓶的道理,所以儘管心裡好奇,卻只是連忙應聲,而沒有多問。
趙肅不再說話,過了會兒,起身走至門口時,又停下來。
「晚飯不用等我了,你們先吃,也不用讓人到宮門口接我。」
「是。」趙吉從來沒有見過趙肅如此心神不屬的模樣。「大人,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情?」
「沒事。」趙肅大步往外走,風揚起衣襬寬袖,說不出的倜儻俊逸。
這個時辰,皇帝應是剛議事完畢,在偏殿看摺子的。
但是經過昨晚一夜的折騰……
趙肅有些吃不準,還是先往乾清宮而去。
遠遠的,一人迎面而來,後頭數人跟隨,端的氣場強大。
趙肅腳步稍稍一頓,隨即迎上去。
「元翁可好?肅昨日方回,未及見過元翁,還望元翁莫要見怪!」
張居正哈哈一笑,伸手過來虛扶,「少雍,半年未見,別來無恙!」
趙肅含笑,「託元翁的福,尚好。」
張居正擺擺手,美鬚迎風飄揚,顯得意氣風發。「昨日剛回,便多休息幾日再說,怎的急吼吼進宮來?」
考成法實施之後,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剔除了不少冗員腐吏,連續兩三年下來,已經頗有成效,政令一出,舉朝上下雷厲風行,莫敢不從。不可否認,張居正一馬當先,手段狠辣,是考成法能夠堅決執行下去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沒有皇帝和趙肅的從中助力和推波助瀾,進展也不會如此之快,成效不會如此之大。
細算起來,歷史上原本要到萬曆八年時才會開始的土地改革,如今眼見情勢大好,張居正已經在盤算著開始清丈全國土地的事宜,露出向田地賦稅下手的端倪。
當然,他在推行考成法的同時,也藉此剷除了許多不同的聲音,只是趙肅這幾年一心在工部做事,與張居正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且對同黨與下屬都再三約束,張居正也抓不到他的把柄,故而兩人相安無事,尚算太平。
如今張居正位居內閣首輔三年有餘,自忖一呼百應,威望日強,也漸漸不再像早年那般隱忍壓抑,說話做事都帶了股凌厲逼人的咄咄氣魄。
相比之下,趙肅有問必答,含笑束手時,似乎顯得有些弱勢,然而旁人若仔細一瞧,就會發現,他的舉止言行,實是一種安之若素,不亢不卑的氣度。
趙肅道:「南下時,我見了佛郎機人的船艦,知陛下對此大有興趣,正想進宮詳稟。」
張居正笑得意味深長,「喔?我還道你是為了陳以勤和葛守禮致仕的事情。」
趙肅有些意外,「陳、葛二位閣老要致仕?」
張居正見他確實不知,便道:「他們已經上了請求致仕的奏疏,只等陛下批覆,左右也在這兩日了。」
趙肅嘆息:「兩位大人為官清正,數十年高風亮節,是該好好歇息一下了。」
張居正道:「少雍若是有事面見陛下,但去無妨,就不必與我閒話了,等過幾日你回內閣再敘不遲。」
趙肅道:「既如此,肅便先行一步,元翁走好。」
張居正點頭,待他上前錯身而過時,用只有二人才能聽見的聲量說了一句話:「陳以勤、葛守禮一去,就要恭喜少雍更進一步了。」
趙肅腳步不停,恍若未聞,轉眼便已走出老遠。
張居正看著他的背影,微瞇起眼,良久才嘆道:「趙少雍風華正茂,將來大有可為!」
他比趙肅大了整整二十歲,言下之意,頗為自己的年紀而感慨。
站在旁邊的張四維一笑,「元翁正當盛年,何故發此慨嘆?」
「此人隱而不發,諸事忍讓,甘願屈居人後,且不重虛名,與他老師高拱大有不同。高拱此人,我尚摸得清他的想法,但趙肅的心思……」張居正頓了一下,搖搖頭,沒說下去。
「元翁多慮了,如今考成法卓有成效,您朝野皆有威望,何懼區區趙肅?」
「我當然不懼。但陳以勤、葛守禮這一走,論資排輩,就該輪到他上來了,而你,也要排在他後面。」他瞥了張四維一眼。「此人對我的政見,時而贊同,時而反對,讓人捉摸不透,有他隔在中間,於新法總歸有阻礙。」
他沒有說出來的話是:趙肅不是自己的心腹同黨,有這麼個人在,總是不能放心。
張四維皺眉,「但是趙肅最近沒出什麼差錯,想抓把柄,似乎不易。」
張居正望著遠處宮殿飛簷之上的高闊天空。「那就再看看罷。」
趙肅在門口等了片刻,進去通報的張宏走出來,面有難色。
「趙大人,陛下說他身體不適,今日就不見了,您請回吧。」
身體不適?
趙肅心頭一跳,隱約想起昨夜翻雲覆雨時那人的痛楚哼聲。
他嘆了口氣,「煩請公公再通稟一聲,就說趙肅在此請罪,直到陛下肯見臣為止。」說罷撩起袍子,端端正正跪了下來。
張宏被他嚇了一跳,「趙大人這是做甚,快快請起!」
他勸了一會兒,見勸不動,只好又折返回去見皇帝。
「陛下,趙大人在外頭不肯走,說要等到陛下肯見他為止。」
朱翊鈞心頭一喜,抬起頭,聲色不動。「喔?那就讓他等等吧。」
苦肉計要做就要做全套,才能收效。
他並不知道趙肅是跪著等的,張宏也沒有說,只當趙肅忤逆了皇帝,兩人正鬧著彆扭呢。
過了片刻,朱翊鈞終究是按捺不住,「去看看,他還在外頭麼?」
張宏應了一聲,出門一瞧,回來道:「陛下,趙大人還在外面跪著。」
朱翊鈞大吃一驚,繼而怒聲道:「跪著?!你怎麼不早說!」
張宏苦著一張臉,囁嚅道:「奴婢以為陛下知道呢!」
「去,把人請進來!」
趙肅進來的時候,便看見朱翊鈞正拿著手中的內閣票擬在看,神情極是認真,但臉色略帶蒼白,掩不住疲弱之態。
一時之間,百味雜陳,難以言喻。
「臣,參見陛下。」
「趙師傅請起。」朱翊鈞面色如常,沒有憤怒,沒有難堪,沒有其他多餘的表情,一切似乎沒有變化。「你來得正好,朕有事與你說。」
「陛下請講。」
「陳以勤與葛守禮二人,不日就要致仕榮休,內閣又該進人了,你心中可有合適的人選?」
趙肅沒有料到他一開口問的是國事,愣了一下,方道:「臣也是剛剛得此消息,一時之間尚無人選,且待臣回去細想再上疏。」
朱翊鈞點點頭,從桌案後起身,正想說什麼,卻不小心扯動傷口,臉色扭曲了一下。
趙肅看在眼裡,抿緊了唇,上前幾步,扶住他。
「陛下……」
朱翊鈞打斷他:「楊博早在萬曆元年就已走了,陳、葛二人再一走,你便要躍居次輔,位列張師傅之後。然則,你現在還管著工部,雖說為朝廷做事,不分先後,但工部位居六部之末,名義上畢竟不是很好聽,朕思忖著,不如在戶部給你騰挪個位置,你再找個信得過的,去管工部。」
趙肅哭笑不得,「陛下,如今戶部有王國光,臣怎好貿然去搶別人的位置?」
再說了,戶部地位太過重要,就算他想搶,張居正也不會答應。
他見朱翊鈞站定,便鬆開手。
朱翊鈞道:「這不是在計議麼,又不是要定下來。」他定定瞧著趙肅鬆開的手,強笑道:「朕還記得小時候,你總牽著朕的手,現在怎麼倒不牽了?」
趙肅默默跪下,將冠帽摘下雙手置於地上。「臣是來請罪的。」
朱翊鈞面無表情,「你何罪之有?」
「臣昨夜……一時莽撞,冒犯君威。」
「朕一廂情願,與卿何干?」
趙肅心神劇震,他想過許多種局面,卻沒想到皇帝會挑明了說。
「臣死罪。」他以額抵地。
「朕讓你進來,就是想讓你請罪的麼?」趙肅聽得皇帝呵呵一笑,卻是落寞孤寂。
「朕自幼得你教導,在你身邊長大。我們走市集,讀詩書,及至後來嘉靖宮變,同生共死。你有難,朕五內俱焚,朕有事,你一心一意為朕排解。你我二人,縱然說不上心有靈犀,可也總算相攜相扶,放眼古今,這等君臣,可多?」
朱翊鈞的聲音低了下來:「朕視你如師,視你如父,半分也不願褻瀆這份情意,可是,若能控制便好了。情之所至,何由人心?」
趙肅沉默良久,啞聲問:「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朱翊鈞笑得苦澀,「朕若知道就好了。朕還記得小時候生了一場大病,醒來時就見你在身旁,那種感覺,到現在都不會忘記,也記得你握著朕的手,教我寫字的情景,甚至記得有一年上元節,你我走遍了大街小巷去看燈……這些事情歷歷在目,想忘,也忘不了。可你若要問什麼時候開始,也許是五年,也許是十年,也許是更久之前。」
朱翊鈞見他沒有反應,退了幾步,愴笑:「你不願接受,朕也不會勉強你。昨夜,昨夜之事,就當作是一場夢罷,你我之間,還是君臣,朕也依然,會把你當成良師,你,你盡可放心了吧。」
趙肅不知怎的,腦海裡忽然閃過許多畫面,卻都是兩人相處時的情景,他眼眶一熱,閉了閉眼,抬起頭,正想說什麼,卻全然愣住。
皇帝的嘴唇緊緊抿著,蒼白的臉上布滿眼淚,頭卻微微仰起,死死盯著橫梁。
此情此景,趙肅縱是鐵打的心腸,也不能不軟下來,何況他對朱翊鈞,是全心全意的愛護,即便也許沒有朱翊鈞那種心思,傾注卻半分不比對方少。
他嘆息一聲,起身,拿袖子去擦那眼淚。
「別哭,一國之君呢……」
朱翊鈞的眼淚流得更凶了,看著他,眼底有著明顯的脆弱和哀求。
趙肅喉頭滾動,聲音也已沙啞:「臣是個老男人,沒有姿色,陛下何以……」
「朕愛你一心為國,殫精竭慮,朕愛你溫文儒雅,對敵從容,朕愛你與他人周旋,談笑間讓對方敗倒,朕還愛你陳述國事時意氣風發的樣子……這些,可夠?」
皇帝的手欲摸向他的臉,趙肅微微一僵,卻終是沒有避開。
少頃,卻在指尖要碰到時,手縮回,朱翊鈞流著淚,慘笑:「你走吧,走吧。」
他轉過身,肩膀微微顫抖,不再看對方。
等了半晌,也沒聽到身後的腳步聲。
卻聽見趙肅嘶啞的聲音:「陛下,容臣想想……」
朱翊鈞欣喜欲狂。
以趙肅的性格,能說出這句話,何其可貴,這說明他的心神已經被動搖。
慚愧,內疚,不捨,感動,諸多感情加在一起,縱然還不是朱翊鈞最終想要的,但已足夠。
他轉身,顫抖著唇,問:「你說什麼?」
趙肅想起昨夜種種,再看皇帝定定瞧著自己,怎麼也說不出拒絕的話。「臣,也許沒法做到陛下那樣……」
「你沒有掉頭就走,朕已滿足了。」朱翊鈞流著淚微笑,張開雙臂。「能讓朕抱一會兒麼,就一會兒。」
小心翼翼乞求的模樣讓趙肅心頭更痛。
伸出手,慢慢將他環住。
朱翊鈞立時緊緊回抱,再不肯放開。
他不停眨眼,淚水想止也止不住了,直沖得雙眼紅腫,心道:這辣椒水後勁也太大了!
◎
樂極生悲的後果就是皇帝發燒不起,大病一場,整整三天沒能理朝視政。
太祖皇帝時,一天十二個時辰,幾乎有十個撲在政事上,後任帝君沒有一個能達到他那種高度。到了武宗正德帝,皇上耽於玩樂,朝會自然成了虛設。嘉靖帝登基初始,本來是日日勤政,但是自從大禮議事件之後,君臣鬧翻,皇帝破罐子破摔,說朝堂一坐亦何益,索性連朝會也取消了,繼任的隆慶帝,也就是朱翊鈞他老爹更不消說,巴不得天天不早朝,也由此早朝制度荒廢下來。
但到了朱翊鈞這裡,他自然不願循父輩老路,碌碌無為,便對朝會制度進行改革。改革之後,除除夕、春節、皇帝壽辰這三個特殊日子之外,大朝每月逢三一次:初三、十三、廿三,在京五品以上官員,外地四品以上官員皆可奏事。小朝每月逢六一次:初六、十六、廿六,採用的是抽查制,也就是說皇帝會隨機抽查在京官員御前覲見,親自詢問工作進度事宜。至於內閣議事,則是每日一次,每次兩個時辰,如果當天超過時限,隔天可以酌情提早結束。
如此一來,原本在嘉靖、隆慶兩帝那裡已經形同虛設的朝會又以新的形式漸漸恢復,大臣們無須再像太祖皇帝時期那樣苦不堪言,也不至於一年到頭沒見著皇帝幾次。
對他們來說,最要命的是那項逢六抽查的接見,皇帝完全是心血來潮,抽到誰,誰就得去殿前問答,事先沒有任何預兆。有些人不做事或者做少了的,難免會露出馬腳,而有些人平日裡埋頭苦幹卻疏於逢迎的,也不擔心沒有得到賞識的機會,如此又在考成法之餘,起到了拾漏補缺的作用,自然是有人歡喜有人愁。
所以朱翊鈞縱然生了三天的病,也還抽空聽了一下內閣的彙報,朝野並沒有什麼異聲,倒是不少摺子呈上來,讓皇帝保重身體,勿要操勞過甚。還有一個言官說得更直白:陛下啊,您如今還沒留下子嗣,可千萬要保重,否則有個三長兩短,社稷就要亂了。看得朱翊鈞嘴角抽搐,甚為無語。
書房內,趙肅與幕僚吳維良相對而坐,煮茶長談。
「大人啊,您這一去就是半年多,可讓我好想!」趙肅不在時,吳維良鎮日往外跑,鬥茶下棋逛書市,打探到不少消息,也有一肚子的話要說。
趙肅哈哈一笑,「我可不是美嬌娘,何勞啟善如此牽腸掛肚?」
「大人說笑了,不知您此番南下,可有何收穫?」吳維良微瞇著眼,拈鬚道。
他年過三十,就迫不及待蓄起鬍鬚,而且對自己這幾縷鬍子頗為寶貝,天天梳理,務必使其柔軟飄逸,再看趙肅光溜溜的下巴,覺得完全無法理解這位趙閣老的審美。
趙肅點頭,待水煮開,親自動手,先給兩人都滿上茶杯,才道:「獲益良多。」
「此趟去廣州,除了替陛下主持萬曆號首航之外,還與閩浙粵三地商賈接觸,以四百萬兩白銀的條件,換取茶葉、瓷器、藥材這三項的五年貿易優先權。五年之後,他們若還想續權,就得競標,價高者得,屆時朝廷又加一處進項,此其一。」
「其二,我到濠鏡去,親眼見過佛郎機人的船艦,對我方應該如何裝備戰船,也有了一個大概的認知。今後大明除了發展水師,火炮的配備也要跟上,還有神機營的火繩槍等。」
「其三,此行帶回了一個羅馬教廷的傳教士,除了引薦給聖上,讓他開眼看世界之外,今後還可透過此人,要到此時與歐羅巴有關的書籍,詢問歐羅巴諸國的發展境況,以資參考。」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天下(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5 |
二手中文書 |
$ 261 |
大眾文學 |
$ 297 |
中文書 |
$ 297 |
華文 |
$ 297 |
文學作品 |
$ 297 |
Comic Book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天下(下)
繼《成化十四年》再一明史之作!
一夜歡愉後醒來,趙肅整個人都懵了!
這可是自己疼愛長大,一手教導起來的弟子,
還是坐擁天下的皇帝啊!
可看著朱翊鈞強忍脆弱,苦澀又委屈地坦露心意,
終究不忍拒絕,渾不知正應了小師兄當日之言,
昔日軟嫩可愛的小包子果然被教得青出於藍,
成了外白內黑的芝麻餡包子……
即使兩人關係改變,趙肅的心志不改,
繼重整水師,再造船艦後,還欲引進西方知識技術,
又在朱翊鈞的支持下開聞道臺、主持會試吸納門生,
不僅為繼張居正之後登上首輔之位鋪路,
也為扭轉這段歷史憾恨尋找一個契機。
他心中亦有一個天下,一個不只屬於朱翊鈞,
更是兩人矢志共同守護的天下!
本書收錄番外:〈泰昌年間〉、〈趙肅的歐洲遊記〉、
〈朝鮮使者〉,及繁體版獨家番外〈團圓飯〉。
作者簡介:
夢溪石
知名作者,所有作品常年位居晉江文學網銷售金榜,其作品以詳實考據和詼諧文風相結合,而贏得眾多讀者喜愛。其在微博上的逗趣蠢萌與筆下呈現的世界呈現鮮明對比,故有「大王喵」的外號。
章節試閱
第二十一章
趙肅有生以來第一次碰到這種完全不知該如何解決的難題。
素來冷靜自持的他連外衣也忘了披上,就這麼坐在床榻上發呆。
直到日上三竿,外頭傳來敲門聲。
「大人?大人!」趙吉連喚了數聲不見應答,連舊日的稱呼也出來了。「少爺!」
趙肅略略回過神。「什麼事?」
「您起身了嗎,小的端水來給您洗漱吧?」趙肅的作息很規律,每日必然早早起來鍛鍊,但今天居然睡到這個時辰,也難怪趙吉詫異。
「等一會兒。」趙肅起身穿好衣服,又整理了一下,轉頭瞥見床上的凌亂,又頭疼了。
「進來吧。」
趙吉推門而入,看到趙肅穿得整...
趙肅有生以來第一次碰到這種完全不知該如何解決的難題。
素來冷靜自持的他連外衣也忘了披上,就這麼坐在床榻上發呆。
直到日上三竿,外頭傳來敲門聲。
「大人?大人!」趙吉連喚了數聲不見應答,連舊日的稱呼也出來了。「少爺!」
趙肅略略回過神。「什麼事?」
「您起身了嗎,小的端水來給您洗漱吧?」趙肅的作息很規律,每日必然早早起來鍛鍊,但今天居然睡到這個時辰,也難怪趙吉詫異。
「等一會兒。」趙肅起身穿好衣服,又整理了一下,轉頭瞥見床上的凌亂,又頭疼了。
「進來吧。」
趙吉推門而入,看到趙肅穿得整...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