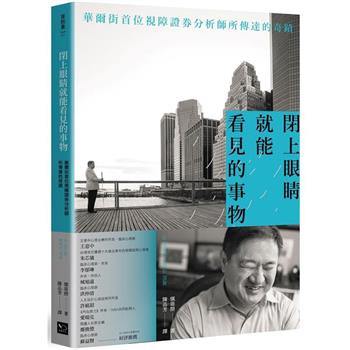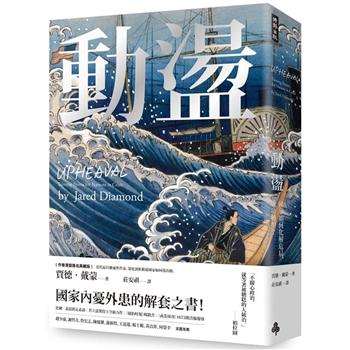第一章
雷打驚蟄前,四十九日不見天。
連綿陰雨打溼了庭前的杜鵑,但雨水帶不走滿地殘紅,它們被人細心地拾起、清洗,放在一個小竹籃裡。
一隻骨節分明的手探入竹籃拈起了幾片花瓣,白皙的手指在一片嫣紅中流連,撣去些許水滴。然而這些花瓣並非用來泡茶,那隻手輕輕一拋,便將它們丟入身前的烏金盤龍爐。
這是一個丹爐,爐子並不大,只半公尺高,耳小肚圓,像隻生氣的河豚。就連盤繞爐身的那條五爪金龍,都胖得憨態可掬。
但這爐子裡燃燒著的東西,可一點也不可愛。
花瓣、硫磺、銀塊等等,甚至還有一截散發著古怪香氣的不知是什麼品種的樹枝,被胡亂地丟在裡頭,可見丹爐的主人並不諳正確的煉丹之道。
不一會兒,泛著青藍的火苗就開始顫動,熱氣在沸騰,龍口裡飄出一股不祥的味道。
庭院裡,淅淅瀝瀝的雨聲中藏著幾句嘀咕。
「快看,又要炸了……」
「這已經是第幾次了?」
「第九百九十八次?」
「最近這天兒不好,別把山震塌了,西邊不是還有個墳堆嗎?到時候棺材都給震出來,可嚇人……」
「你一個妖怪還怕死屍?」
「對了,上次你吃的蘑菇就是人家墳頭上採的。」
「靠!」
「……」
「炸了炸了炸了!」
「噗!」卻是一聲悶響。
那人伸手摁住了爐蓋,指間微光湧動,直接將所有波動都扼殺在爐子裡面。可那爐身上的小金龍卻似活過來一般,甩著尾巴探起頭來,極其嫌棄地吐出一堆黑色廢渣,吊著眼睛,說:「這什麼玩意兒,老子要吐了。」
「你已經吐了。」那人隨手將黑色廢渣揮進垃圾桶,語氣不鹹不淡。他本是席地而坐,沒穿鞋子,裡衣外頭罩著件黑色紗衣,倒頗有幾分仙風道骨的意思。
如今煙散了,他取過旁邊的丹道古籍蹙眉看了兩眼,又興致缺缺地丟開,懶散地側臥在地,便似現了原形的妖精,沒了那仙氣,墜落凡間化作哪個高門裡醉生夢死的風流貴少。那雙天生自帶眼線的勾人雙眸望著庭中的風雨,裡頭寫滿了無趣。
小金龍安靜了一會兒,終於忍不住說道:「主人給你設下的時限早到了,這結界又困不住你。你如果真那麼無聊,幹嘛不下山去看看?我聽金玉說,現在的世界跟以前可大不一樣了,新鮮的事情多著呢,手機電腦、飛機遊艇,還有外賣,有趣又好玩,你說我們這山上連網路都沒有,你留在這裡幹什麼?」
那人沒回答,手指有一下沒一下地輕敲地板,也不知在想些什麼。
風雨聲忽然大了,引得滿院杜鵑哀鳴。
「你不知道,大家都不敢告訴你,你離開以後,四九城(四九城:皇城四門,內城九門,引申指北京。)裡的那些妖都說你瘋了,回不去了。堂堂南區老大,屠夫司年,這麼被人編排你都不管?我以前可沒見你這麼心善。」
聞言,司年終於微微瞇起眼,最後卻也只有一聲嗤笑。
小金龍知道這人最聽不得別人勸,但又不得不說,「這兒雖然有結界,可道觀沒了主人,能撐住這百餘年已經快到極限了,結界遲早會破。你不下山,他們都不下山,都跟間破道觀死磕,圖什麼?」
司年抬起眼簾,反問:「你又圖什麼?」
「我圖自由啊。」小金龍答得爽快:「我又沒長腳,你不帶我出去,我不得永遠都待在這兒。」
小金龍其實看不太明白,這人剛被送進道觀的時候,一身殺氣重得很,成天想出去。可現在能出去了,他又不走了。
「行了,你想出去,就讓金玉帶你去。」司年揉著肩坐起來,似是不願再繼續這個話題。目光向庭中一掃,陡然冷冽。
「你們嘀嘀咕咕的,當我沒聽見?」
話音落下,只見風雨的庭中立刻滾出兩個身影來。高個的一頭板寸,五官周正,笑容憨直。矮個的長著一對小虎牙,面容白淨,眼神靈動。
可他倆還沒說話,就被一聲「閉嘴」堵住了口。
司年站起來,紗衣隨著他的走動飄搖,似天邊那抹即將要落下來的黑色的雲。黑雲飄進了裡屋,只留下餘音渺渺。
「等金玉回來了,讓他來見我。」
虎牙和寸頭對視一眼,又齊齊湊向丹爐,作賊似的壓低了聲音問:「你問出什麼沒有?老大到底打算什麼時候下山啊?」
小金龍揚起頭,「你們不是都聽見了嗎?我問出個屁。」
「你整天跟他在一塊兒你不知道嗎?」
「你們整天聽牆角你們不知道嗎?」
雙方皆是無話可說,於是兩妖一爐在廊下排排坐,對著春雨,坐困愁城。
半晌,虎牙支著下巴說:「你們說,其他的妖怪們,在大城市裡都是怎麼生活的呢?聽說現在大城市生活壓力很大哦,要讀書找工作還要還房貸,幾十年都不一定買得起一間廁所,更別說討老婆,這也太可怕了吧。」
小金龍吊著眼睛,「人類都能活,你不能活?」
虎牙誇張地瞪大了眼睛,「我只是一個長在山溝溝裡的柔弱的小妖怪,人類多可怕啊!」
旁邊的寸頭只有憨笑。
末了,小金龍道:「反正這山一定得下,主人曾經說過,從紅塵中來的,必定得回到紅塵中去。」
另一邊,回了裡屋的司年沒有休息。窗半開著,能看到遠山上的煙雨,他在竹榻上自己跟自己下棋玩了一會兒,隱約聽見後山又有異響,輕「嘖」一聲,便撐傘出了門。
他是從後門出去的,這麼多年他一直住在道觀的客舍,從這裡出去,恰好是一條通往山頂的石階。
綠竹小傘盛放在竹林裡,他拾級而上,聽雨滴穿林打葉,看滿目青蔥翠綠,心裡本該更顯幽靜,可風中總隱約傳來人世的喧囂聲。
他的腳步加快,前方是個茅草亭,亭名無垢。
站在亭中,風裡夾雜的聲音更清晰了。有行人急匆匆避雨的腳步聲,有小孩兒的哭鬧聲,有年輕情侶不耐煩的爭吵聲,甚至還有山下人家炒菜時鍋鏟觸碰鐵鍋的聲音。
一切的聲音,彷彿都在催促他:你該下山了。
司年抬頭望,鶴山上的結界確實越來越薄。過不了多久,不止這些聲音會透過來,恐怕整個鶴山都會被埋在人間的煙火裡。
他不由回望,距離後門不遠處的山泉旁矗立著一塊巨石,巨石上斧鑿兩個大字——照野。
照野是道觀的名字。
鶴山,照野觀,被巨大結界隔絕於世的地方,對於生活在鶴山的妖怪來說,是牢籠,也是樂園。
結界的封閉避免了世間一切紛擾,可作為一個連手機都沒有用過的老古董,司年也說不清楚是他們拋棄了時代,還是時代拋棄了他們。
小金龍說,四九城裡的妖怪都以為他瘋了。可照野觀,不就是一個瘋妖院?被關在這裡的妖怪,哪一個不是末路狂徒。
新時代來臨,他們自然也該走上新的路。
司年也不是不想下山,只是……
恰在此時,林中草葉輕顫,走出一個人來。這人穿著一身西裝,頭上還塗著髮膠,梳著一個追趕在潮流前線的髮型,未語先笑,不像個妖怪,像個精明商人。
「果然在這裡。」金玉撣了撣衣服上的水,跨入亭中,跟司年並肩站著,順著他的視線看出去,說:「剛才走過來的時候我看到了,元晝他們又在後山打架,崩了一大塊山石。現在正在緊張收拾殘局,就怕你過去呢。」
司年不予置評。
金玉笑笑,又說:「我這次去北京,專程拜訪了其他幾區。西區是個新來的,東區和北區還是原先那兩位,大家都是重情義、念舊情的,託我問一句,您打算什麼時候回去。」
司年挑眉,「原話?」
「原話……」金玉摸了摸鼻子,「四爺問您死了沒有?沒死好滾回去上班了。現在當不成地主不能圈地也不能收保護費更不能打打殺殺了,但是工資很高,五險一金,還有團建。」
這都他媽的什麼玩意兒?
司年聽得直想翻白眼,但好歹克制住了。揉揉眉心,他問:「那件事你打聽到多少?」
金玉搖頭,「線索太少了,人海茫茫要上哪裡去找?不過,既然卦象上說緣分就在這個月,那不需要刻意找,自然而然就會遇到的,不用著急。」
「你看我像著急的樣子嗎?」
挺像的。
金玉惜命,面對赫赫有名的「屠夫」,當然不會把心裡的話說出來。而且作為一個合格的情報販子,他絕對是專業的。
「如果需要,我可以繼續找,但距離卦象上顯示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微笑道。
司年其實真的不急,如果可以的話,他寧願一輩子都找不到卦象上說的那個人,因為那是個——姻緣卦。
半個月前,就在他「刑滿釋放」的那一天,他得到了將他關押在這裡的人,也就是道觀主人遺留下來的一份禮物,即他離開前為司年算的一卦。
卦象顯示,他將在驚蟄過後的一個月內,遇見自己的真命天子。
真命什麼?真什麼天子?命什麼?
這是個男人吧?
我也是個男的吧?
這是做什麼?奉天道之命行斷袖之事嗎?
無淮子那個萬惡的假道士,生怕他看不清楚,竟然還把「真命天子」這四個字給他用朱砂圈了出來,附贈一句「百年好合」。這讓司年還怎麼好好下山?就算要下山,他也得先把這該死的道觀連山一起給炸了。
他讓金玉去查卦象上的那個人,自然也是為了躲開他。
姻緣算什麼?
姻緣如狗屁。
其實司年並非對姻緣有天生的排斥,只是從沒有對誰動過心罷了。讓他意外的還是卦象上那人的身分,他不僅僅是個男人,還是一個純正的人類。
無淮子寫下了他的生辰八字,他今年正好三十歲。
司年問過金玉,如今的男子三十歲時都在做什麼?
金玉說:在拚二胎。
司年越發煩躁,覺得還不如留在山上煉丹的好。他怕自己一個沒忍住,還沒看上對方,就想在他墳頭上種草。
新時代了,確實不該打打殺殺的。
「你喜歡男人嗎?」司年忽然看向金玉。
「不喜歡,但我尊重一切性取向。」金玉掛上職業的微笑,然而被司年瞇起眼來那麼一掃,心裡還是毛毛的。
你不要這麼看我了,我真的不搞基。
司年不再言語。此時雨小了許多,他乾脆把傘留在了亭中,施展寸步一下來到了後山,正巧趕上那幾個打架熱衷分子偷摸著逃離現場。
雙方於一處灌木後狹路相逢,司年嘴角掛著淡笑:「打架嗎?算我一個。」
照野觀的瘋妖們,撲通跪了一地。想當年大家也都是橫行霸道的主,誰曾想來到鶴山以後會碰上這屠夫,只能感嘆一句流年不利,跪求一聲「打妖別打臉」。
司年掃視一周,忽然發現他們這山頭,一個女妖都沒有。
這難道真的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麼?
思及此,司年的臉色不禁又臭了一分,看著越發陰晴不定。可就在眾妖以為自己又要大難臨頭瑟瑟發抖時,他卻又轉身走了。
跪在最前面的妖名叫元晝,看起來瘦如麻杆,卻是這山頭上打架最厲害的妖,也最崇拜司年。他站起來就要追上去,可司年走得太快,他連片衣角都沒碰到。於是他又折回來,疑惑地看向金玉,「老大這是怎麼了?」
金玉聳聳肩,「他最近見不得男的。」
元晝:「吭?」
「反正你們最近都別往他面前湊。」
「為啥?老大思春了嗎?」
「唔……」金玉思考片刻,答:「現在還沒有。」
金玉不敢說實話,怕被司年聽見,墳頭種草。可所謂言者無意聽者有心,這模稜兩可的答案落在元晝耳中,那就跟真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作為一個合格的崇拜者,元晝覺得老大寂寞了這麼多年,可能真的是想女妖了,這也是妖之常情嘛。他可以謀劃著下山給他搶一個來,反正結界快破了。
另一邊的虎牙與寸頭二妖組,則在謀劃著火燒照野觀。他們覺得,反正照野觀遲早得塌,早一天塌,不就能早一天下山麼?
而且放火玩多開心啊,這在以往是過年才能幹的事情呢。反正要是最後出了岔子,就推到小金龍頭上去,丹爐最容易走水了。
可司年一心想著卦上的男人,絲毫沒有預料到即將到來的爛攤子。
金玉很快又離開了,他是鶴山這百餘年來唯一一個能自由出入的妖,託他的福,鶴山雖與世隔絕,但卻不至於對外面的事情一無所知。臨走前他送了司年一支手機,作為即將下山的賀禮。
金玉辦事周到,送手機還配備了詳細的使用說明,並且提前下載好了各種常用APP,唯一的缺點是——山上沒網路。
結界還沒有破,照野觀裡收不到人間的網路,但山頂卻有一絲微弱的訊號。司年得了這麼個新鮮玩意兒,一時把卦上的男人都拋到了腦後,乾脆跑去山頂的清涼亭待著,任誰都打擾不到他。
山頂果然能透過越來越薄的結界收到一絲訊號,於是一個小時後,司年熟練的開始上網衝浪。
其實對於司年來說,手機這東西並沒有讓人多驚奇。妖界那麼多法器、寶器,極盡精巧之能事,他也不是沒見過。但手機的功能無疑強大、全面,且毫無使用門檻,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瞧著倒新鮮。
司年仔細把玩了一會兒,便翻到了使用手冊的最後一頁,那上面記錄了一個電話號碼。它被金玉特地寫在這裡,可這電話號碼的主人,卻讓司年一時想不起來是誰。
段老先生?是哪個段老先生?
對於從前的許多人和事,司年早拋到腦後了。不重要的,就沒必要記著;即便是重要的,看不順眼也就不記了,這是他一貫的作風。段這個姓瞧著很陌生,他想了許久才想起來,當年那個被他救過的小子,好像是姓段。
司年很少救人,善心大發也就那麼一次,救過便罷,也不稀罕得別人的感謝。但那人硬是要報恩,哪怕知道了他在外頭的名聲都不曾退卻。司年離開四九城的那一天,他作為一個人類,還曾來送行。
姓段的……到現在還記得他的,只能是他了。只是算算時間,他應當已經不在人世,所以這「段老先生」,是他的後人?
想起舊人,回憶的匣子便如潘朵拉的魔盒,被猝不及防地打開了。司年抬頭望著星辰寥落的夜空,忽然便想到了自己曾走過的那些路。
以及自己在這裡空耗的這許多年。
他坐在這裡,看著天上的星星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淡。金玉說這是因為空氣汙染,星星不是不見了,而是被遮住了,但這對司年來說都是一個意思。
我看不見星星,它就不存在,管它是真沒了還是被遮了。
總而言之,沒甚意思。
司年收起手機,沒了再把玩的興致,卻也不想回道觀,便在這清涼亭裡坐了一晚。
誰又知道,他只是離開了一個晚上,道觀裡就翻了天了。
事情是這樣的:
鶴山的結界還沒破,元晝一眾暫時不能下山,抓不來女妖怎麼辦?他們可以自己變。一群瘋子聚集在一起的結果就是——沒有什麼世俗的規矩能夠束縛住他們的腦洞,每個妖都可著自己喜歡的樣式來變,十個妖裡,有九個走的是性感妖嬈路線。
元晝為了自己崇拜的偶像,有著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但妖嬈的麻杆依舊是根麻杆,嚇到了半夜起床的兩個縱火犯。
縱火犯手裡提著兩桶油,其中一個手中還點著根蠟燭。他們見到妖嬈麻杆,還以為看到了後山墳頭裡爬出來的女鬼,手一抖,火星就掉進了油桶。
彼時,他們正站在司年的丹房門口,那扇門裡,裝了許多煉丹用的硝石。
照野觀的後院客舍,就這麼被炸上了天。
最慘不過烏金盤龍爐,只聽一聲巨響,爐蓋像鐵餅被炸飛了百公尺遠。
司年在山頂聽見響動時,望著道觀的方向舉目遠眺,只見剎那間火光沖天,其中伴隨著群妖亂吼,熱鬧非凡。
「啊啊啊啊啊啊鬼啊啊啊啊啊!」
「操操操操操我的蓋兒!」
「蓋兒!」
「老大你在裡面嗎?快救老大!」
「老大我來救你了!」
「先救我的蓋兒!我的蓋兒!」
「……」
司年額頭上青筋暴起,一個閃身出現在道觀裡,抬腳便把叫得最大聲的元晝踹進了火堆。吵鬧聲戛然而止,所有妖的動作彷彿被按下了暫停鍵,傻呆呆地看著他。
「你們要進去陪他嗎?」司年勾起嘴角。
「不不不不不。」眾妖瘋狂搖頭,齊齊後退。
司年冷笑一聲,五指微張,黑色的法力瞬間噴薄而出,將客舍與道觀主體的連接牆面全部震斷,隔絕了火勢。但他並沒有把火徹底撲滅,反而看著它繼續燃燒。
大家看不清他的臉,只見一對綴著流蘇的耳環在火光中搖曳,既美得驚心動魄,又叫人害怕。
大家都不敢出聲,連小金龍都不急著找他的蓋兒了。一直到客舍最後一面牆倒塌,司年才大發慈悲地將元晝從火裡提溜出來,扔進了觀中的池塘。
撲通一聲,水花四濺。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城南妖物生(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8 |
二手中文書 |
$ 297 |
中文書 |
$ 297 |
文學作品 |
$ 297 |
Comic Book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城南妖物生(上)
堂堂南區大妖,身負「屠夫」的凶殘名聲,
司年不敢置信,在被放逐兩個甲子後,
迎接自己的竟是一卦姻緣卦──
他將在一個月內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對象還是個三十歲的男性純人類?!
這是做什麼?奉天道之命行斷袖之事嗎?
既然如此,先避開那個三十歲的報恩代表段家小子,
再抹去頭號嫌疑人「章先生」與他相遇的記憶,
便應該沒事了……吧?
面對爺爺「恩人是妖怪」、「要報恩」的怪誕要求,
身為盛光實業的霸道段總,段章面不改色表示:
不管是人是妖,該報的恩我一定好好報。
不過,這個神祕漂亮的青年就是百年前段家的恩人,
四九城傳說裡令人聞風喪膽的屠夫司年?
確實心高氣傲、脾氣暴躁又野性反骨。
可那恣意的美麗看著刺人,卻也讓人想據為己有……
商品特色
《妖怪書齋》系列~~南區大妖歸來!
凶殘鳥妖╳人類霸總?!
屠夫司年冷心冷情,從不會為誰停留,為誰心憂,
可這男人竟挾報恩之名想將他拽進姻緣的墓裡?!
作者簡介:
弄清風,一個資深懶宅,愛好編故事,夢想是暴富,但火鍋才是人生的奧義。雜食動物,腦洞大如海,梗多嚼不爛,做夢老是夢到恐怖片,但拒絕寫恐怖故事。熱愛甜文爽文以及一切可愛生物,顏控晚期,拒絕治療,希望《銀魂》永不完結!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雷打驚蟄前,四十九日不見天。
連綿陰雨打溼了庭前的杜鵑,但雨水帶不走滿地殘紅,它們被人細心地拾起、清洗,放在一個小竹籃裡。
一隻骨節分明的手探入竹籃拈起了幾片花瓣,白皙的手指在一片嫣紅中流連,撣去些許水滴。然而這些花瓣並非用來泡茶,那隻手輕輕一拋,便將它們丟入身前的烏金盤龍爐。
這是一個丹爐,爐子並不大,只半公尺高,耳小肚圓,像隻生氣的河豚。就連盤繞爐身的那條五爪金龍,都胖得憨態可掬。
但這爐子裡燃燒著的東西,可一點也不可愛。
花瓣、硫磺、銀塊等等,甚至還有一截散發著古怪香氣的不知是什麼...
雷打驚蟄前,四十九日不見天。
連綿陰雨打溼了庭前的杜鵑,但雨水帶不走滿地殘紅,它們被人細心地拾起、清洗,放在一個小竹籃裡。
一隻骨節分明的手探入竹籃拈起了幾片花瓣,白皙的手指在一片嫣紅中流連,撣去些許水滴。然而這些花瓣並非用來泡茶,那隻手輕輕一拋,便將它們丟入身前的烏金盤龍爐。
這是一個丹爐,爐子並不大,只半公尺高,耳小肚圓,像隻生氣的河豚。就連盤繞爐身的那條五爪金龍,都胖得憨態可掬。
但這爐子裡燃燒著的東西,可一點也不可愛。
花瓣、硫磺、銀塊等等,甚至還有一截散發著古怪香氣的不知是什麼...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