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徐望從沒想過這輩子還能遇見吳笙,哪怕是在夢裡。
但是他遇見了。
茫茫雪原,皚皚林海,他只穿一條短褲漫無目的地前行,穿過一棵又一棵樹,越過一個又一個小雪坡,哆哆嗦嗦抱著胳膊,沒半點平日的健談與帥氣,以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狀態,遇見了他高中時的心頭白月光。
八成是為了配合他的夢,吳笙也穿著一套同周遭環境極不和諧的睡衣,亞麻條紋的長袖,在禦寒方面比他的赤膊強點,但也就強那麼一點點,鼻頭同樣被凍得泛紅,但人家就有定力站在那兒一動不動,連眉頭都不皺一下。除了五官脫去了當年的稚氣,眉宇間多了幾分成熟和沉穩,剩下的都和徐望記憶中那個代表年級升旗,結果升到一半旗線纏繞卡住了,於是在全校中二少年不懷好意的哄笑中,敏捷爬上旗杆親自解開旗線,然後像瑪利歐一樣順杆滑下來,繼續若無其事升旗並最終傲視全場的boy一樣。
這傢伙最讓人難以忘懷的就是從高一到高三始終不可撼動的年級第一,以及從高一到高三越來越令人髮指的……裝逼。
偏偏徐望就喜歡他的裝逼,喜歡到私底下曾好幾次偷偷模仿他爬旗杆,結果……打住,這麼難得的重逢時刻不要回憶那麼不開心的事。
「吳笙。」十年沒喊過的名字,徐望以為多少會有生疏,可是沒有,這兩個字就像在心中百轉千迴了無數次,極流暢地出了口,霎時,就將他帶回了昔日時光,心底泛起輕輕淺淺的溫熱。
吳笙眼中的驚訝更甚——片刻前於這冰天雪地裡迎頭遇見,他就已經面露驚訝,這會兒被喊了大名,那驚訝乾脆從眼底蔓延到了整張臉上。連穿著條紋睡衣漫步在林海雪原都沒皺一下眉的人,對著一下子就喊出了自己名字的昔日同窗,竟一時組織不出完整語句:「你……」
高中三年,徐望都沒見過「話說不利索」的吳笙,要是回到以前,他能拿這事兒笑話他一學期。但現在,他實在騰不出空,滿心滿臉都塞滿了期待,眼睛一下也捨不得眨地盯著對方,恨不能「誘供」:「對,我……」
「高中……」
「嗯!」
「我下鋪的……」
「嗯嗯!」
吳笙應該是想起來了。詫異慢慢淡去,眉頭漸漸舒展,眼中徐徐浮起的笑意赫然還是那個傲視全年級的男生,讓人一邊氣得牙癢癢,一邊又迷得心癢癢。
徐望肆無忌憚地望著他,嘴角咧著,心花開著。
終於,對方率先伸出了友誼之手:「好久不見,張望。」
徐望:「……」在自己的夢裡打人犯法不?
徐望這邊氣得肝疼,捂著胸口都不能緩解扎心之痛,吳笙那邊倒更開心起來,儘管他掩飾得很好,但徐望是誰啊,躺下鋪隔著床板YY了對方整個高二高三的少年癡漢,吳笙那點微表情他再熟悉不過了。
這傢伙絕對是故意的,高中時候他就以擠對自己為樂。當然自己也不是軟柿子,你給我一刀,我必還你一劍,雖然成績反撲無望,但嘴炮也從來沒落下風。
只是沒想到,都到自己造的夢裡了,大腦皮層虛構出的這個吳笙愣是沒在性格上進行半點「美顏」,哪怕多少溫柔一點呢。
行了,徐望啪啪拍兩下自己的臉,貪心不足蛇吞象,難得做個美夢,難得這個十年後的吳笙還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難得天寒地凍衣衫單薄,來個熱烈擁抱順理成章——
「好久不見!」無視掉對方伸出的手,徐望撲過去就是一個熊抱,彷彿要將過往留下的遺憾都在這一撲裡消解。
吳笙猝不及防,在巨大的衝擊力下後退半步,然後站穩,僵住了。
徐望才不管對方適不適應,一八一的個頭就小鳥依人地在人家胸膛蹭,一邊蹭還一邊感嘆:「這夢……睡死過去都值了……」
天上開始飄雪。很細的雪,一粒粒落到徐望的鼻尖,落到他臉頰同吳笙條紋睡衣領口相摩擦的地方。剛沾上,又咻地融化,不忍心多看這美麗畫面一眼。
天地良心,徐望最開始真的覺得抱一下就已經心滿意足了。但人就是這樣,一旦嘗到甜頭,就總想吃更多的蜜,要不怎麼都是一步步滑向罪惡深淵呢,從來沒聽說誰是一猛子扎到罪惡河裡。
「我喜歡你,我從高二開始就喜歡你,一直到現在不管我心裡開發了多少建案,只有你,只有你吳笙,拿著我心裡唯一一塊宅基地!」
無數次午夜憶青春,無數次幻想如果當年表白會怎樣,無數次用「幸好沒說不然害人害己」來安慰自己,但只有徐望自己清楚,這是壓在他心底最深處的遺憾。
如今終於得償所願,哪怕只是南柯一夢,他也希望過把癮再醒。
一口氣說完,也不管對方接收消化多少,徐望抬起頭朝著吳笙的嘴唇就吻了上去。
吳笙沒躲,當然也可能是被先前那段清新脫俗的告白給震住了,還處於「你是誰,你說啥,你想幹嘛」的懵逼中。
徐望趁火打劫,吻了個徹底,吻了個盡興,真心死而無憾了。
「吼嗷——」背後猛然襲來凜冽冷風,伴隨著野獸吼叫,徐望渾身汗毛顫慄,再顧不上親嘴,「刷」一回頭!
黑熊那一掌「刷」得比他更快,結結實實呼上他肩胛骨。
死而無憾只是個比喻,不需要這麼認真吧!!
徐望活了二十九年,磕了碰了常有,卻在這一爪子裡才明白什麼是真的疼。
大腦當機,身體木然,整個人隨著熊掌力道往前倒。吳笙想擎,沒擎住,被他一併撲倒。跌入厚厚雪地的瞬間,徐望再度聽見了黑熊的咆哮,這一次比上次更近,更凶狠。
他要死了,而且很可能還會把吳笙一起連累死。
童話故事的開頭,恐怖電影的結尾,這夢做的,太失敗了。
吐槽只是一瞬間的念頭,「耳中音」卻是一字一句圓潤清晰,就像有個小人兒站在他耳道裡說話,甚至語調還帶了點詭異的調皮——
【鴞:寶貝兒~提前放假,送你回家。】
徐望眼前忽然一白,就像無數探照燈對著這邊打強光。他本能地閉上眼睛,只一霎,身下的吳笙消失,他結結實實摔趴到了地上,「吧唧」一聲,清脆悅耳。
雪停了,天暗了,吳笙沒了,順便還帶走了殺人熊。
徐望懵裡懵懂地爬起來,四下張望,哪裡還有茫茫白雪,廣袤山林?這就是他租的房子樓下,黑漆漆的凌晨四點,硬邦邦的柏油地,林立的商鋪全都緊閉,哪怕早點鋪,也剛開始有人忙碌、準備。
「嘟嘟——」急促的汽車鳴笛聲讓徐望回過神,他這才發現自己正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央,連忙快走幾步上了步行街道。熟悉的早點鋪老闆貓著腰從半開的捲簾門裡出來倒垃圾,看見他,一臉驚訝,操著一口陝普打招呼:「今兒個咋這麼……」
老闆原本想說的是咋這麼早,不想話說一半,才看清這位「熟客」的打扮——赤膊上身,一條黑色的寬鬆短褲。平心而論,熟客平日裡穿西裝打領帶看著偏瘦,這一打赤膊,倒是有點線條的,看著賞心悅目,但你不能仗著自己盤兒亮條兒順就大深秋的光膀子浪吧。
然而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老闆只能硬拗:「咋這麼……涼快。」
徐望低頭看看自己,又抬頭看看老闆,一時分不清夢境與現實。如果是夢,還帶這樣連續劇的?如果是現實,他好端端在自己床上睡著,睜眼睛就站大街上了,合著他活了二十九年突發夢遊?
「嘶——」突來的疼痛讓徐望倒吸口冷氣,下意識抬手摸後肩,一片溼漉漉。
徐望怔住,又疼,又慌,以至於遲遲不敢將手拿回來看。他現在真的寧願自己是夢遊了。
伸手摸自己後背這個姿勢實在有點扭曲,早點鋪老闆看不過去了,關切地問:「咋咧?」
「沒事。」徐望勉強扯出個微笑,搪塞兩句後飛快奔進樓裡。
幸而天還未大亮,跑進樓道裡的徐望後怕地想,否則絕對能把人嚇著。
早點鋪老闆逃過一劫,於是受驚嚇的只有當事人自己——明亮的聲控燈底下,徐望攤開手掌,一片猩紅。
只著內褲的他根本進不去家門,只得在樓道裡苦等,終於在天放亮時,等到了下樓遛彎的李大媽。
李大媽眼神不好,心腸倒熱,一聽他把鑰匙忘家裡了,也沒多琢磨為啥這位平日西裝革履的小夥子今天穿得這麼「休閒」,二話不說就把手機借給了他。
徐望在滿樓道密密麻麻的小廣告裡尋了一個排版設計沒那麼花哨、看著就有撲面的憨厚樸實感的「派出所備案開鎖王」,然後謝過李大媽並婉言謝絕了其「上我家坐坐歇一會兒」的邀請,維持著後背緊貼防盜門的姿勢,目送其下樓。
後背的傷口已經被血凝住了,即便沾到黑色防盜門上少許,也看不出來。
開鎖王是個非常年輕的小夥,來得很慢,抵達的時候李大媽都遛彎回來了。饒是如此,小夥還哈欠連連,睡眼惺忪,一臉「提早上工」的辛苦。不過等看見徐望清涼的造型,那目光就瞬間警惕起來了。
徐望心虛,染了血的那隻手其實已經握拳了,卻還不放心,下意識往身後藏。
小夥眼睛裡精光一閃,剛要開口,徐望比他還快,一聲嚎叫石破天驚:「李大媽——」
封閉的樓道差點被這一嗓子震得掉土渣,開鎖王耳朵還嗡嗡的呢,就見一老太太噠噠噠從樓上小碎步下來,一邊奔赴「現場」還一邊往胳膊上戴紅袖箍。
僅剩的那點懷疑也讓這不容置疑的正氣給鎮住了,在李大娘再三說明徐望的確是住在這裡的有為青年後,開鎖王拿出根錫條捅進鎖眼,喀噠,鎖開,速度之快讓徐望懷疑自己是不是壓根沒鎖門。
飛快進屋,利索關門,火速套T恤,再從容開門、付錢。
終於踏踏實實坐回客廳沙發,已日上三竿。徐望先打電話跟公司請假,然後才拿了手機鑰匙錢包醫保卡去醫院看傷,直到醫生問他怎麼受傷的,他還處在蒙圈裡。
如何回答大夫的他忘了,反正肯定不是「一有為青年在首都三環裡被狗熊一掌拍肩say hi」這麼挑釁醫生智商的版本。
從醫院回來,已是正午時分。再度坐到出租屋的沙發裡,徐望才終於能稍稍轉轉腦子,理理發生的這一切。
他下班回家,到點睡覺,夜裡做了個夢,夢見了林海雪原,夢見了高中初戀——單方面的,完成了遲來十年的表白,達成了強吻成就,然後被一黑熊撲倒,肩膀挨了一熊掌,夢醒,他在十字街頭。
如果沒有肩膀上的傷,還勉強可以用「夢遊」來解釋他蘇醒時的所在地。可如果發生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吳笙哪裡去了?熊哪裡去了?還有,他雖然是第一次被熊拍,但常識還是有的,一熊掌呼過來只是皮肉傷,連骨折骨裂都沒有?
徐望在客廳沙發裡窩了一下午,一刻不間斷地想著昨夜那些匪夷所思的遭遇,可直到夜幕降臨,沒開燈的客廳陷入寂靜的黑暗,仍是沒理出個所以然來。
算了,不想了。
徐望甩甩頭,騰地站起來,結果動作太劇烈,牽動了肩膀傷口。他連忙再不敢動,緩了半晌,才小心翼翼去浴室,洗臉刷牙,讓整個人在冷水的洗漱裡一掃塵霾,清清爽爽。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和諧社會,共建小康,要是夢遊,他就治病,要有壞人,他就報警,富強民主愛國敬業誰怕誰!
有了決斷的徐望不再七上八下,脫鞋上床,蒙頭就睡,明天又是嶄新的一天……
八點。九點。十點。十一點。十一點半……
好吧,他睡不著。
肩膀還疼著呢怪事還無解呢這要能睡著他心得有多大!
打開手機手電筒,環顧臥室一圈,沒異樣;照照自己身上,羽絨服,保暖褲,運動鞋,沒問題;摸摸褲袋,鑰匙、錢包都在,完美。
不管是不是夢遊,他都不想再經歷一次凍成狗完後還要借樓上李大媽手機找開鎖王。
【咕咕——】
又是彷彿在耳朵裡響起的聲音!徐望身體一僵,模糊的記憶碎片回籠——昨夜在墜入雪原遇見吳笙的前一刻,他也聽見了這個聲音!
彼時的他以為是夢中幻聽,可現在他醒著,比上班時打起的精神都多,前所未有的清明。那是某種鳥類的叫聲,徐望形容不出來,只覺得這聲音與黑夜十分契合,乘著夜風,送入心懷恐懼者的耳膜,殺傷力簡直加成。
回籠的記憶碎片裡不僅有叫聲。徐望一股腦爬起來,也不管牽不牽動傷口了,疼得齜牙咧嘴也要第一時間下床往外跑。
一口氣跑到客廳,徐望聽見了第二聲。
【咕咕——】
隨後,臥室裡傳出窸窸窣窣的異響。
徐望站在距離臥室門兩公尺開外的地方,伸脖子往裡面看,只見床頭還是靠著牆的床頭,但床身已經成了一個籠罩著光暈的長方形流沙坑,哪裡還有床墊床單的身影,有的只是源源不斷往坑裡陷的流沙。
幸虧那聲鳥叫讓他把昨夜模糊的片段都想起來了,否則現在他又要進到那個鬼地方了。雖然能遇見吳笙是好事,但那畢竟都是假的,吳笙早八百年前就跟著爹媽出國定居了,可挨一熊掌的疼絕對是真真切切的……
哎?哎??
徐望正為逃過一劫慶幸呢,忽然覺得有一股力量拉扯著他往臥室裡去!眨眼間他就已經被拽到臥室門口!
徐望拿出吃奶力氣扒著門框死不撒手,可那力量竟越來越強,到最後他整個人被拉得打橫騰空起來,跟狂風裡的人形旗似的!
眼看再僵持下去自己就要被扯斷成兩截,徐望不再頑抗,絕望鬆手。
被吸入流沙坑的時候,徐望想了兩件事:一,這事兒太他媽魔幻了,必須報警,就算被當成神經病也要報警!二,如果吳笙還在,找個沒熊的地方再親。
上一次是熟睡中陷入那詭異之地的,徐望從頭到尾如墜五里霧,直到見了吳笙,精神一振,腦筋才慢慢清楚起來。所以在那之前他是怎麼來這裡的,又在這皚皚雪原裡茫然懵懂地摸索了多久,記憶全然模糊。
但這一次他醒著,清晰體驗到了那種從高空墜落的失重感,就像坐在自由落體裡,彷彿永無止境的極速下墜,讓人產生出一種整個身體都被打碎的窒息。
不知過了多久,臉頰忽然傳來極涼的觸感,先是冰,然後慢慢有些溼潤。
徐望呆愣半天,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落地,並且是臉朝下,一頭栽進雪裡。
他大鬆一口氣,懸著的心肝脾肺腎終於歸位。衝過終點的姿勢好看與否已經不重要了,至少,他還活著,並再次感受到了讓人心安的地球引力。
雪和臉皮都夠厚,爬起來撲稜撲稜,又是一個體面青年。徐望環顧四周,又極目眺望,雪原,林海,遼闊蒼穹,浩渺遠山,錯不了,就是昨天那地兒。
這是「夢境」?就算徐望願意一意孤行地堅信,他那十根通紅的手指頭都不能答應——剛剛扒門框扒得太用力,指肚現在還一跳一跳地疼。
冰天雪地裡站著不動是最冷的,沒一會兒,徐望的腳就開始發木。他連忙走起來,辨不明方向,也不知要去往何方,只茫然前行,努力維持著身體熱度。
不知過了多久,一聲短促清脆的「叮——」毫無預警響起。徐望被嚇得心裡一緊。
那聲音乍聽很像一些餐廳廚房出菜窗口上擺著的按鈴,菜一出來,廚房就要「叮」一下提醒夥計。但很快,他就回味出不對,和那些彷彿由他耳膜深處生出的詭異聲音不同,剛剛那聲「叮」好像來自於他的……左胳膊?
徐望立刻停下腳步,二話不說就上手,哪知道費半天勁也沒擼起密不透風的羽絨服袖子,隔著衣服拍一拍,好像也沒什麼異樣。但他還是不放心,索性脫掉半面外套,讓胳膊上只剩保暖大學T,總算一擼到手肘,露出整條小臂。
下一刻,徐望眼睛霍地睜大,於瑟瑟寒風中,愣住了。
只見小臂上不知何時出現一個菱形圖案,淡彩紋身似的,圖案正中是一張貓頭鷹的臉,下方則是一個「鴞」字,看起來就像一個手機APP的LOGO。
作為一個常年奮戰在建案接待中心的購屋顧問,一個只需要帶業主看看房屋模型給老闆圈圈地圖的幾乎與風吹日晒絕緣的精緻青年,徐望發誓被拖進流沙之前他那胳膊還白得跟藕節似的,更微妙的是現在那個貓頭鷹臉的右上方還掛著一個小小的「1」。
沒有哪個智慧手機時代的青年能忍著不去點。絕對沒有。
既恐懼忐忑又難耐心癢的指尖終於觸碰到貓頭鷹臉,菱形圖案瞬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四個選項——〈花名冊〉、〈文具盒〉、〈小抄紙〉、〈成績單(1)〉。
小臂就是橫向手機螢幕,圖示就是APP,選項就是系統功能表——這模式實在太親民,徐望幾乎是無縫接入,很自然去點新消息的來源:〈成績單〉。
介面切換,一條置頂消息從左往右滾動:〈蘇明展、陶阿南、蔚天杭、岳帥,3/23交卷。〉
顯然,剛剛那聲「叮」就是這則消息的提示音。
但是3/23是什麼?交卷又是什麼意思?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子夜鴞(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41 |
二手中文書 |
$ 261 |
科幻/奇幻小說 |
$ 297 |
華文 |
$ 297 |
中文書 |
$ 297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子夜鴞(一)
過了十年,心尖的白月光吳笙竟穿著睡衣站在眼前,
這肯定是夢啊!就算是短褲赤膊站在雪原林海之中,
徐望也只想趕快來個親親抱抱舉高……媽呀!有熊!
一記熊掌落下,足以讓他認清現實──
吳笙是真的,還有其他人……也是真的。
而這脫離現實、超越認知的地方是──「鴞」。
午夜子時,鴞啼兩聲,
被選中的人都將無法抗拒地墜入這個魔幻空間,
被迫組隊展開一場又一場的闖關冒險直至天明。
日裡,他們作息顛倒,跋涉千里,奔赴空間開啟點,
夜裡,接受沒有最凶殘只有更凶殘的各種關卡挑戰,
而一路勝利通關是擺脫「鴞」的唯一途徑。
但有酷愛硬啃難題的吳軍師在側,
「聲(笙)望金錢」小隊徐隊長信心喊話:
奮起吧,夥伴們!
刺激危險平常過,闖關冒險我最行!
商品特色
《鬼服軍團》、《喪病大學》作者再一魔性歡暢之作!
不容拒絕的魔幻空間,
保證凶殘(歡樂)的闖關(心動)冒險!
午夜子時,鴞啼兩聲,「聲望金錢」小隊預備備──
管他是熊、炸彈、海怪還是喪屍,儘管放馬過來!
作者簡介:
姓顏,名涼雨,字壯壯,平生最愛三件事,吃飯,寫文,看鬼片。自認閱盡一切重口味,落筆卻永遠小清新。沒什麼大的志向,只希望能用鍵盤敲打出生活的美好,也希望不管過了多久,那些曾經喜歡過我或者依然喜歡著我的朋友,不會為這份喜歡後悔。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徐望從沒想過這輩子還能遇見吳笙,哪怕是在夢裡。
但是他遇見了。
茫茫雪原,皚皚林海,他只穿一條短褲漫無目的地前行,穿過一棵又一棵樹,越過一個又一個小雪坡,哆哆嗦嗦抱著胳膊,沒半點平日的健談與帥氣,以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狀態,遇見了他高中時的心頭白月光。
八成是為了配合他的夢,吳笙也穿著一套同周遭環境極不和諧的睡衣,亞麻條紋的長袖,在禦寒方面比他的赤膊強點,但也就強那麼一點點,鼻頭同樣被凍得泛紅,但人家就有定力站在那兒一動不動,連眉頭都不皺一下。除了五官脫去了當年的稚氣,眉宇間多了幾分成熟和...
徐望從沒想過這輩子還能遇見吳笙,哪怕是在夢裡。
但是他遇見了。
茫茫雪原,皚皚林海,他只穿一條短褲漫無目的地前行,穿過一棵又一棵樹,越過一個又一個小雪坡,哆哆嗦嗦抱著胳膊,沒半點平日的健談與帥氣,以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狀態,遇見了他高中時的心頭白月光。
八成是為了配合他的夢,吳笙也穿著一套同周遭環境極不和諧的睡衣,亞麻條紋的長袖,在禦寒方面比他的赤膊強點,但也就強那麼一點點,鼻頭同樣被凍得泛紅,但人家就有定力站在那兒一動不動,連眉頭都不皺一下。除了五官脫去了當年的稚氣,眉宇間多了幾分成熟和...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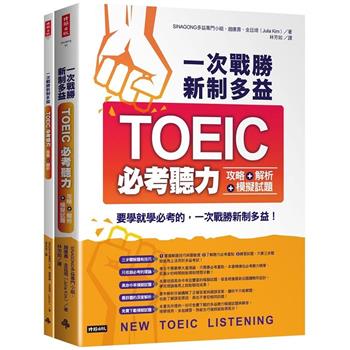





 2026【圖表整理+最新法規】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看這本就夠了[十六版](初等考試/五等特考)](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4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