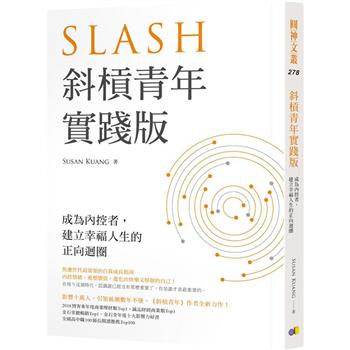第一章
11/23,貴州。
踏入紫色漩渦的時候,五個小夥伴耳畔不約而同迴蕩起樊先生提供的有償情報。
【11/23,鴞會送你們進入一個民國時期的案發現場,多半是凶殺,偶爾也有奇人異事、怪談等雜類,但萬變不離其宗——撥開迷霧,找出真相。】
推理解謎,這四個字聽在小夥伴們耳朵裡,簡直等同於「獎勵關卡」。有吳笙在,走解謎線,他們就是想悲觀,心裡也止不住花兒朵朵開,再靠近看,每一片花瓣都是一張卷子,上面全是「對勾」,一百分。
就這麼洋溢著勝券在握的微笑,小夥伴們視野重新清明。
純白密室,未來科技感,太空艙。
五個小夥伴:「……」
完全一樣的場景,讓五人在剎那間有種時光倒流的錯覺,彷彿回了9/23的腦內地獄,下一秒暗格就要彈出。
「喀——」
很好,果然彈出來了。
池映雪的臉色比暗格還沉,顯然這設施並沒有承載什麼美好記憶。
另外四個夥伴的臉色也好不到哪裡去,這是民國?這是破案?這是解謎?樊夜白要是不拿出個「七天無理由+極速退款+假一賠十」的豪華套餐,他們絕對要去無盡海逢人就刷差評!
【鴞:歡迎來到亂世民國!】
剛把賣家腹誹完,耳內提示就替樊先生洗刷了冤屈。
五人一怔,立刻仔細聽。
【鴞:規則很簡單,一號暗格者,接任務、完成任務、交卷;二~五號暗格者,確保自己存活到一號暗格者交卷。過程中,如彼此相遇,二~五號暗格者,可輔助一號暗格者交卷。切記:一,每人只可以使用一次文具,再用無效;二,五人中任何一人死亡,即視為交卷失敗。】
【鴞:你們有三分鐘時間挑選暗格,倒數計時開始。】
五夥伴面面相覷,顯然,這關已經在形式上進行了更新,而且很可能就是最近的事,所以樊先生那邊才沒有及時跟進。但核心,仍然是民國+解謎。
按照規則,一號暗格是這關的絕對主力。
四道目光落吳笙身上,幾乎沒有任何猶豫。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吳軍師不推脫,但還有事情叮囑:「規則裡說『如果相遇』,說明我們五個會分開;『確保自己存活』,說明二~五號會遇見危險;所以除非條件允許,否則你們不要硬來找我,確保自身安全是第一位。」
徐望替三個夥伴點頭:「明白。」
明白是明白,但民國亂世,風雲詭譎,他們怎麼可能讓自家軍師獨闖呢!
◎
民國天津,五大道,白公館。
「白先生,這些錢不敢說是酬勞,您就拿著喝喝茶,一旦找到我兄弟,薛某人還有重謝!」
說這話的是一個面相忠厚的青年,身量魁梧,一襲文質彬彬的中式長衫,愣是讓他穿出了勇武之氣。他朝著坐在沙發裡的白先生,抱拳作揖,語氣誠懇,字字鏗鏘。
公館主人白先生,是一個摩登英俊的青年,頭髮梳得一絲不苟,鼻梁上架著金絲邊眼鏡,一身西式裝扮,和來訪的這位薛姓委託人,在畫風上格格不入,彷彿新舊兩個世界。
「薛先生放心,這事兒,我接了。」
白先生聽了十幾分鐘的「案情陳述」,期間一直若有所思地安靜著,弄得薛青山很緊張,這會兒終於開口,沒半點廢話,就是乾淨俐落的「我接了」,之於薛青山,像是一陣甘霖。
「那就有勞先生了!」薛青山千恩萬謝,就好像不是他給對方錢,而是對方給他錢。
白先生笑笑,雖然還沒開始工作,但不妨礙他坦然接受甲方預支的感恩。
送走薛青山,白先生回到書房,看著滿目各類書籍和桌案上堆著的好幾本「調查手劄」,莫名羨慕起民國的「乙方們」。這種亂世,只要你有真本事,就能硬氣,要是這本事通了天,那別人出再多的錢,也不敢說「雇」你,得說「請」。
白先生,家境殷實的「青年偵探」,在最繁華的五大道置了這座白公館,專接各類疑難雜案。不為賺錢,就是個愛好。不承想做出了名聲,剛剛來的這位薛少爺,就是慕名而來,拿著足以讓任何偵探涉險追凶的錢,卻只是想尋一個人——他的結拜兄弟,杜錦年,失蹤了。
不過此刻,白先生,並不是真的白先生。他的身體裡,是吳軍師的靈魂。
吳笙千算萬算,沒算到這一次竟然是魂穿模式。都怪那暗格艙和9/23的太像,以至於他想當然認為,還和上次一樣,雖然是意識在闖關,但是依然是自己模樣。這下倒好,他成了別人,那四個夥伴肯定也模樣、身分各異。就是在大街上走個迎頭碰,估計也是相逢不相識。
吳笙一邊想著,一邊再次抬起手臂。
他進入一號暗格,也是這次闖關唯一的任務執行者。而現在,不,應該說在薛青山到來時,他的任務就頒布了——
〈小抄紙〉:接受薛青山的委託,找到杜錦年。
民國天津,海河旁,掛甲寺。
徐望還沒睜開眼睛,先聞到了香火氣,幽靜,肅穆,讓人不自覺心內安定。
這是他這個夜晚,唯一平靜的瞬間。
然後,他睜開眼睛,看見了這個世界,看見了滿院子的和尚,看見了自己穿著的僧服,又在蓮花池的倒影裡,看見了自己那張雖然唇紅齒白、眉目靈動,但全然陌生的少年臉。
心潮就此澎湃,驚濤拍岸的,啪啪啪啪啪,每一下都啪得他頭暈目眩,無比懵逼。
直到一個年紀稍大點的和尚過來訓斥他:「還愣著做什麼,快走。」
徐望傻愣愣地問:「走哪兒?」
說話間,院內逐漸冷清下來——剛還在院內的和尚們,已經陸續出了門,在這剛入夜的街上,像一支修行的隊伍。
「程家啊。」和尚一邊說著,一邊把他往門外推,「程家的老太爺往生了,明天接三,要做法事的。」
徐望茫然:「接三?」
「往生三日,逝者登望鄉臺望鄉,此時誦經超渡,讓他知道,家裡人已等他三日,然逝者不可復生,這一場法事,也算得上他和家人的最後一面了。到時候師父放焰口,你跟著師兄們誦經就行。」
徐望:「……」放焰口又是啥啊!他的知識體系在這一塊是空白區啊!
「快去啊——」眼看院裡要沒人了,和尚猛推他後背一把。
徐望踉蹌著到門口,一咬牙,小跑跟上前方的僧侶隊伍。
往好的方面想,在這民國亂世裡做個和尚,至少沒有性命之虞了,寺院有一縷香火,他就有一口飯,就算不能和小夥伴們會合,堅持到吳笙交卷,總可以的。
天色完全暗下來,月上梢頭,空氣漸漸涼了。徐望抬頭看月亮,看著看著,那月亮就成了吳笙的臉。
他在心裡說:你可要快點交卷,這沒頭髮的夜晚,太冷了。
民國天津,程家。
夜已深,靈棚仍燃著白燭。白日裡孝子賢孫們都哭完了,這會兒只有幾個下人守著,全是青壯年,穿得整潔但樸素,皮膚多是晒得黝黑,一看就是苦出身。
錢艾就在其中。
一睜開眼睛,面前就是靈棚,然後小風一吹,燭火一搖,照著那些紙紮的童男童女,馬匹牛羊,簡直比喝風油精還刺激。要了老命的是,他還覺得自己和那倆童男童女對上眼了,莫名覺得倆紙人在看他,並且這感覺一來,還抹不去了,他怎麼左右擺頭,原地轉圈,都覺得那兩雙眼睛跟著他動。
旁邊一個方臉下人都困乏了,見他渾身難受似的不老實,疑惑咕噥:「幹嘛呢(嘛呢:「什麼」之意。)?鬼上身啊。」
還沒等錢艾說話,另外一個圓臉下人不樂意了,滿眼求生欲:「大哥,這種玩笑話不好在這時候說吧……」
錢艾簡直想給圓臉點個讚。在靈堂說鬼上身,你是不是嫌命太長!
方臉一愣,再看這靈堂、白燭、紙人,不言語了。但已經晚了,他也開始覺得紙紮人在看他,於是走上了錢艾的老路——左右擺頭,原地轉圈。
程家後花園,院牆外。
「師父?你就沒想過改行嗎?」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將連著繩索的八爪鉤遞給旁邊的中年人。
「改什麼行?」中年人將八爪鉤往牆上一扔,一拽,繩索穩穩繃直。
「就……別當飛賊了。」少年人和中年人,都穿著一襲黑衣,包頭蒙臉,捂得連親媽都認不出來。
「不當賊?老子喝西北風去?」中年人一躍而起,體態十分輕盈,順著繩索俐落上牆,挪到旁邊,俯下身體伏在牆頭,以免引人注意,然後衝下面催促:「上來。」
少年規勸不成,只得抓住繩索,一點點往上爬。
中年人等半天,發現徒弟才爬了一半,無語:「收腹,提氣,足下一點,借力而起……不是讓你盪秋千!」
中年人素來沉穩,很能壓住脾氣,但今夜實在腦袋疼。自家徒弟不知道中了什麼邪,一路聒噪就算了,勸他改邪歸正他也忍了,現在連堵牆都翻不過來,要這麼個破徒弟有何用!
「我教你的你都就飯吃了?」中年人忍無可忍,伸手下去一把將人薅住。
少年藉著繩索和師父的拖拽,終於爬上牆頭。
月黑風高,師徒二人順利入了程家。
這幾天程家辦白事,往來人雜,注意力又都在喪葬事宜上,正適合「隨風潛入夜,偷盜細無聲」。
況金鑫魂穿了,魂穿到了一個飛賊徒弟身上。他奉公守法了二十三年的人生,正在一點點滑向犯罪的深淵。
民國天津,南市(三不管地帶)。
「兄弟,到你了。」池映雪一睜開眼睛,就看見有人給他遞過來一個籤筒。
籤筒裡還剩六支籤。
他快速環顧四周,一個簡陋的、散發著汗臭氣的窩棚,一群流裡流氣但面色凝重的小青年,怎麼看都像不法據點。
「抽啊。」拿著籤筒的人催他。
池映雪莫名其妙,抬手剛要抽,忽然發現不對,雖然這隻手也很好看,但不是自己的手。
他再摸摸頭髮,掐掐臉,撈開衣服看看前胸,果然,這是另外一個人的身體。
「嘛呢?」籤筒快被懟到他臉上了,「趕緊抽!」
池映雪蒙頭蒙腦,隨手抽出一根——籤子底部,紅色。
空氣突然安靜。屋子裡的人好像都鬆了口氣,但面上,仍繃得沉重。
「兄弟,認命吧。」那人把籤筒放下,嘆息著拍拍他肩膀。
池映雪蹙眉,發出了甦醒後的第一問:「認什麼命?」
那人皺眉,皺得比池映雪還深,聲音也沉下來:「抽黑紅籤兒就是這個規矩,各憑天命,你想不認?」
池映雪靜靜看了他片刻,決定還是不能委屈自己:「認不認的再說。你先告訴我,我是誰?我在哪裡?為什麼要抽籤?抽到紅籤會怎樣?」
一屋子小青年:「……」
拿籤筒的臉都要氣白了,籤筒一摔,壓根不理他,直接推門出去:「九爺,紅籤出了,貓五。」
池映雪:「……」
這是抽籤名?行動名?幫會名?
「貓五,別記恨兄弟們。」左右兩雙手,一雙擒住他一條胳膊,還沒等他反應過來,身後已上來人,將他雙手牢牢捆在背後。
哦,貓五是他在這裡的名號,真是……沒有比這再難聽的了。
衣服也難看。池映雪低頭看看自己,再抬頭看看一屋子「妖魔鬼怪」,腦海中對民國風情的美好暢想,幻滅得渣都不剩。
拿籤筒的人返回屋內,身後跟著一個穿著十分體面的男人。四十歲左右,身材頎長,一襲長袍馬褂,復古穩重,盤扣精緻,袖口還紋著圖樣。他的臉很英俊,歲月幾乎沒有讓他的俊美打折扣,可歲月還是在他眉宇間,沉澱下了斂不去的肅殺之氣,眼神也銳利,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狠辣。
一進門,他的目光就落到池映雪身上。
「有什麼要求你儘管提,提完了安心上路,家裡人不用擔心,自會有人照顧。」男人的聲音冷冽,即便是這樣溫和的語氣,仍聽得人脊背發涼。
一屋子小混混,平日裡也是欺行霸市的主兒,對著這位九爺,連正眼都不敢抬,大氣也不敢出。
池映雪倒沒什麼感覺。吳笙說了,鴞讓二~五號生存到交卷,說明肯定會遇見危險,如今他一進來,就要被人送上路,很符合關卡劇情,沒毛病。
「我提了,你都能答應嗎?」他問得充滿懷疑,且態度裡毫無尊重。
一屋子人臉都青了,嚇的。
九爺卻微微一笑,很是和藹:「除了命,都行。」
池映雪點點頭,決定信他一次:「我是誰?我在哪裡?為什麼要抽籤?抽到紅籤會怎樣?」
「……」連珠炮的問題,給九爺弄愣了。
「回答問題,這就是我的要求。」池映雪自認體貼地做了補充說明。
九爺:「……」
一屋子混混:「……」
拿籤筒那個:「九爺,他可能是抽到紅籤嚇的,腦子不好了……」
九爺抬手。拿籤筒的立刻閉嘴。
九爺沉吟片刻,一一作答:「你叫貓五,是我們福壽會的人。福壽會殺了海幫的人,現在海幫上門,要我們抵命。老規矩,抽黑紅籤兒,抽到紅籤的,就要替幫會抵命。還有其他問題嗎?」
池映雪定定看了他良久,末了真心實意道:「你這身衣服好看,能給我也弄一套嗎?」
◎
況金鑫跟隨師父從假山密道裡出來時,程家大院起了霧。霧氣讓老宅森冷起來,配上滿目素白喪布,更顯陰風惻惻。
況金鑫背著方方正正的大箱子,跟背聖衣的聖鬥士似的,亦步亦趨跟著師父穿過假山,往院牆處去,準備神不知鬼不覺地溜掉。
他們已經得手了。箱子裡滿滿都是古玩字畫,況金鑫雖然對此沒有太深入的研究,但師父放著滿室銀元、首飾不拿,單要這一箱東西,他就明白,誰最值錢了。
不過有一點很奇怪。他這位師父,來這程家,簡直像回自己家一樣熟悉。沒走一點冤枉路,徑直就入了密道,摸進人家的「財富中心」。而且一進去,也不翻找,一眼鎖定這箱子,讓他扛起來就走,沒半點留戀。
目的太明確,線路太清楚。
「誰在那裡?」旁邊樹叢裡冷不防傳來一聲質問。
況金鑫嚇一激靈,腳下本能一頓,就覺得眼前「刷」一下——師父已經上牆了。
況金鑫沒時間擦汗,立刻以最快速度往牆根衝,想藉著衝力一腳蹬住牆面,身體借力上去……
錢艾一衝出來,就見一個背著大箱子的小子,正手腳並用往牆頭上爬,爬得那叫一個緩慢,那叫一個艱難,看得他都有心想過去幫忙托舉一把。
他是被茅房的味道熏得懷疑人生,所以才尋到這片鳥語花香之地,準備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方便一下,哪知道剛鑽進樹叢,就聽見異樣的腳步聲。
眼前這景象,傻子也看明白了:「小賊哪裡跑——」
一句半文不白的詞兒喊出來,錢艾立刻有種夢迴開封府的感覺,瞬間王朝馬漢附體,張龍趙虎傍身,一個虎步衝過來,二話不說就薅住小賊一條腿!
況金鑫已經趴上牆頭了,眼看就要成功,就覺得腳踝一疼。低頭,一張黝黑的臉,雙目炯炯有神,小老虎似的。
對不住了。況金鑫在心裡默默道,而後避開眼睛,一腳蹬到對方臉頰上!
錢艾本來預計賊要往回抽腿,萬沒料到鞋底蹬了過來,一時不察,被蹬了個正著,疼是其次,關鍵是打人還不打臉呢,於是在滿腔憤懣下,過都不過腦子,直接嚷:「我去,你還真踢啊——」
況金鑫在這個「我去」裡,愣住了。再看底下那張臉,熟悉的感覺撲面而來。
「錢哥?」因為不確定,況金鑫這一聲呢喃得很輕,而且剛一出口,已經到了牆外的師父,就一把給他拽下來了。
於是這兩個字和他落地的嘈雜聲混在一起,聽在錢艾耳朵裡,比這滿院的霧氣還謎。
前科?
錢多?
錢……哥?
這世界裡能喊他錢哥的,除了小況,不做第二人想。但……不會這麼巧吧!而且就算真是小況,怎麼就能一眼認出他是錢艾?「我去」又不是他專用的,隊長、軍師、小雪,都可能喊。
錢艾仰脖看著牆頭,忽然有衝動跳上去,朝外面問個清楚。
可牆外越來越遠的腳步聲,明確告訴他,賊不止一個,而且已經跑遠了。
「嘛呢嘛呢,在這幹嘛呢!」一個中年人罵罵咧咧過來了,「靈棚那邊少個人就成單數了,壞了規矩出了事,你擔得起嘛。」
錢艾低眉順目陪笑臉。不是他脾氣好,而是甦醒之後,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在聽這人嘮叨,已經免疫了。這人是程家請來的茶房,也就是專門幫人料理紅白喜事的,所有環節、規矩他都懂,從換裝裹、停屍、入殮、接三,到燒七、弔唁、出殯,一連串事宜都由他張羅操持。
回靈棚的路上,茶房一直絮絮叨叨,聽在錢艾耳朵裡,就是吐槽,他也終於鬧明白了茶房忽然發火的原因——有人上門弔唁了。
「就沒見過這麼不懂規矩的,哪有沒入殮就來弔唁的。再說,這都嘛時辰了,孝子們也要休息啊,誰來『陪祭』?誰來『謝孝』……」
錢艾聽得一知半解的,反正哼哈點頭總沒錯。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子夜鴞(五完)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41 |
二手中文書 |
$ 261 |
科幻/奇幻小說 |
$ 261 |
Light Novel |
$ 261 |
Comic Book |
$ 297 |
中文書 |
$ 297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子夜鴞(五完)
就算是不識面目的魂穿,也無法掩蔽真愛,
確認過眼神,徐隊長與吳軍師一秒匹配,
帶著默契滿分的小夥伴們高歌猛進,
不論是懸案謎團在前,還是榜上有名的強敵攔路,
小隊依舊快樂闖關前行,直至神祕的第十三關,
這個前輩口中從無闖關者能記得內容的關卡……
而想到通關後關鍵時刻即將到來,徐望左右為難──
是要確保自己小隊安全離開「鴞」?
還是冒著不知後果、代價的風險,堅持關閉「鴞」,
為其他深受正常生活被剝奪之苦的眾人博得解脫?
人與我之間的人性考驗從來艱難,
幸而他身邊有最愛及值得幸賴的夥伴在,
「不管怎麼選,我(們)都陪著你。」
本書收錄番外〈他們的4:37〉、〈風生水起〉、〈請進〉,
以及繁體版獨家番外〈小四金失蹤案〉。
商品特色
熱血感動終結!
最後的選擇,最終的考驗──
想關閉「鴞」,竟得一打十三?!
為完成一夜十三關的任務,徐小隊長登高一呼:
大夥兒,「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時候到了!
作者簡介:
姓顏,名涼雨,字壯壯,平生最愛三件事,吃飯,寫文,看鬼片。自認閱盡一切重口味,落筆卻永遠小清新。沒什麼大的志向,只希望能用鍵盤敲打出生活的美好,也希望不管過了多久,那些曾經喜歡過我或者依然喜歡著我的朋友,不會為這份喜歡後悔。
章節試閱
第一章
11/23,貴州。
踏入紫色漩渦的時候,五個小夥伴耳畔不約而同迴蕩起樊先生提供的有償情報。
【11/23,鴞會送你們進入一個民國時期的案發現場,多半是凶殺,偶爾也有奇人異事、怪談等雜類,但萬變不離其宗——撥開迷霧,找出真相。】
推理解謎,這四個字聽在小夥伴們耳朵裡,簡直等同於「獎勵關卡」。有吳笙在,走解謎線,他們就是想悲觀,心裡也止不住花兒朵朵開,再靠近看,每一片花瓣都是一張卷子,上面全是「對勾」,一百分。
就這麼洋溢著勝券在握的微笑,小夥伴們視野重新清明。
純白密室,未來科技感,太空艙。
五個小...
11/23,貴州。
踏入紫色漩渦的時候,五個小夥伴耳畔不約而同迴蕩起樊先生提供的有償情報。
【11/23,鴞會送你們進入一個民國時期的案發現場,多半是凶殺,偶爾也有奇人異事、怪談等雜類,但萬變不離其宗——撥開迷霧,找出真相。】
推理解謎,這四個字聽在小夥伴們耳朵裡,簡直等同於「獎勵關卡」。有吳笙在,走解謎線,他們就是想悲觀,心裡也止不住花兒朵朵開,再靠近看,每一片花瓣都是一張卷子,上面全是「對勾」,一百分。
就這麼洋溢著勝券在握的微笑,小夥伴們視野重新清明。
純白密室,未來科技感,太空艙。
五個小...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