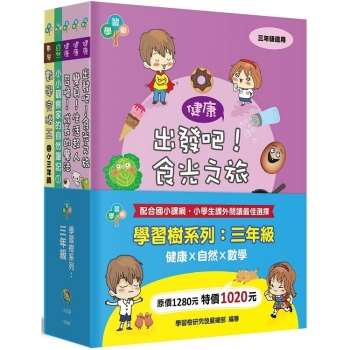1
購物季即將揭開序幕,戶外舉辦的活動一下子多了起來。年末公演與購物季重疊,估計到年初為止都會忙得不可開交。蜂擁而至的工作讓公司發出歡樂的哀號,但身為隨機人員同時又是最底層的第九分隊,正在痛苦地慘叫。
「唱歌跟殺豬一樣。」
凱文摸了摸自己冒出黝黑鬍碴的下巴,接著說道。
「我敢保證,不出一年,他就會從電視上消失。你有沒有看到?人家區區『一片』歌手,架子可大得很啊。就因為他這麼囂張,連他的保鑣都把我們看扁了。」
像今天這種有知名藝人參與的活動,除了主辦方僱用的護衛隊之外,通常也會出動明星自己的貼身保鑣,雙方陣營時不時便有摩擦產生。貼身保鑣耍大牌是常有的事,根本無足掛齒,但對於進公司還不到一個禮拜的凱文來說,卻彷彿遭受了天大的人格侮辱,整個人都激動到不行。
「尤其是那個黑人大隻佬。當自己是歌手還是大明星啊?哪來那麼多要求。」
「那種傢伙本來就比藝人還囂張。」
一旁安靜聽著的德瑞克,抓抓鼻梁說道。
「大家都是做護衛的,他憑什麼?」
「當然是因為他們懂得更多、更有前途嘛。」
德瑞克抓了抓後腦勺,眼珠子一轉。
「女生倒是滿漂亮的。」
「嗯,是沒錯啦。胸部又大,皮衣都要被她撐破了。」
剛才還在裝模作樣的德瑞克,很快就露出了粗鄙的笑容。這是他第一次對凱文下班後到現在的話題表現出興趣。凱文瞥了眼德瑞克彎起的嘴角,興奮地說道。
「你有看到嗎?她的胸部都跟臉差不多大了。」
德瑞克微微點頭。
「對吧?眼裡就只有那個了吧?艾德,你也看到了嗎?」
如果是指那些十幾歲上下、在表演場地把護衛隊當下人使喚的無禮少年,我倒是看了個夠。之前忙著阻止一群膽大妄為的女孩衝進百貨公司門口,只為看一眼美少年搖滾樂團,我根本沒機會欣賞到美女的胸部,於是便搖搖頭。
「臭小子真可憐。多虧了這副墨鏡,我簡直是大飽眼福啊。」
「您還真是一刻也沒分心呢。」
在前座開車的艾許,從後視鏡看向後面說道。被隊長沒好氣地一說,凱文也一臉心虛地笑了笑。
二十歲後半的凱文,是艾許介紹進來的臨時員工。預計在這裡實習一個月、熟悉工作,之後就要進到艾許的公司。軍人出身的他,雖然和艾許在同一個部隊服役,卻與木訥、嚴守階級制度的艾許不同,是個愛講話的傢伙。喋喋不休的程度,就連平時話最多的德瑞克也忍不住要給他使眼色警告一下。
「拜託你,就算只做短短一個月,也給我認真一點。一個護衛只顧著看女人的胸部嗎?只要那個女的說出去,我們一個個都得打包走人啊,臭小子。」
艾許語氣煩躁地抱怨。凱文隨即聳聳他寬大厚實的肩膀,難為情地笑著。
「臭小子,不准笑。我會看你的表現再決定要不要帶你走。」
「反正你一定會帶的嘛。」
為了打理和瑞秋部長一起設立的保全公司,艾許預計在兩週後向公司辭職。然而,他所面臨的情況卻並不樂觀。無法在保全公司的十二月檔期之前找到人,這幾乎要壓垮他對創設公司懷抱的滿心期待。
「要不是找不到人,我才不會帶你去咧。」
只見艾許語氣挑剔,說起話來又硬邦邦的,凱文自說自話地嘀咕著:「太好了。」艾許立刻勃然大怒。
「什麼?太好了?」
明明音量大到每個人都能聽見,凱文還無比委屈地看著艾許。
「我哪有說。」
「我都聽見了。」
「艾德,我有那樣嗎?」
凱文用神經兮兮又委屈到不行的眼神朝我看來,但我也只是笑笑,給不了什麼反應。
我們在一棟老公寓前放凱文下車。後視鏡裡的凱文對著逐漸遠離的車子揮揮手,德瑞克瞄了他一眼,語帶煩躁地咕噥一句:「一個大男人怎麼這麼多話?」
平日裡德瑞克的吵鬧程度也不亞於凱文,不過他因為感冒加上分手的傷痛未癒,也變得沉默寡言許多。
「你也是啊。」
「什麼?」
德瑞克看著我,托腮的臉皺成一團。
「你也沒有比他安靜到哪去。」
「我才沒那麼誇張好嗎?」
我對著忿忿不平的德瑞克咧嘴一笑,對方不爽地皺起眉頭。前座的艾許也幫腔道。
「艾德說得沒錯,你真的很吵。」
「你們是怎樣啊?我最近很嚴肅的。」
「這小子,一跟他說真話就要生氣。」
「都說了我沒心情跟你抬槓。」
眼見德瑞克開始大小聲,艾許於是聳聳肩笑了起來,大概是覺得從凱文那邊受的氣全都得到了補償。德瑞克連發火的力氣都沒有,只是死死瞪著艾許的後腦勺,並未繼續說下去。
他從口袋裡掏出衛生紙,擤完鼻涕之後,便隨手塞進車子內部凹陷的收納空間。以往總會念叨幾句的艾許,這回也沒有表示什麼,只是默默地開車。
艾許將車停在下東城的公車站旁,那一帶附近到處都是餐廳,開往我家的那輛公車也會行經這一站。下車之前,我將已經脫線脫得稀稀疏疏的圍巾緊緊裹在脖子上。
「今天去喝一杯吧。」
就在我打開門的前一秒,德瑞克捉住我的手腕說道。在換季感冒的摧殘下,他面容憔悴地吸了吸鼻子。
「你請客我就去。」
「慢走不送。」
眼看德瑞克回答得毫不留戀,我噗哧一笑,用掌心拍了拍對方的太陽穴。
「好好休息啊。」
德瑞克睜著一雙鬱鬱寡歡的八字眼,一邊偷瞄我一邊說道。
「什麼啊?你真的不喝嗎?」
手指勾住把手將車門一拉,冷風便灌了進來。我站上人行道把門關上,車子卻沒有馬上出發。車窗被搖了下來,德瑞克驚天動地地擤著鼻涕,把頭伸到窗外。
「真的不去喝一杯?」
「嗯。」
「我請客也不喝?」
「……那就去好了。」
「沒品的渾蛋。」
那傢伙罵罵咧咧地臭著一張臉把窗戶關上。看他嘮叨個不停,雖然不太厚道,但我還是忍不住笑了出來。德瑞克動作遲緩地拎著自己的東西走出來,朝我輕輕揮了一拳。我往後避開尾隨而來的拳頭,並敲了敲駕駛座的車窗。降下的車窗縫隙間,露出了艾許不耐煩的表情。
「一起去吧,德瑞克說他請客耶。」
「是要叫我酒駕嗎?瘋了吧你。」艾許擺擺手說道。
「喝得差不多就回去吧。不准說我壞話。」
「不然你想怎樣?這樣我們喝酒的時候就沒話題聊啦。」
看著邊吸鼻子邊抱怨的德瑞克,艾許大嘆一口氣。
「那您愛怎麼罵就怎麼罵吧。」
他一臉疲憊地看看德瑞克再看看我,最終關上窗戶,踩下油門駛進車道的側臉顯得粗糙不已。
距離辭職已經不到兩個禮拜,艾許散發出的氛圍也跟以往不大一樣。他會擺出不想上班的態度或者傷腦筋的表情,在休息室講電話講到一半時,只要我一進去就又一副諱莫如深的模樣。過去團結一心的第九分隊開始變成一盤散沙,總能從艾許身上感受到將走之人特有的漫不經心。
平時和德瑞克常去的那家啤酒吧就在不遠處。很特別的是,這間由一般倉庫改建而成的啤酒吧裡,放著各式各樣的Arcade遊戲機。德瑞克點完幾道簡單的配菜和啤酒後,又是咳嗽又是打噴嚏的。
「啊……再這樣下去我會死的。」
擤了一整天的鼻涕,德瑞克摸著紅通通的鼻子嘀咕道。
「這都什麼事啊?被甩了不夠,竟然還感冒。」
「這就叫業障啊。」
「什麼?」
「報應。」
「找死嗎?」
德瑞克火氣一上來,撿起剛才擤過鼻涕的衛生紙朝我一扔。衛生紙球打中臉頰,掉到桌子上。我用食指和拇指小心翼翼地捏起那坨溼答答的東西,一把扔回去給那個臭小子。
「髒死了。」
「你最好也給我感冒。」
「不行。」
「為什麼?」
「那樣會傳染給那個人啊。」
他整張臉都垮了下來。啊,原來如此啊。德瑞克一邊挖苦我,一邊把眼前的啤酒灌下大半。
「想不到我還有被你晒恩愛的一天。」
「不行嗎?」
「喔,我完全無法想像你會做這種事。」
德瑞克誇張地抖動著身體。看到他幼稚的反應,我無聲地笑了笑,正在用衛生紙擦鼻子的德瑞克抬起眼睛端詳著我。
「……什麼啦,有這麼喜歡喔?」
我撫摸著啤酒瓶上凝結的冰涼水氣,對著他的臉默默點頭,對方立刻緊閉嘴巴,而後稍微打開。德瑞克歪歪地垂下腦袋,擺弄著手中的Zippo打火機。
「煩死人了,真是的。」
「怎樣?」
「你是那種就算在談戀愛,也不會表現出來的類型啊。從來不放閃的傢伙,突然一副樂呵呵的傻樣。」
「……也沒那麼誇張啦。」
「你也很搞笑耶。」
眼看德瑞克的女友一任接著一任地換,我也沒什麼特別感覺;同理,即便有了麥昆,我和德瑞克的關係也不會因此而疏遠。友情和愛情的問題幾乎是截然不同的領域,至少對我而言,為了這種事情表現出失落,是很丟臉的事。在朋友之間展露出自己沒有獲得這方面的滿足,感覺也有些尷尬。
不過看樣子,這傢伙倒有點不是滋味了。我嘻嘻一笑,覺得發牢騷的他也滿可愛的。德瑞克隨即板起面孔。
「你笑什麼?」
「因為你好笑啊。」
他朝桌子這邊俯身。
「有那麼漂亮嗎?」
「就那樣。」
「哪樣啊?」
「很帥啊。」
德瑞克整個人湊到我面前,大聲地喝了幾口啤酒。短暫的靜默之後,他開口道。
「有照片嗎?」
見我搖頭,德瑞克馬上嘖嘖兩聲,用薯條沾了一大坨番茄醬。
「她是做什麼的啊?」
「……上班族。」
「很受歡迎嗎?」
「好像是。」
「你說她比你大對吧?大幾歲啊?」
「五歲。本人看起來,嗯……感覺會大更多。」
德瑞克聞言哈哈大笑。
「我指的不是外貌,是他的氣質……」
「意思一樣啊。」
他一句話就把我擋了回來。對於德瑞克這句玩笑成分居多的發言,我只是笑笑,並未極力反駁。畢竟這傢伙想像出來的女性,絕對不會與麥昆本人有半分相似。況且以目前的情況來看,要把麥昆介紹給德瑞克的可能性也還是未知數。
「長得如何?」德瑞克一邊把剝了殼的花生拿在手中把玩,一邊問道。看著花生在他厚實的手裡,腦海忽然閃過麥昆對花生過敏的事。
「個子很高。」
「就這樣?」
「給人一種……強悍的印象。」
「胸部呢?大嗎?」
德瑞克把花生一股腦兒地倒進嘴裡,嚼得喀啦作響,一臉索然無味地問道。我不禁失笑,完全無法想像麥昆用女生的方式來誇耀自己的性徵,他身上的男性魅力實在太過強大了。
「這方面的魅力嘛,嗯……倒是滿傲人的。」
「噢噢。」德瑞克下垂的眼睛睜得老大。意思是很性感囉?已經理解成另一種意思的德瑞克上下打量著我。
「她會不會玩膩之後就把你丟在一邊啊?光聽你的描述,感覺這個人完美到有點可疑耶。」
「他不是那種人啦。」
「哪有,你之前的女朋友不就是這樣嗎?」
「嗯……是沒錯。」
我爽快地點頭附議,德瑞克反倒小心翼翼起來,一言不發地剝著花生。
「不過,她從一開始就劃清界線了。」
「那你現在的女朋友有在為你們的將來考慮嗎?她被你迷倒了嗎?」
「這個嘛。」
「『這個嘛』又是什麼回答啦?」
「我們才交往沒多久,而且也還沒時間……想得那麼遠。」
僅憑著一腔喜歡就奮不顧身的人反而是我。要為這段關係下一個定義,或者去想像我們的未來,在一切都還模糊不清的時候都為時過早。而我們倆的關係便如同浮雲一般,有種缺乏現實考量的感覺。
我的債務與麥昆的色情片事業,究竟是一個問題還是兩個?又或者問題根本不只這些?我們還沒好好去瞭解、接受彼此所面對的現實,更別提該如何正視其中的問題了。
「只要我……好好表現不就得了?」
我垂下眼睛,一把碾碎手裡的花生殼。德瑞克粗魯地擤著鼻子嘲笑道。
「一聽就知道是戀愛菜鳥。」
「我談的次數也不少了。」
「反正就是不得要領啊。」
聽德瑞克這麼一說,我點點頭。
「這種事情又不是你好好表現就一定能順利。別陷得太深,勞心傷神的戀愛可是很累人的,還要過好久才能忘得掉。」
他輕輕咂嘴,從前口袋裡掏出香菸。
撇除偶爾穿插的短暫約會,算起來,這已經是他今年第三次和交往超過兩個月的女生分手了。不過,只要幾杯黃湯再加上幾天的憂愁,德瑞克就能一如既往地擺脫離別的痛苦。令人心碎的離別縱使留下了陰影,但從德瑞克臉上逐漸變多的笑容和越發輕盈的動作,都能看出他正在慢慢好轉。
許多人的戀愛都和德瑞克一樣,用酒精和些許心痛便可輕易抹去。他勸我也抱持這種心態去談情說愛,我沒有回答,只是把手裡那顆光滑的花生剝成兩半,企圖轉移話題。
「我最近有去蔣的辦公室。」
德瑞克「喀啦」一聲打開Zippo打火機,詫異地看著我。
「什麼?」
「他說這段期間會幫我扣掉利息。」
他頂著扭曲的面容,把手裡的Zippo打火機往桌上一扔。
「幫你扣掉利息?」
「嗯。」
「那傢伙又想對你做什麼啊?」
我悶不吭聲地摸著幾乎沒喝的啤酒瓶長嘆一口氣,德瑞克隨即說道。
「你有辦法看著那個渾蛋的臉做事嗎?還是說你的拳頭睡著了?」
「我們幾乎見不到面。」
「是做什麼的?」
「就……簡單的文書整理。」
「沒有拖著你去做一些要靠肩膀出力的事情?」
我笑得肩膀都在抖。第一次聽到蔣的提議時,我的想法也和德瑞克差不多。
「所以具體來說是什麼工作啊?」
「外匯交易、洗錢,諸如此類的。」
「不能直接叫警察嗎?」
「那這大概是我們這輩子最後一次見面了吧。」
德瑞克神情苦澀地咬著香菸濾嘴的邊緣。
一直住在法拉盛唐人街近郊的德瑞克,最討厭的兩種人,就是越南派系的黑道和唐人街的黑社會。他們雖未對居住於法拉盛的白人造成太大影響,卻已足夠成為眾人厭惡的對象。
「你都什麼時候去啊?」
「星期天、星期一。」
德瑞克把啃到一半的香菸點燃,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皺著一張臉,呼出的煙霧裡夾雜著嘆息。
「我說這個不是要讓你嘆氣的。」
「那你這算什麼好消息嗎?」
「算是好消息吧。」
我咀嚼著鹽味十足的下酒菜,被鹹得口乾舌燥,在舉杯解渴的同時拿出了手機。可能是拍攝行程太忙了,麥昆完全沒有聯絡我。本來想傳個簡訊給他的,在察覺到德瑞克的視線之後,我便把手機塞回口袋裡。
「就算這樣,我曾經也覺得蔣立武這傢伙還不錯。」
這番沒頭沒腦的發言,讓我不禁看向對方。
「只有剛開始的時候啦。」德瑞克辯解似的補上一句但書。
「他沒有中國黑社會那種骯髒又油膩的招牌土包子形象,身上也沒味道。」
我覺得有趣,便直勾勾地盯著他看。德瑞克用拳頭掩著嘴巴,清清嗓子說道。
「長得跟你也有點像,我還以為是你親哥哥咧。」
「……我可沒他長得那麼倒霉。」
「看久了就知道你們長得完全不像,只是乍看之下形象有點類似而已。你給人的第一印象也不太好相處啊。」
「是喔?」
「剛轉學過來的時候,大家都不敢隨便惹你耶。因為立武那小子有在暗中罩你嘛。」
我用掌心撫過乾燥的臉頰,手肘搭在桌上托著腮,慢吞吞地俯身喝了幾口啤酒,應聲道:「他有嗎?」
「蔣不是常常到學校接你嗎?他只帶你一個人玩,你拿到駕照之後還開那傢伙的車,他是直接給你備用鑰匙了吧?」
我輕嘆一聲點點頭。這麼一想,兒時的鄉愁中,總是有蔣的存在。
位於法拉盛唐人街和北方大道附近的這間學校,從移民第三代到不太懂英語的留學生,移民人口的比例占了將近三分之一。美籍華裔的占比更是居多,彼此之間也形成了一條無形的紐帶。
蔣和我因為年齡差的關係,一起上學的時間只有一個學期。然而,他的名字卻像標籤一樣,在我在學期間一直如影隨形。校內出了名的資優生沒上大學,而是到趙偉連手底下做事,隨著消息在學校裡傳開,也開始有人對我投以懷疑的目光。因為在學校沒什麼機會能碰到面,我其實不太瞭解蔣的校園生活。只知道他屬於那種不論身處何處,都是最耀眼、不會被人群淹沒之流。
「德瑞克。」
「嗯。」
「你覺得,人之所以變得極度憎恨某個人……都是出於怎樣的動機呢?」
「不是討厭而是憎恨嗎?這應該可以用來形容那種不共戴天的殺父仇人吧?」
「對吧?」
「什麼啊?」
「我無法發自內心地去恨蔣。」
或許是過往的緬懷在作祟,對蔣感到厭惡的心中總是摻了點雜質。不痛不癢的雜質,令我不禁質疑起自己的憤怒是否正當;而那份疑心,又驅使我去摸索值得讓蔣討厭我的理由,進而逐漸產生自我懷疑。這種過程一再重複,到頭來也只會對自己感到失望而已,我最終直接放棄了思考。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在水面行走(3)的圖書 |
 |
在水面行走 3 作者:Jangmokdan 出版社:平心工作室 出版日期:2024-10-14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在水面行走(3)
「我們別讓彼此……心裡留下疙瘩吧。」
所有的錯誤,似乎都是因那部《轉移錄》而起,
偏離原始劇情的內容就像在昭告世界:
艾德‧塔爾伯特喜歡男人。
他愛麥昆,卻為了自尊心不願直面現實,
無論是在色情片裡興奮喘息的自己,
還是默認將兩人的感情暴露在鏡頭前的麥昆。
但是,紙永遠包不住火,
麥昆的另一重身分突然被曝光──
從未露面的傑出劇作家,竟是同志色情片製作人。
聳動的新聞標題吸引了無數觀眾,
艾德也徹底被攤開在大眾面前,供人審視……
這場意外,瞬間瓦解了艾德和麥昆謹慎維持的表面平和,
可對於總是選擇逃避的他們來說,
又何嘗不是一種轉機?
商品特色
◎韓國RIDIBOOKS 4.7顆星好評推薦!還曾改編為同名網路漫畫、廣播劇,討論度依舊熱烈!
◎特邀人氣繪師Kanapy繪製全新封面,扶後頸,抓領帶,深情對望……無法抗拒的魅惑氛圍~~
◎接受性取向的轉變,讓「同志色情片演員」不再是能夠輕易拋下的經歷,或許還會越陷越深……
◎身分暴露之後,終於點燃深埋在兩人之間的未爆彈──龐大債務和色情片事業,甚至是……他們不曾設想過的問題?
◎隨書附贈沉醉不醒藏書票。
榮獲韓國2019年RIDI BL小說作者大賞!4.7顆星好評推薦☆
性慾旺盛事業型CEO╳不善言辭禁慾系直男
著迷、淪陷、纏綿,他們和普通人一樣相戀,
只要故事的起點,不是同志色情片……
作者簡介:
Jangmokdan
熱愛動物和大自然,並喜愛著各種事物。我從小就喜歡英美文學,快二十歲的時候接觸到了BL題材。2006年執筆創作了《美國的平凡十幾歲少年們》,開啟了創作生涯,已出版的作品有《相思夢》、《在水面行走Walk On Water》、《盜賊》,目前居住在韓國首爾。
章節試閱
1
購物季即將揭開序幕,戶外舉辦的活動一下子多了起來。年末公演與購物季重疊,估計到年初為止都會忙得不可開交。蜂擁而至的工作讓公司發出歡樂的哀號,但身為隨機人員同時又是最底層的第九分隊,正在痛苦地慘叫。
「唱歌跟殺豬一樣。」
凱文摸了摸自己冒出黝黑鬍碴的下巴,接著說道。
「我敢保證,不出一年,他就會從電視上消失。你有沒有看到?人家區區『一片』歌手,架子可大得很啊。就因為他這麼囂張,連他的保鑣都把我們看扁了。」
像今天這種有知名藝人參與的活動,除了主辦方僱用的護衛隊之外,通常也會出動明星自己的貼身保鑣...
購物季即將揭開序幕,戶外舉辦的活動一下子多了起來。年末公演與購物季重疊,估計到年初為止都會忙得不可開交。蜂擁而至的工作讓公司發出歡樂的哀號,但身為隨機人員同時又是最底層的第九分隊,正在痛苦地慘叫。
「唱歌跟殺豬一樣。」
凱文摸了摸自己冒出黝黑鬍碴的下巴,接著說道。
「我敢保證,不出一年,他就會從電視上消失。你有沒有看到?人家區區『一片』歌手,架子可大得很啊。就因為他這麼囂張,連他的保鑣都把我們看扁了。」
像今天這種有知名藝人參與的活動,除了主辦方僱用的護衛隊之外,通常也會出動明星自己的貼身保鑣...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