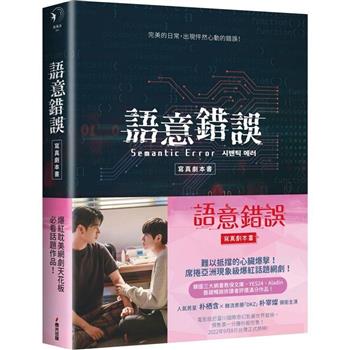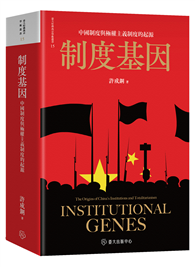楔子
「……二月玉面蝶,三月赤肉嬰,四月斷腸鼓,五月逆竿血……」
街坊空地上,孩童們一邊踢著羽毬,一邊隨口亂唱,這首歌兒是從哪家孩子開始傳起不得而知,他們也不懂辭中含意,只是一個勁兒地唱得歡樂。
「……六月飛白雪……七月離魂天……八月……」
唱到這兒,一名雙髻小兒的腳尖不小心碰歪了羽毬,同伴沒一個能接住,羽毬在地上無力地彈了幾下,原來孩子們紛紛張大了嘴巴,手指著天上。
悠悠晴空一角,正飛來了一隻五彩大蝴蝶,身軀如甜瓜,羽翼如紗窗,大過尋常蝴蝶數倍。
大都市集的上空飛來這隻異蟲,沒多久便引起了民眾爭相圍觀,大家從沒見過這隻龐然大物,耳語四起,議論紛紛。這時,有位頭裹皂羅巾的長鬚男子從對街走了過來,馬上被這群民眾拉住。
「王學士,你來得正好!快來瞧瞧!」
被喚做王學士的男子,名為王和卿,平日雅好吟曲,喜好逍遙愜意的生活,也最愛各種新鮮事物。
「您博學多聞,幫咱們鑑定看看,那是哪來的怪蝶?」
王和卿看了一眼,覺得眾人大驚小怪,笑道:「世上哪有這麼大的蝴蝶,八成是紙鳶吧?」
「喂喂喂,牠動了!」
只見那五彩巨蝶翩然起舞,在樓頂間恣意滑翔,等於粉碎了王和卿的推斷,紙鳶不可能如此自在騰飛,何況也不見有何絲線,那的確是活生生的蝴蝶。
「有意思。」王和卿好奇心大起,撇下眾人追逐那五彩巨蝶而去,足足追了兩個街坊,跑得上氣不接下氣,趕到一座運河橋邊。
那五彩巨蝶輕飄飄地停在橋頭,雙翅展開,背朝著王和卿。他悄悄地走近,想要抓住這隻稀有珍物。
突然間,五彩巨蝶轉身回望,牠的頭上赫然掛著一張慘白少女的臉孔。
這人面蝶身的妖怪,當場嚇煞王和卿,倏地牠振翅而升,颳起的大風把王和卿整個人一搧,搧過了運河橋東。
第一折 賀聖朝
幽空漸藍,星兒濛濛,晨風吹寒天欲曉,一位衣著樸素、目光炯炯的青年獨立在城東一隅,像一盞吹不熄的孤燈,總算等到長夜將盡。
他所在的這座城名為『大都』,城如其名,它稱得上有史以來最宏偉巨大的都城,鬧區市集無不繁華鼎盛,條條大道,寶馬匹匹競馳,水路穿梭,商船艘艘匯聚,陸行漕運,四通八達,冠蓋雲集,萬國咸通。
儘管如此,卻容不下這位布衣青年一宿好眠,任憑他站在這裡一整晚,直挨到敲更天明,也不見有人上前關切,人情如此炎涼,可見一斑。
時為元朝至元年間,當今的皇帝,乃是蒙古人孛兒只斤.忽必烈,世上的人都尊其為忽必烈大汗,他是天下君王之王,擁有的國土,涵蓋蒙古、中原,以及西域的四大汗國,堪稱古今空前未有之霸業。
蒙古人又喚大都城為『汗八里』,即大汗的居所,不僅是天子腳下京城,亦是號令全國的軍政中樞。
當初,忽必烈大汗捨棄了逐草而居的放牧生活,選擇前朝金國國土作為定居之地,雖然引發眾多貴族們的不滿,卻改變不了他經營中原的雄心,其後又推行漢法,敕令如大刀闊斧,揮去了嗜血蠻人的汙名與習性。
之後,忽必列決定開始築城,便命西域人也黑迭兒,花了八年功夫,興建一座雄偉宮殿,並規劃皇城周邊設施與城廓,於是,一個足以向全世界誇耀的大都市於焉誕生。
這座城邑原本是金朝國都燕京,自從哀宗完顏守緒自縊,該朝已經滅亡了三十年,烽火的傷痛逐漸淡去,人民開始安於現狀,放棄了抵抗侵略者的舉動,而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後,便將金國所屬臣民,包括女真人與漢人,均列為漢人階級,屬於次等人種。
那位布衣青年便是其中之一,他名叫馬致遠,原本住在城外田廓附近的一處小鄉里,自幼寒窗苦讀,過著簞食瓢飲的生活。這是他生平第一次上京,抱著一股鵠鴻之志,向街坊鄰居、親朋好友借了錢前往城內,自詡滿腹經綸的他,期待能藉此展露頭角,踏出功名生涯的第一步。
天光敲醒了馬致遠倦睏的眼皮,他守著一扇棗紅色雉尾雕繪木門,這門則嵌在一棟高三層的典雅樓舍上,門口匾額上鐫著『梨園』二字。
這是大都城天字第一號的梨園劇院,北方的太平治世直接或間接促成了它的成立,因為,新的朝代下就會打造出新的城市,新的城市會孕育出新的娛樂,相較起舊有的傀儡戲、皮影戲、說話人,百姓更需要更多刺激與新鮮感,於是當劇院一開張,立刻有如風掃落葉一般,一夕之間搶走了大半客源。
當時的劇院,人們又俗稱為『勾闌』,表演的是以角色說唱方式,來敘述民間故事或歷史故事的一種戲曲,由於題材不拘,內容旁雜,故索性喚作雜劇,而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關劇』。
這『關』字,指的是梨園的戲班頭子,關漢卿,雜劇便是他創出來的新玩意兒,他參考唐代諸宮調、參軍戲為主梗,再把詩客文人消遣自娛的曲子詞,以及傳統茶館裡的說話人,全都合併在一塊兒,有別於傳統鄉間的酬神劇,少了呆板莊嚴,多了生動詼諧,兼之戲中情節高潮迭起,曲折離奇,時而悲壯、時而淒婉,果然人人愛看,甫一推出就場場客滿,愈演愈烈。
一開始,戲班子是在城北鐘鼓樓前搭野棚,後來,為因應觀眾各種飲食上的需求,也為免其受日曬雨淋之苦,關漢卿便積極籌資,蓋了大都的第一間大眾劇院,便是這棟『梨園』。
大都人首見這種新興的娛樂,一些認為有利可圖的商人,抓住這股風潮跟進,仿傚者日益眾多,造成劇院一家接一家的蓋,沒多久,形形色色的劇院如雨後春筍竄出,唱曲的伶人更成了各大戲班爭相網羅的對象,但大部分的雜劇不是瞎扯胡鬧,就是枯燥無趣,惟有梨園的關漢卿不斷創新劇目,穩居主流,任誰都跟不上他這位大才子筆下的神思飛舞。
因此,大都多了一句順口溜:「關劇一開,眾戲迴避。」
今天正是關漢卿新戲上演的日子,各家劇院惟恐生意慘淡,有的刻意改檔期,有的乾脆就休館一日,眾家戲班頭子紛紛派人刺探,美其名是到場祝賀,實則是借觀摩之名,想看看能不能攫取到什麼好靈感。
早起的民眾經過梨園,見到有人居然已經在門口等待,心想不能落於人後,陸陸續續也有其他人開始排隊,將近正午時分,已有一窩蜂的人群排在馬致遠後頭,大家交頭接耳,討論起以前上演過的劇碼。
「記得上一齣是《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看關公氣蓋山河,一身豪膽,直教人滿腔熱血呀。」
「我喜歡『《閨怨佳人拜月亭》那一齣,悲喜交織,久久不能忘懷。」
「對對對,那齣關漢卿自己也上臺演一角呢!」
「他能編能唱又能演,又精通五音六律,果然是大都第一奇人。」
馬致遠對此充耳不聞,一切似乎與他毫不相干,忘了自已正杵在這群看戲人的首位。
就在這時,隊伍外緣走來了一位頭戴鹿紋皮帽的少年,他無視於眾人,像蒼蠅般繞著這條人龍往前鑽,個頭不高的他穿梭在人與人的空隙中,如入無人之境,而且身法行雲流水,一點兒也沒沾染到別人髒衣服上的塵埃。
當然,如此插隊的舉動,很快地引起了其他排隊民眾的不滿,紛紛鼓譟斥喝。
「哪來的小鬼!沒規沒矩!」
「呔!給我乖乖排隊!」
但那鹿紋帽少年不理不睬,腳下走位異常靈巧,幾名壯漢伸手想逮他,都被他左閃右避,一迴旋一溜煙,他人已接近劇院門口。
「簡直目中無人,大家上,教訓這小子!」
眼看那鹿紋帽少年要遭群眾修理,馬致遠突然一把拉住他,回頭道:「喂,別打他,他是我朋友!我們約好一起來排隊。」
一聽到有人仗義執言,更讓那鹿紋帽少年有恃無恐,大剌剌地跳到門前臺階上,站好定位,甚至搶了馬致遠的頭香。
其實馬致遠根本就不認識這鹿紋帽少年,倒也不是好心幫他,純粹覺得後頭那些粗人囉嗦,只想跟他們唱唱反調罷了。
鹿紋帽少年報以微笑,馬致遠裝熟也不是,不理他也不是,氣氛有些兒尷尬,幸好那些民眾已按下怒氣,又繼續閒聊天。
「話說回來,好好的劇院,為什麼叫梨園?」
「可能是後院有種梨子吧?」
鹿紋帽少年噗嗤一笑,他注意到,身旁馬致遠也從嘴角迸出一聲冷笑,不禁試探道:「你也懂這典故,對吧?」
馬致遠睥睨這名鹿紋帽少年,仔細一瞧,對方相貌俊美,星眸皓齒,體態穠纖合度,皮膚又白又淨,顯然是出身富貴之家,不由得遲疑一會兒,才說道:「相傳唐明皇喜愛歌舞,他在離宮後院種了一園子梨樹,常跟后妃與皇親國戚們在此歡宴,為了娛賓,唐明皇挑選優秀的樂師與宮女,長駐在園中演唱。引用這典故為劇院命名之人,倒也有幾分文采。」
後面一人打岔道:「我只看過雜劇會唱唐明皇,不曉得唐明皇也會唱戲?」
「那不能叫戲曲,頂多只是宮廷樂舞罷了。」鹿紋帽少年仰頭道:「關漢卿先生的戲可是獨創,開啟了當代新文體之先河。」言語之中對這位劇作家極度推崇。
這份敬意並未感染那些民眾,他們對什麼文壇地位沒感覺,真正有興趣的還是戲本身好不好看:「說到關漢卿這傢伙,這回不曉得又要玩什麼把戲了,每次做新戲都保密到家,讓人等得牙癢癢又心癢癢。」
「有小道消息說,新戲好像跟妓女有關。」
「居然連妓女都上臺啦?那可有看頭了。」
旁聽的馬致遠卻頗不以為然,這種風月豔事哪上得了檯面,也不怕辱沒了文筆。
「有傳出是誰主唱嗎?是男角是女角?」
「他們當家花旦前兩個月才剛嫁人,不再唱了,所以我猜是末本。」
旦本指的是女角擔綱,末本指的是男角擔綱,由於每一齣雜劇全由一位主角主唱,從頭唱到尾,其餘角色幾乎都只有臺詞,只有在劇情需要時,才會擔任副唱或合唱,換言之,主角的人選,決定了全劇的成敗。
「下午都要開演了,主角還是一團謎霧,這梨園戲班真是怪得可以。」
鹿紋帽少年也有話想說,但不想搭理那些俗人,轉身對馬致遠道:「你覺得呢?不發表一下高見嗎?」
馬致遠反問得犀利:「恕我失禮,這勞什子雜劇毫無價值可言,所謂文以載道,請問這雜劇之道何在?」
「原來……你不喜歡看戲。」鹿紋帽少年的神情略顯失望,彷彿是在問,既然你不喜歡,又為什麼要在這邊排第一個?
馬致遠猜得出少年的心思,本來這種事不願對陌生人說,但守夜一整晚,實在悶得受不了,於是坦承道:「你知道按察司知事大人嗎?他今日預定的行程是來這兒看戲,我想求見他一面,看能不能賞給我一個好機會。」
「這種賣國求榮的奸人,你還求他做什麼?」
他們口中這位按察司知事大人,當年不僅貪生怕死投降蒙古兵,為自已掙得一席官位,背後還不知陷害了多少抗元忠良,晚生的鹿紋帽少年雖未逢其時,照樣大表不齒。
「沒辦法,皇帝把科舉給廢了,讀書人無用武之地,生在這個被外族統治的年代,就算一輩子窩在終南山,也別想出人頭地,不毛遂自薦,莫非等到地老天荒不成?……你懂嗎?」
「不要你呀你的,叫我小朱。」
馬致遠不想跟一個陌生小鬼報名,沒想到肚子竟搶著回答,發出咕嚕咕嚕的叫聲。
「……你餓了嗎?」
廢話,馬致遠瞪了小朱一眼,面黃肌瘦的他,與一臉白玉羊脂似的小朱可說是天差地遠,他忽然有種錯覺,這細皮嫩肉的小朱看起來也挺美味可口。
別說他早用光了盤纏,便是有錢,也不能拿來吃喝,他是故意餓自己幾頓,就像他也是故意在梨園從卯更站到巳時,動機很單純,就為了在大都搏個寒貧清高的美名,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反倒成了排隊看戲的閒人。
中午一過,梨園終於開放進場,棗紅大門一拉,一位青衣小矮子冒了出來,安撫觀眾的情緒:「不好意思,讓各位客倌久等了,再過一個時辰我們就要開演啦!」
「嘿!今兒個要唱什麼戲?」
「這……班頭有交待,現在還不能說。」青衣小矮子趕緊轉移焦點,捧出銅盤道:「讓小的來為各位客倌帶位,請爺們高抬貴手,別忘了打賞打賞小的。」
看戲原則上不收入場費,但必須給帶位小夥計賞錢,現場也可另叫茶點,至於位子好不好,服務周不周到,端看各人出手大方而定。
青衣小矮子堆著笑臉,期待馬致遠走上前一步,不料這人不動如山,身旁小朱催促道:「你怎麼不進去?」
「等會兒好了。」馬致遠隨口敷衍,總不能說他已阮囊羞澀,一文不名吧?
人潮拚命往前擠動,卻被馬致遠堵住入口,後面的人一聽到他沒有進戲院的打算,嫌他礙著路,大家硬是把他推出隊伍外。
除了青衣小矮子,梨園又跑出來兩位小夥計一起接待客人。
「李大爺打賞十兩銀,帶『清梅席』。」
「盧大爺二十兩銀,帶『松風席』。」
唱名聲此起彼落,多給銀兩不打緊,個人面子最重要。
然而,原本良好的進場秩序,臨時被兩名插隊者所破壞,他們穿著制服,那是按察司的差役,有特權加持,小夥計自然不敢怠慢,安排他們優先通關。
「站住,先別走!」
大膽揪住其中一名差役的人竟是馬致遠,他劈頭便問:「你不是說,知事大人會來?怎麼只有你們兩個?」
「喔,我們只是先替大人占個位子。」
「所以,知事大人尊駕就快到囉?」
「呃……大概是吧?」
「到底來是不來?」
「會來就會來,不來就不來,大人來或不來,我們做屬下的怎麼敢確定呢?」
「什麼?」這差役明明收了馬致遠一筆賄賂,害他花光身上所有錢,如今幾句敷衍了事的話,教他這滿腹鳥氣哪吞得下去,只是要開打可能也打不過這兩名壯丁,退而求其次,轉問道:「好歹告訴我,大人此刻人在何處?」
那差役畢竟拿人手短,小聲透露道:「照理說,不能透露給外人,看在你有進取之心,我就指點指點你好了。」
聽著那差役附耳細說,馬致遠卻皺起了眉頭。
「琵琶閣?」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限量親簽版│劇神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82 |
奇幻冒險 |
$ 228 |
中文書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限量親簽版│劇神
元朝大都城天字第一號的梨園劇院裡,
關漢卿編寫的新曲,總是場場客滿絕無冷場。
但一紙公文封條,禁演令立刻生效,
原因竟是穿著戲服,深夜殺人的
──女鬼!?
「……二月玉面蝶,三月赤肉嬰,四月斷腸鼓,五月逆竿血,六月飛白雪,七月離魂天,八月枉死城……」
一曲兒歌,道盡含冤待雪的真相,
為了要解開禁演令,關漢卿踏上解謎之途,
卻不想竟意外揭發了一樁又一樁,
被時代輾壓的女性悲情遭遇。
不為酬神,不講奉獻,
折折曲曲,只有句句血淚的人間百影,
一場人鬼神共鳴泣的大戲,
就要登場!
章節試閱
楔子
「……二月玉面蝶,三月赤肉嬰,四月斷腸鼓,五月逆竿血……」
街坊空地上,孩童們一邊踢著羽毬,一邊隨口亂唱,這首歌兒是從哪家孩子開始傳起不得而知,他們也不懂辭中含意,只是一個勁兒地唱得歡樂。
「……六月飛白雪……七月離魂天……八月……」
唱到這兒,一名雙髻小兒的腳尖不小心碰歪了羽毬,同伴沒一個能接住,羽毬在地上無力地彈了幾下,原來孩子們紛紛張大了嘴巴,手指著天上。
悠悠晴空一角,正飛來了一隻五彩大蝴蝶,身軀如甜瓜,羽翼如紗窗,大過尋常蝴蝶數倍。
大都市集的上空飛來這隻異蟲,沒多久便引起了民眾...
「……二月玉面蝶,三月赤肉嬰,四月斷腸鼓,五月逆竿血……」
街坊空地上,孩童們一邊踢著羽毬,一邊隨口亂唱,這首歌兒是從哪家孩子開始傳起不得而知,他們也不懂辭中含意,只是一個勁兒地唱得歡樂。
「……六月飛白雪……七月離魂天……八月……」
唱到這兒,一名雙髻小兒的腳尖不小心碰歪了羽毬,同伴沒一個能接住,羽毬在地上無力地彈了幾下,原來孩子們紛紛張大了嘴巴,手指著天上。
悠悠晴空一角,正飛來了一隻五彩大蝴蝶,身軀如甜瓜,羽翼如紗窗,大過尋常蝴蝶數倍。
大都市集的上空飛來這隻異蟲,沒多久便引起了民眾...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