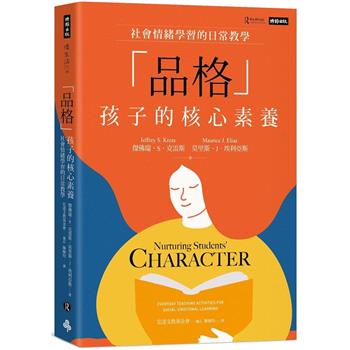第十二章
等司年察覺到時,才發現尚肅正盯著他下身,尤其是股間那泥濘紅腫的地方不住地看。
「你這是做什麼?」
司年臉上一熱,羞得想從他身下鑽出來,卻被尚肅手快地抱住大腿。
「乖,別動,我就是看看腫得嚴不嚴重。」
上頭時越是投入失控,事後也便越擔心,好在仔細看過後,發現只是略有紅腫,並沒有給司年的這處造成多少傷害,尚肅這才稍心安。
拉住司年的雙腿盤於自己腰間,再一把抱他起來,讓司年坐於自己身上再用雙手環住他,然後尚肅道:「寶貝,我們去洗澡。」
看尚肅現在適應得多好,知道司年受不了身上髒有異味,都不用司年提醒,便主動說要帶他去洗澡。
可司年聽見他這話,想到的便是上一回他倆在浴室裡,他被摁在牆上幹得連自己是誰都快不認得的事。
「不!」
司年想也不想拒絕,然後努力想從尚肅滾燙且如牢籠的懷裡掙脫。
「我自己洗!」
尚肅實在拗不過他,也不想太過惹急了他,兩個人抱在一起倒在床上你逃我往地鬧了一陣,最後尚肅妥協地放了手。
一得自由,司年跟隻受到驚嚇的兔子般飛快自尚肅身邊竄出,跑進浴室,「哢嗒」反鎖上門。
尚肅只覺得好笑,取過床頭櫃上的紙巾盒抽出幾張擦了擦腿間的泥濘,便在腰間圍條浴巾,開始更換被他們弄亂弄髒,避免不了沾染腥膻的被子床單。
等尚肅也洗完從浴室出來,臥房裡已沒了司年身影,尚肅一路找出去,最後在廚房裡找到了蹲在垃圾桶前的司年。
一看見尚肅,司年便道:「我們丟進去的一次性飯盒不見了。」
尚肅走過去,果然垃圾桶裡空空如也,「也就是說,垃圾是可以被回收的,不會在屋子裡堆積對居住環境造成影響和染汙。」
說罷,尚肅挑了下眉,繼續道:「倒還挺人性化。」
「冰箱看過了嗎?」
「看了。」
司年慢慢站起來,尚肅扶了他一把。
司年說:「東西挺多的,快把冰箱塞滿了。」
這點尚肅倒不奇怪,距離他們上一次從冰箱裡拿出盒飯,期間他與司年做了這麼多次,用的姿勢都是從電視機的圖片上學來的。那一百種姿勢,堪比性愛姿勢大百科,還真是大大擴展了他與司年的眼界。
一個圖片所示的姿勢換取一份食物和生活用品,這一番操作下來,盡興痛快之餘,可想而知冰箱裡會出現多少東西。
但接下來又聽司年說道:「就是這回冰箱裡的食物有點問題。」
什麼問題?
尚肅看向司年,司年卻只道:「你看看就知道了。」
尚肅於是走過去打開冰箱,仔細一看才知道司年所說的「問題」是什麼。
這次密室給的食物不再是成品,打開包裝就能吃的那種成品,而是直接給的食材。
比如一份酸甜排骨,那它就會給一份生排骨和做酸甜排骨所需的油、鹽、醬、醋、糖和料酒。
尚肅把冰箱裡的食材都取出,生活用品以及情趣用品暫時放在一邊,他把所有食材一一分類,如果不按圖片背後所說的那幾道食物來烹煮,那他們大概可以湊出七菜一湯。
「蒸排骨,煎牛排,炒雞蛋,蔬菜湯……主食可以是蔥油拌麵……把豬肉上的肥肉分離炸乾可瀝出豬油,豬油可以拌飯,油渣也是一道菜,當零食也不錯……」
看著尚肅指著檯面上的食材一一介紹他們可以用這些食材煮出的菜和主食,司年在一旁無語半晌,終於說道:「只能交給你了,我不會做菜。」
尚肅頓了一下,抬頭,對他就是一笑,「那太好了,我又多了一樣可以抓取你的心的方式。」
尚肅笑起來有多好看,就曾有雜誌特意開了兩頁以專門來描述尚肅各個時期的笑。初入影壇時少年羞澀純淨又不失張揚的笑,二十歲時未褪盡稚氣又開始邁向成熟時介於兩者之間矜貴沉斂一笑,三十歲左右的尚肅笑容少了,可每一笑都淺淡如初冬的風,微涼清冽卻又神清氣爽讓人留戀。但不管哪一時期的笑,都讓周圍景色黯然失色,只覺美好如畫,讓人心悅不己,如痴如醉。
司年本想說「抓取我的心是什麼鬼」,但一見近在眼前的淺笑,即刻什麼都忘了。
「年年你有什麼是不吃的嗎?」
尚肅聲音響起,司年才如夢初醒般回神,忙道:「沒有,我什麼都吃,沒有忌口的。」
尚肅看向旁邊的人司年,眉目皆有笑:「年年可真好養。」
因為在福利院裡,忌口就代表不能吃更多東西。
司年垂下眼簾,已經沒什麼情緒波瀾地想起他小時候其實覺得大多東西都難吃的不行,比如不喜青椒、胡蘿蔔、洋蔥,有些孩子直接就說出來,但福利院條件有限,照顧他們的阿姨無奈之下只能用油拌飯頂多添些醬油調味給這些孩子吃。
那時的司年也就六七歲吧,目睹此景想的卻是,我挑剔,那我能選擇的東西就會變少,甚至沒得選擇,但我若是能忍下來,可以選擇的便會更多,至少能從中選一個我比較不討厭的,而不是只能吃白飯。
所以再不喜歡他也忍下來,頂多是把不愛吃的先挑到一邊再慢慢吃掉,然後發現,不知從何時起,這些他不愛吃的食物,其實也挺好吃的。以至於到如今,若說有什麼是司年不能吃的,那還真沒有。
當然這些根本沒必要說給尚肅聽。
司年對於尚肅會炒菜這一事還挺好奇,「你一個大影帝,想必很忙吧,哪來的工夫學這些?」
司年日常工作也忙,所以他一閒下來只想做條翻身都懶的鹹魚,到飯點能及時拿起手機點外賣都算勤快了,宅在家裡的時候,一天一頓都是經常。
尚肅正思索待會兒要做些什麼菜給他與司年吃,聞言回道:「我曾經為了拍好戲特地找大廚學過一段時間,然後發現自己煮飯做菜還能排憂解壓,所以一沒什麼事就會自己下廚,身邊不少家人朋友都吃過我煮的飯菜,他們都還覺得不錯。」
司年驚了:「炒菜做飯還能排憂解壓?」
司年一個燒開水泡麵都嫌麻煩費事的人實在想不明白。
尚肅能理解司年的驚訝,畢竟上網打遊戲都有不少人玩不明白不知道樂趣在哪,更何況炒菜做飯這種在不少人看來瑣碎複雜的事情。而且他也不需要司年能理解和明白,他覺得司年只要喜歡他親手做的飯菜就好了,不需要喜歡上炒菜做飯,所以他只大致解釋了一下:「從洗菜到切菜,再到下鍋翻炒放調料,從頭到尾都是一件需要專注的事情,一不留意分神,切菜會切到手,炒菜會把糖認成鹽,少放或多放鹽,一盤菜可能就這麼毀了。而人一旦專注於某事就會把另外的事情淡化甚至忘卻,等忙完這些再回過頭來一想,可能原來讓自己煩心的事情也不是那麼煩心了。」
也就是轉移注意力。
司年表示理解了。
尚肅又補充道:「當然前提是你得喜歡做這件事,因此這件事才能成為你用來排憂解壓的一種方法。」
司年又在廚房待了一會兒,在尚肅開始做飯時,司年從櫥櫃底層某個角落翻出買東西賺送的一條圍裙給尚肅繫上,又發現自己在廚房實在幫不上什麼忙,自覺將洗好烘乾的衣服床單被套等拿出來,該疊的疊,該收的收。
因為食材有限,尚肅這次就簡單做了一菜一湯,主食是蔥油拌麵。
兩個人坐下來吃飯的時候,尚肅不由感慨了一句:「真像是在過日子。」
正在吃麵的司年眼皮子一掀看他。
嘴裡的麵條嚼了好幾下嚥進肚子,司年很誠實地道:「拌麵很好吃。」
尚肅一笑,「你喜歡吃就好。」
司年夾了一筷子青椒炒牛肉放進嘴裡,然後又用乾淨的碗盛了湯喝一口後,說:「要是真的出不去,你一個在國內外拿獎拿到手軟的大影帝只能做家庭煮夫了。」
有這樣的手藝做家庭煮夫並不算埋沒,可惜了他的影帝身分,影圈失了這麼一位演員,外頭不知道有多少影迷粉絲得哭到暈厥啊。
尚肅先喝了口湯,「我一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就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既然一時半會兒出不去,目前他就專心去做尚肅,一個努力追求心上人討好心上人的普通男人尚肅。
一頓飯吃完,飯前沒幫上什麼忙的司年主動說要洗碗。
尚肅沒反對,只不過在司年洗碗時人跟著一塊擠進廚房,司年洗碗他就幫著擦乾再放碗櫃裡。
「夫夫」齊心,甚至用不上五分鐘,就把碗筷盤子都洗完擺好了。
飯後,休息得差不多了,尚肅提出要去跑一會兒。
司年屋子裡有一臺跑步機,自這臺跑步機搬進他家裡,司年一個月能跑上三回衝上三公里都算他超常發揮了。尚肅一走上跑步機,直接就調了距離,要跑十公里。
司年:「……」
所以,對他來說,強健的體魄和腹肌這些東西,只能羡慕,不能強求。
他就仍舊做他普普通通,朝九晚五的理工宅男好了。
尚肅跑步,司年也沒閒著,他窩在沙發裡看書。
除了不能出去,一時間,屋子裡的氣氛讓人聯想到一個詞:歲月靜好。
偶爾從書裡抬頭,眼睛朝揮汗如雨的尚肅看去,曾經喜歡孤獨,喜歡一個人待著的司年心想:如果這就是兩個人一塊過日子,倒也沒什麼不好。
跑步中的尚肅視線不時落在窩在沙發裡的司年身上,汗水自眼睫毛尖處不時滴落劃過的眼睛中,盛著淺淺卻無法錯過的暖意。
沒有辦法去計算時間,只能餓了吃,睏了就睡的日子並不知道過了多久,但電視裡的一百張圖片,變暗的已經將近一半,圖片上所剩的姿勢也越來越突破羞恥度,同時屋子裡也逐漸多出不少東西。
不照做就無法獲取食物,甚至會困死在目前所處的密室裡。
尚肅和司年知道他們別無選擇。
在這裡,從他們褪去身上所有衣物的那一刻起,就不該再有羞恥心。
此時,一身軍官制式純黑色皮革衣服穿戴在身上的尚肅翹著二郎腿,正坐在泛著冷色光澤的金屬椅子上,拿著皮鞭的手支在扶手上,皮鞭的尖輕輕打在另一隻手掌心。
這一身黑色皮衣,有大簷帽,有能露出胸肌與腰身的上衣,有堪堪遮住重點部分的皮褲,還有一雙有著堅硬鞋底的長筒馬靴。
這一身,讓尚肅既高貴又欲色十足,既冷傲又誘人至極。
眼中帶著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意,可身上所穿之物卻又是能讓人飛蛾撲火的誘惑。
相互矛盾,又相得益彰。
與他相比,立於他面前的司年一身白皙的皮肉被捆上一圈圈皮帶,把他本就單薄削骨的身體勒出不少肉來,胸前被勒出兩團一掌可握的乳肉,嫣紅的乳尖點綴其上,他的雙手被皮革縛於身後,股間夾著一黑色硬物正於他身體裡嗡嗡嗡地劇烈震動,掛在硬物上的一根皮穗子因為劇烈的震動而不斷擺動。
司年打開的竭力撐在地上的兩隻腳之間,一滴又一滴水滴打溼了地板,形成一圈圈四濺的水斑,這些,都是自司年半軟的小肉棒裡滴出來的汁液。
司年很難受,身體因為按摩棒的震動而顫抖不已,可他卻口不能言,因為他嘴裡塞著一個口枷。
司年只能用泛紅溼潤的眼睛看向尚肅——不,是用乞求的目光看向他的上官。
上官的鞭子再一次輕輕擊打在掌心處,然後冷聲道:「跪下。」
司年眨了眨眼睛,隨後曲起膝蓋,有些艱難地跪在地上。
接著上官又道:「過來。」
雙手被捆於身後的司年只能膝行過去,幾步的距離,他幾乎花盡了全部的力氣,等他終於移到上官打開的腿間,人便不由倒在一邊的大腿上,睜著一雙含著水光的眼乞求地看著他俊美無比的上官。
上官眼神冷漠,摸上他的臉的手卻滾燙炙人,修長的手指撫過他白皙的臉頰,於他塞了口枷的唇上來回摩挲。
上官問:「可知道錯了?」
枕在他腿上的人嗚咽一聲,無法吞嚥的嘴裡落下來一條清亮的水光。
上官憐憫地為他擦去,沾上他唾液的手指吃進嘴裡,泛著冷光的眼睛瞇起來一些,「味道不錯。」
「你既以知錯,那便從輕發落,現在,是你贖罪的時候了。」
上官摘下他的口枷,按著他的頭,讓他的臉摁至腿間那腫硬的地方,上官滿足地吐了口氣,方道:「舔。」
司年忍住在身體裡肆虐的酸麻,難耐地吞嚥口水,眼睛盯著近在咫尺的,把皮褲勒出鼓鼓的一個大包的地方,張開嘴伸出舌頭,隔著一層皮革,從下方兩個渾圓的地方開始舔,順著粗大鼓起的紋路一路舔上去,把這一大塊地方都舔上自己的口水。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Evil Desire之密室(下)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Evil Desire之密室(下)
司年覺得自己中了一種名為尚肅的毒。
導致他坐立難安,日思夜想,心像空了一塊,怎麼也填不滿。
要想拔毒,就得經歷一場剜心剔骨的痛,
讓他徹底認清他與尚肅之間從未開始也不可能開始這個現實。
與其飄渺不定地淪陷幻想,不如快刀斬亂麻,讓自己清醒。
所以司年決定去找尚肅,不顧一切,不留餘地的去。
沒忘記,在夢裡是尚肅親口告訴他即將心拍的電影叫《永夜》。
好不容易混進了劇組,還搭了個有臺詞的臨演,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能讓尚影帝特意前來親身指導;
火鍋店裡,尚肅分分鐘鐘的細心照料與直球告白,
讓兩人瞬間重返密室的感覺……
章節試閱
第十二章
等司年察覺到時,才發現尚肅正盯著他下身,尤其是股間那泥濘紅腫的地方不住地看。
「你這是做什麼?」
司年臉上一熱,羞得想從他身下鑽出來,卻被尚肅手快地抱住大腿。
「乖,別動,我就是看看腫得嚴不嚴重。」
上頭時越是投入失控,事後也便越擔心,好在仔細看過後,發現只是略有紅腫,並沒有給司年的這處造成多少傷害,尚肅這才稍心安。
拉住司年的雙腿盤於自己腰間,再一把抱他起來,讓司年坐於自己身上再用雙手環住他,然後尚肅道:「寶貝,我們去洗澡。」
看尚肅現在適應得多好,知道司年受不了身上髒有異味,都不...
等司年察覺到時,才發現尚肅正盯著他下身,尤其是股間那泥濘紅腫的地方不住地看。
「你這是做什麼?」
司年臉上一熱,羞得想從他身下鑽出來,卻被尚肅手快地抱住大腿。
「乖,別動,我就是看看腫得嚴不嚴重。」
上頭時越是投入失控,事後也便越擔心,好在仔細看過後,發現只是略有紅腫,並沒有給司年的這處造成多少傷害,尚肅這才稍心安。
拉住司年的雙腿盤於自己腰間,再一把抱他起來,讓司年坐於自己身上再用雙手環住他,然後尚肅道:「寶貝,我們去洗澡。」
看尚肅現在適應得多好,知道司年受不了身上髒有異味,都不...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