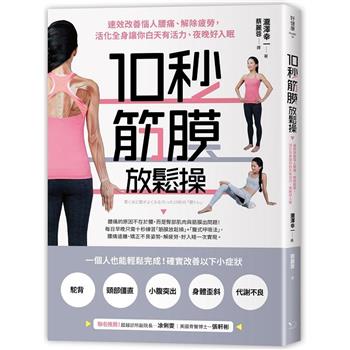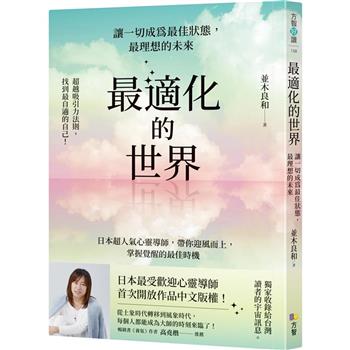★★《紐約時報》即時榜暢銷書★★
★★讓人一口氣讀完的《早安美國》推薦書★★
★★《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作家★★
小心那些住進你家裡的人。住在一起的,就是家人嗎?三個糾纏不清的家庭和一間有著深沉秘密的房子,扣人心弦直到最後一頁。
莉比滿二十五歲後不久,終於接到她等待許久的信――來自已逝父母信託基金的通知。她帶著激動的心情拆開了信:我終於要知道我是誰了。
很快地,她知道了親生父母的身份,同時,也知道自己是一棟座落於泰晤士河畔倫敦雀兒喜區高級地段豪宅的唯一繼承人。她更從一則剪報上得知,二十五年前,警察因有人通報嬰兒持續的哭泣聲而到了那座豪宅,卻發現廚房地上有三具屍體,全都穿著黑色長袍,旁邊留下潦草書寫的遺書。根據當年的報導,原本住在豪宅裡的另外四個孩子都不見蹤跡,只有一個十個月大的嬰兒趟在臥室嬰兒床上,那就是她。
她原有生活的一切都在收到信的這一天改變了,而她不知道的是,還有其他人也一直在等待這一天……
作者簡介:
莎•傑威爾(Lisa Jewel)
出生於倫敦。她的第一本書《Ralph’s Party》是一九九九年最暢銷的出道處女作。此後她陸續出版了十六本書,近期作品主要為心理驚悚小說,包括《The Girls》和《Then She Was Gone》,兩本均入選為「理查與茱蒂圖書俱樂部」(Richard & Judy Book Club)的選書,以及《I Found You》和《Watching You》。
麗莎是《紐約時報》排行榜前十名,也是《星期天泰晤士報》(Sunday Times)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的作家,她的書已經在全球以二十五種語言出版。
她和丈夫、兩個女兒、兩隻長毛貓、兩隻容易緊張的天竺鼠和一隻可愛的紅棕狗住在倫敦。她每天在咖啡館裡寫作,每次持續二到三小時,禁絕網路,至少產出一千字。
譯者簡介:
吳宜璇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譯有《迷途青春》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各界讚譽
「情節豐富、黑暗、錯綜複雜而令人著迷,這本懸疑小說巧妙融合了長篇家族故事和黑暗的犯罪元素,製造了令人驚嘆的寒意。」—《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露絲‧韋爾(Ruth Ware)
「在腦海中縈繞不去、氛圍強烈、讓人欲罷不能的一直閱讀下去。」—《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梅根‧米蘭達(Megan Miranda)
「令人著迷……傑威爾又一部黑暗傑作,她用令人驚嘆的情節和豐富的人物性格,熟練而巧妙地敘說故事。」—《書目雜誌》星級評論
「讓人不忍釋卷……獨特、精心設計的角色,不斷變換視角,以及令人不安的敘事方式,創造出一個具有生命力、充滿驚喜、讓人著迷的故事。」—《出版者週刊》星級評論
「傑威爾以令人不寒而慄的心理驚悚筆法讓人緊跟著莉比的足跡,逐步揭露家族過去黑暗、扭曲的秘密。」—《華盛頓郵報》
「這位懸疑大師開展了另一個精彩的家族秘密故事。」—《娛樂周刊》
「節奏緊湊、富有想像力的故事,讓讀者持續猜測結局到最後。」—《今日美國》
「麗莎•傑威爾的故事令人著迷……捨不得放下來。等我們解開她的最後一個謎團時,會非常訝異這些故事線索自己交織成一個精巧而令人滿意的結局。」—《明尼阿波利斯星論壇報》
「沒有人能夠像麗莎•傑威爾一樣寫出如此令人寒毛直豎的家庭懸疑驚悚小說。」—Goodreads網站
名人推薦:各界讚譽
「情節豐富、黑暗、錯綜複雜而令人著迷,這本懸疑小說巧妙融合了長篇家族故事和黑暗的犯罪元素,製造了令人驚嘆的寒意。」—《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露絲‧韋爾(Ruth Ware)
「在腦海中縈繞不去、氛圍強烈、讓人欲罷不能的一直閱讀下去。」—《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梅根‧米蘭達(Megan Miranda)
「令人著迷……傑威爾又一部黑暗傑作,她用令人驚嘆的情節和豐富的人物性格,熟練而巧妙地敘說故事。」—《書目雜誌》星級評論
「讓人不忍釋卷……獨特、精心設計的角色,不斷變換視角,以及令人不安的敘事方式,創造出一...
章節試閱
3
切爾西大宅,一九八○年晚期
我的名字和我父親一樣,都叫亨利。同名容易造成混亂,但我母親稱我父親為親愛的,我妹妹稱他為爹地,而幾乎所有人都稱他藍柏先生或直接尊稱他為先生,我們克服了同名的問題。
我父親是他父親的唯一繼承者,他父親的財富是靠吃角子老虎得來的。我從沒見過我的祖父,我父親出生時他就已經很老了,但我知道他來自黑潭(Blackpool),名字叫哈利。我父親一生中從來沒有工作過,只是閒坐著等哈利去世,這樣他才能擁有自己的財富。
他拿到遺產那一天,在切爾西的切恩大道買了我們住的這棟房子。哈利臨終之際那段期間,他就一直在找房子,幾個星期前看上了這個地方,並且因為擔心有人在他繼承遺產之前就出價而緊張兮兮。
房子在他買下時是空的,他花了好幾年時間跟一大筆錢,用他慣稱為裝飾品的東西擺滿整間屋子:鑲板牆壁上探出麋鹿頭,門上方掛著兩把交叉的狩獵用劍,有著鏤空扭紋椅背的桃花心木座椅,中世紀風格、滿是刮痕和蟲蛀的十六人宴會餐桌,櫥櫃裡裝滿手槍和皮鞭,一條二十英尺長的壁毯,畫著其他人祖先的陰森油畫,一大堆沒人會去讀的燙金皮革書籍,還有前院一座仿真尺寸的大砲。我們家裡沒有舒適的椅子,沒有讓人感覺溫暖的角落。舉目所及盡是木頭、皮革、金屬。每樣東西看起來都很硬。尤其是我父親。
他在我們的地下室練舉重,在他自己的私人酒吧裡用專屬小酒桶喝健力士啤酒。他在梅菲爾百貨花八百英鎊買手工西服,肌肉和腰身差點塞不進去。他的髮色如舊硬幣,粗糙的手有著緊繃的紅色指節。他開捷豹的車。雖然他討厭高爾夫球,但他還是會去打,討厭的原因是他天生不太會揮桿,他太僵硬、沒有彈性。他會在週末去打獵,通常是星期六早上穿著緊身粗花呢夾克,帶著後車廂的槍消失,然後在星期天傍晚拎著冰桶裡的兩隻斑鳩回家。我大約五歲時,有天他帶著
跟街上某個人買來的英國鬥牛犬回家,用的是他經常塞在外套口袋,如薄荷般鮮綠的五十英鎊鈔票。他說這隻狗讓他想起自己。後來,那隻狗在古董地毯上拉屎,立刻被掃地出門。
我母親是個絕世美女。
這不是我說的,是我父親說的。
妳媽媽是個絕世美女。
她有一半德國、一半土耳其血統。她叫瑪蒂娜,比我父親小十二歲,在那些人來之前,她是個時尚象徵。她會戴上深色墨鏡去斯隆街購物,用我父親的錢買色彩鮮艷的絲巾、有著鑲金包裝的唇膏和濃郁的法國香水,有時會有人邀她拍照,她手上掛著名牌包,照片登上雜誌封面。他們稱她是社交名媛。她其實不是。她會打扮得光鮮亮麗地參加華麗派對,但是當她在家時,她就只是我們的媽媽。不是最好的那種,但也不會是最糟的,而且絕對是我們這個大而陽剛、滿是稜角的切爾西豪宅裡,讓人感覺相對柔軟的部分。
她曾經工作過一年左右,幫重要的時尚人士相互引介。至少在我印象中有這回事。她的皮包裡有幾張銀色名片,上面用粉紅色字體印著「瑪蒂娜.藍柏公司」。她在國王路一間商店上方的明亮閣樓裡有間辦公室,擺了玻璃桌、皮椅、傳真機,整排套著透明塑膠袋的衣服,立柱上擺著插滿白百合的花瓶。我和我妹妹不用上學時,她會帶我們去陪她工作,從箱子裡整疊白紙中抓幾張紙和幾支馬克筆給我們塗鴉。電話不時響起,我媽媽會說:「早安,這裡是瑪蒂娜.藍柏公司。」偶爾會有訪客按下對講機—我妹妹和我會搶著看輪到誰負責按鈕開門。訪客都是激動莫名、瘦巴巴的女性,討論的話題都是衣服和名人。那間公司沒有所謂「同事」,只有我們的母親,有時候會有一臉天真的年輕女孩來實習。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只知道那間閣樓辦公室消失了,銀色名片也消失了,我媽媽回來繼續當家庭主婦。
我和妹妹在騎士橋那一帶上學,很可能是倫敦最昂貴的學校。那時我們的父親不怕花錢。他喜歡花錢,花越多越好。我們的制服配色是狗屎棕配上黃疸黃,男孩們還得穿燈芯絨短褲。值得慶幸的是,當我年紀大到會因為服裝感到羞恥的時候,父親已經沒有錢付學費,更別說到哈洛德百貨的制服部買燈芯絨短褲。
他們出現之後,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家、以及我們的生活全變了樣,一切發生得如此緩慢,卻又驚人地快速。在柏蒂帶著兩個大皮箱和裝在藤條箱裡的貓,出現在我們家前門台階上的第一晚,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她將對我們帶來什麼影響,她將會把那些人引進我們的生活,以及這一切竟會這樣結束。
我們以為她只是來過個週末。
4
莉比彷彿可以聽到這房間裡曾存在過的每句低語,感受到曾坐在她所坐的這個位置上每個人的氣息。
「一七九九年,」羅伊爾先生正在回答她的上一個問題。「算是倫敦最古老的法律文件之一了。」
羅伊爾先生隔著打過蠟的辦公桌面看著她。他的唇間閃過一絲笑容,說道:「唉呀呀,好極了。可真是不得了的生日禮物,不是嗎?」
莉比緊張地微笑。「我還是沒辦法相信這是真的,」她說。「老覺得會有人跟我說這只是個大笑話。」
她選擇的詞彙——大笑話——似乎不太適合這個歷史悠久、帶著沉穩氛圍的地方。她真希望自己能有其他措辭。但是羅伊爾先生似乎不介意。他保持笑容,俯身向前遞給莉比一疊厚厚的文件。「這不是個笑話,我可以跟妳保證,瓊斯女士。」
「這裡,」他說,從那疊文件中抽出一樣東西。「我不確定現在給妳看這個是否合適。又或者應該跟著那封信一起寄給妳。不知道該怎麼說—總之有點為難。它被放在那疊文件中,我保留了下來,只是以防萬一有什麼問題。看來這麼做是正確的。所以,請吧。我不知道妳的養父母跟妳說了多少關於妳原生家庭的故事。但妳或許會想花點時間看看這篇報導。」
她展開那張報紙,攤放在她前面的桌子上。
社交名媛和丈夫雙雙自殺
幼兒失蹤;一名寶寶倖存
警方昨日在接獲可能有三起自殺案的線報後,趕赴前社交名媛瑪蒂娜.藍柏和她丈夫位於切爾西的住處。警方在中午抵達,發現藍柏夫婦的屍體並排躺在廚房地板上。還有一名尚未查出身分的男子也陳屍該處。二樓房間裡找到一名推測約十個月大的女嬰。該嬰兒有受到妥善照料,身體健康。根據鄰居們近年來的觀察,有其他孩子也住在這棟子裡,同時還有很多成年人經常來來去去,但目前並未發現任何蹤跡。
死亡原因尚待確認,初步的血液採樣顯示三人應該是服毒自盡。
現年四十八歲的亨利.藍柏是他父親哈利.藍柏位於蘭開夏郡黑潭鎮的房產的唯一受益人。近年來健康不佳,據說需以輪椅代步。
警方目前正在全國各地搜尋這對夫婦的兒子和女兒,據了解他們的年齡介於十四至十六歲。任何有關於孩子行蹤訊息的人請盡快聯繫首都警方。任何近年曾與該家庭一同住在該棟房子的人,也是警方關注的重點。
她盯著羅伊爾先生。「意思是……? 那個被留下的嬰兒——是我嗎?」
他點頭。她能看出他眼中真誠的憐憫。「是的,」他說。「真是個悲慘的故事,不是嗎? 而且是個謎。我指的是那些小孩。他們也是這棟房子的信託受益人,但他們倆都沒有出現。我只能假設,嗯,他們已經……總之就是現在這樣了。」他向前傾身,抓著領帶並勉力微笑。「需要我拿支筆給妳嗎?」
他遞過一個木製碟子,上面擺了幾支看起來很昂貴的原子筆。她拿了一支,筆身上印著燙金的公司名稱。
莉比茫然地望著那支筆好一會兒。
她有哥哥。還有姐姐。
自殺。
她輕輕甩了甩頭,然後清了清嗓子說:「謝謝。」
她的手指緊攢著那支筆,幾乎想不起來該怎麼簽她的名字。那疊文件的頁面邊緣貼著塑膠標籤紙,指引她該簽名的地方。筆尖不斷劃過紙張的聲音有些令人煩躁。羅伊爾先生和顏悅色地看著她。他將桌上的茶杯往旁邊推了幾吋,然後又移回來。
她可以非常強烈地感受到當她簽下名字那一刻的意涵,此刻生命的無形轉折將她從此方帶向了彼方。在這堆文件的一邊,是推著車在超市精打細算地購物,一年只有一個星期的假期,還有一台車齡十一年的歐寶汽車;另一邊則是切爾西的一棟豪宅鑰匙。
「很好,」當莉比將簽好的文件遞回給羅伊爾先生時,他這麼說,像是鬆了一口氣。「很好,很好,好極了。」他翻過每一頁,檢視每個箭頭標籤旁的簽名處,然後抬頭看著莉比,帶著微笑說,「好了。我想是時候把這些鑰匙交給妳了。」他從書桌抽屜裡拿出一個米色小麻袋。上面的標籤寫著「切恩大道十六號」。
莉比看了看,袋子裡有三套鑰匙。一套掛了印著捷豹汽車標誌的金屬鑰匙圈。另一套是內附點菸器的黃銅鑰匙圈。還有一套沒有鑰匙圈。
他起身。「要出發了嗎?」他說。「我們可以用走的。離這裡不遠。」
這天是個炎熱的夏日。正午的陽光火熱地穿透薄薄的雲層,莉比可以透過她的帆布鞋鞋底感受到人行道鋪面的熱度。她們沿著街道走去,兩旁都是餐聽,全都對街開放,攤平的桌面架在特製平台上,上方有大型的方形陽傘遮蔽陽光。戴著大墨鏡的女士們三三兩兩地喝著酒,她們當中的一些人和她一樣年輕,而她對於她們能夠在星期一下午坐在豪華餐館裡喝酒感到驚訝。
「嗯,」羅伊爾先生說,「我想這裡可能會是妳的新街坊,如果妳決定住在這棟房子裡的話。」
她搖搖頭,緊張地擠出一絲笑聲。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一切好荒謬。
他們經過小巧的精品店和古董店,裡面滿是狐狸和熊的銅製雕塑,還有跟她浴缸一樣大的吊燈。然後他們經過河邊,莉比還沒走到河邊就先聞到潮濕的狗騷味。大船在河面交錯而過;還有艘載了許多有錢人的小艇噴著水沫駛過,船上擺著放了香檳的銀色冰桶,一隻黃金獵犬在船頭吹著風、瞇著眼睛曬太陽。
「就從這邊過去,」羅伊爾先生說。「再一、兩分鐘。」
莉比的大腿因摩擦而疼痛,她希望自己穿的是短褲而不是裙子。她可以感覺到自己的汗水被胸罩中間的布料吸收,而她看得出來,穿著緊身西裝和襯衫的羅伊爾先生也因為高溫而難受。
「我們到了,」他說,轉身面向有著五或六間紅磚屋的一整排房子,每一間的高度和寬度都不同。莉比還沒看到扇形窗上用捲曲字體寫的十六號數字,就已經猜出哪間是她繼承的房子。這棟房子有三層高、四個窗戶寬。很美。但就像她預想的那樣,被封起來了。煙囪頂端和排水管長滿了雜草。外觀看起來並不討喜。
但依舊非常美麗。莉比深吸一口氣。「這房子好大。」她說。
「是的,」羅伊爾先生說。「總共有十二個房間。不包括地下室。」
這棟房子並沒有緊臨著人行道,外面有著華麗的鐵欄杆和茂密的花壇。一道鍛鐵頂棚通向大門,左邊擺了一座實體尺寸的大砲,固定在混凝土石塊上。
「我有這個榮幸嗎?」羅伊爾先生指著將擋板固定在門前的掛鎖。
莉比點了點頭,於是他解開掛鎖,移開擋板,發出了可怕刺耳的怪聲,後面是一扇巨大的黑門。他搓搓手指,一把一把有條不紊地找出這扇門的鑰匙。
「上一次有人進來是什麼時候?」她問。
「天哪,我想已經是好幾年前了。那時候屋裡淹水,我們不得不緊急找水管工來,修補損壞之類的。來,我們進去吧。」
他們走進門廊。戶外的高溫、車流的嗡嗡聲、河水的迴聲都消失了。裡面很涼爽。深色木地板上有著刮痕和灰塵。前方樓梯配著深色木製扭紋扶手,立柱頂端雕刻著裝滿水果的碗。門上刻有布紋雕飾,搭配華麗的青銅把手。有一半牆面上有著深色的木製鑲板,貼著已破舊的酒紅色羊絨壁紙,紙面已被飛蛾啃噬得光禿一片。空氣的味道很重,感覺滿布塵絮。唯一的光線來自每扇門上方的氣窗。
莉比打了個顫。實在太多木頭了。光線不足,空氣也不足。她覺得自己像在棺材裡。「我可以打開嗎?」她把手伸向其中一扇門。
「想做什麼就什麼。這是妳的房子。」
這扇門通向後方的長形房間,裡面有四扇窗戶,可以望見茂密的樹木和灌木叢。房裡是更多的木頭鑲板壁面、木製百葉窗,還有滿滿的木地板。
「那會通往哪裡?」她指著木製牆面某處的一扇窄門,詢問羅伊爾先生。
「那個,」他回答,「是通往傭人房的樓梯。直接通向閣樓上比較小間的房間,還有一扇隱藏門設在二樓的樓梯平台。這是這種老房子常見的設計。蓋得像倉鼠籠一樣。」
他們一間一間、一層一層地探索整棟屋子。
「家具都到哪裡去了? 家飾品呢?」莉比問。
「早就沒了。這家人為了生計全都賣掉了。他們直接睡床墊。自製衣服。」
「所以他們很窮?」
「是的,」他說。「我想,實際上他們很窮。」
莉比點頭。她沒想過自己的親生父母是窮人。這是當然的,她可以隨心所欲地創造想像中的親生父母。就算不是被收養的孩子也都會創造幻想的親生父母。她幻想中的父母很年輕,交遊廣闊。他們在河邊的房子有兩面落地玻璃窗和大片露台。養了兩隻狗,都是母的小型犬,脖子上戴著鑽石。她幻想中的母親是時尚公關,父親則是平面設計師。他們會帶她去吃早餐,把她放在高腳椅上,餵她吃撕成小塊的布里歐麵包,並在桌子底下親暱地互踢對方的腳,小狗蜷曲著趴在桌下。他們是在參加完雞尾酒會開車回來時,死於跟跑車擦撞的車禍事故中。
「還有留下什麼嗎?」她說。「除了遺書?」
羅伊爾先生搖了搖頭。「嗯,沒什麼特別的。除了一樣。當妳被發現時,妳的嬰兒床裡有樣東西。我相信它還放在這裡,在妳的嬰兒床裡。我們要不要去看看?」
她跟著羅伊爾先生進入一樓的大房間。這裡有兩個可以俯瞰河流的大面上下拉窗。房裡空氣凝滯厚重,天花板角落佈滿了厚厚的蜘蛛網和灰塵。房間另一端有個開口,他們將那個角落改裝成另一個小房間。看起來是更衣室,三面都是裝飾著華麗串珠,漆成白色的衣櫥和抽屜。房間的正中央則是一張嬰兒床。
「那是……?」
「是的。那就是他們發現妳的地方。妳那時咯咯地笑,很開心的模樣。」
嬰兒床設計成可晃動的搖籃,附有用來前後推動嬰兒床的金屬槓桿。槓桿漆成了厚重的乳白色,床邊繪製了有點怪的淡藍色玫瑰花樣。嬰兒床的正面有個小金屬徽章,上面是哈洛德百貨的標誌。
羅伊爾先生伸手從後方牆上的架子拿起一個小盒子。「在這裡,」他說,「這東西被放在妳的毯子裡。我們跟警方都認為這是要留給妳的。警方將它當作證據存了好幾年,一直到案件沉寂下來才還給我們。」
「是什麼東西?」
「打開看看。」
她從他手上接過那個小紙盒,打開蓋子。裡面裝滿了撕碎的報紙。她的手指摸到某個硬而滑順的物體。她從盒子裡拿出它,懸在指尖垂下。那是一隻綁在金鍊子上的兔子腳。莉比有點嚇到,鍊子從指縫滑落到木地板上。她伸手撿起來。
她的手指滑過兔腳,光滑的皮毛冷冰冰的,爪子尖銳。她用另一隻手把玩著那條鍊子。一個星期前,她滿腦子都還是新涼鞋、單身派對、頭髮分岔、記得要幫家裡的盆栽澆水,現在已經變成睡床墊的那些人、死兔子,和一間又大又恐怖的房子,整間空蕩蕩的,只放了一張哈洛德百貨買的大嬰兒床,側面畫著詭異的淡藍色玫瑰。她把兔腳放回盒裡,不自在地拿著。然後,慢慢將手放到嬰兒床的床墊上,感受當年在此沉睡的她那小小的身軀,感受最後將她放到這張嬰兒床上的那個人,將她安穩地用毯子包裹好,放上兔腳。當然,現在這裡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張空床,和陳舊霉味。
「我叫什麼名字?」她說。「有人知道嗎?」
「有,」羅伊爾先生說。「妳父母留下的紙條上寫了妳的名字。寧靜。」
「寧靜?」
「是的,」他說。「很好聽的名字。我這麼認為。帶點……波西米亞風?」
她突然有種要窒息的感覺,很想立刻發狂似地衝出這個房間,但這麼戲劇化不是她的風格。於是,她開口說,「我們可以去看看花園嗎? 我需要一些新鮮空氣。」
3
切爾西大宅,一九八○年晚期
我的名字和我父親一樣,都叫亨利。同名容易造成混亂,但我母親稱我父親為親愛的,我妹妹稱他為爹地,而幾乎所有人都稱他藍柏先生或直接尊稱他為先生,我們克服了同名的問題。
我父親是他父親的唯一繼承者,他父親的財富是靠吃角子老虎得來的。我從沒見過我的祖父,我父親出生時他就已經很老了,但我知道他來自黑潭(Blackpool),名字叫哈利。我父親一生中從來沒有工作過,只是閒坐著等哈利去世,這樣他才能擁有自己的財富。
他拿到遺產那一天,在切爾西的切恩大道買了我們住的這棟房子。哈利臨終之際那...
作者序
如果說我的童年在他們來之前很正常,這是不正確的描述。實際上,與所謂正常相去甚遠,但至少「感覺起來」是正常的,因為那是我所熟知的世界。直到如今,幾十年後再次回顧,我才明白有多怪。
他們來的時候,我將近十一歲,我妹妹九歲。
他們和我們一起生活了超過五年,讓一切變得非常、非常黑暗。我和妹妹不得不學習如何生存。
當我十六歲,而我妹妹十四歲時,那個寶寶來了。
如果說我的童年在他們來之前很正常,這是不正確的描述。實際上,與所謂正常相去甚遠,但至少「感覺起來」是正常的,因為那是我所熟知的世界。直到如今,幾十年後再次回顧,我才明白有多怪。
他們來的時候,我將近十一歲,我妹妹九歲。
他們和我們一起生活了超過五年,讓一切變得非常、非常黑暗。我和妹妹不得不學習如何生存。
當我十六歲,而我妹妹十四歲時,那個寶寶來了。


 2021/10/07
2021/10/07 2021/06/13
2021/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