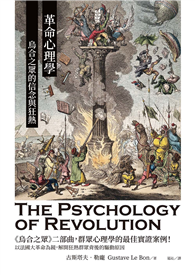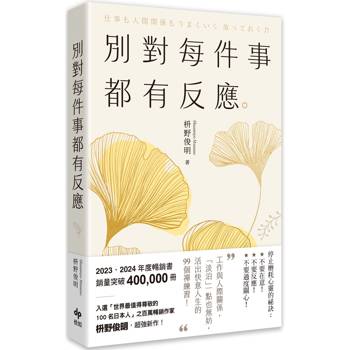讀者著迷推薦:「我看完了,看到凌晨四點,到天亮都還睡不著。」
成熟的敘事結構╳流暢的節奏發展╳細膩的情感表達,
中國懸疑推理小說巨匠、百萬暢銷書作家 雷米 扛鼎之作!
豆瓣圖書高分好評7.9分,改編電影縝密籌備中!
成熟的敘事結構╳流暢的節奏發展╳細膩的情感表達,
中國懸疑推理小說巨匠、百萬暢銷書作家 雷米 扛鼎之作!
豆瓣圖書高分好評7.9分,改編電影縝密籌備中!
所謂執念,求而不得,念念不忘……
時隔二十三年的泣血追凶,成了三個男人的心魔,也成了他們的靈魂救贖。
「凶嫌於C市鐵東區犯下連環強姦殺人碎屍案,經警方循線追查,終於於今年8月逮獲凶手,並經C市人民檢察院依殺人罪嫌起訴。24歲凶嫌許姓男子以販售生豬為生,作案手法……目標……塑膠……提醒民眾,應小心人身安全……」
從警三十多年,杜成是第一次被同僚們壓在病床上強迫休息。
他知道,他要死了,但他不在乎要不要治病,
他最在乎的是那樁連環殺人案的凶手,至今仍逍遙法外──
當年,抓錯人了。
杜成重新探訪當年的被害人家屬、探查所有的拋屍地點,
直到他到法院調閱檔案時,他才發現,有人跟他一樣執著於找到真凶,
在這期間,還意外地翻出連同此案一起埋藏的案外案……
「當他在黑暗的街路上凝視那些更黑暗的角落時,總覺得有一雙眼睛,正在回望著我。」
「牠們又溫馴又單純,可是仍然對人類絕對信任,我寧願和牠們在一起。人多可怕。」
「我已經等了二十三年,不在乎再多等一會兒。」
「我見過最黑暗的罪惡,最強烈的情感,她也有了自己的祕密──其實,我也有。」
「我不怕受罪,反正是要死的人,真正怕受罪的人,他們活該。」
有人為了心中的正義、為了隱藏在心中已久的祕密,願意以身涉險;
有人困在養老院將近二十年,不願帶著仇恨和不甘死去,誓死也要抓住那個惡魔;
有人行蹤詭異,不斷拿著望遠鏡在固定的地點徘徊,監視著某人的一舉一動;
眼看案情逐漸明朗,卻有人從中作梗,不斷阻擋杜成揭開血淋淋的真相,
那個人──究竟是誰?
讀者著迷推薦
成熟的敘事結構、優美的文筆文風、細膩的情感表達、合理的節奏把握、流暢的發展脈絡、清晰的人物關係,讓這部長篇小說流暢生動,引人入勝,讓讀者與故事中人一起感同身受,引發強烈共鳴。
沒有人是純粹的善,也沒有人是純粹的惡,每個人都是複雜的,他們都會鬼神更可怕,卻也都可能會比彩虹更美麗。──豆瓣讀者Christina~Fan
雷米在描寫案件的同時,在許多地方不經意間為我們描繪了這一時代變遷,增加了故事的分量。──豆瓣讀者煎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