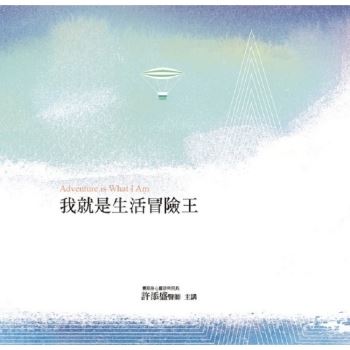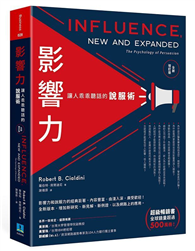圖書名稱:長安的荔枝
銷售破百萬冊!數萬網友評為神作,最受期待影視大IP!
繼《長安十二時辰》後,馬伯庸再一次挖掘大唐盛世不為人知的祕辛!
★豆瓣2022年度中文小說NO.3,近10萬人8.5高分推薦
★當當小說暢銷榜NO.1,16萬讀者100%熱烈好評
「這是一次久違的計畫外爆發,寫得格外酣暢,從動筆到寫完,恰好是十一天,和李善德的荔枝運送時間相同。」――馬伯庸
一顆小小的荔枝,道盡大唐九品小官的職場血淚……
天寶十四年,楊貴妃生辰當日,一人單騎十萬火急地衝入長安城,無人知道馬上乘載著什麼,更無人知道這關乎一個人的性命……
「一騎紅塵妃子笑」的背後涉及多少權勢爭鬥?是多少人的辛酸血淚?
賞味期限只有四天的新鮮荔枝,如何在沒有高速公路和冷藏運送的年代跨越五千里路?
文字鬼才馬伯庸從底層小人物的視角刻劃偉大王朝步入末日的景象,
看唐朝「社畜」李善德在泥沼般的官場職場掙扎向上,展現小人物視死如歸的氣魄――
「就算失敗,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離終點多遠的地方。」
各種利益的博弈、管理層內部的矛盾、職場的情商、不得已的違規,甚至還有不斷修改需求的「甲方」。閱讀每一行字,都像是在閱讀自己。――歷史學教授 于賡哲
進入官場幾十年卻依然是個九品小官的李善德,終於迎來職涯的高峰――人生第一個肥缺。不僅是替聖人辦事的體面工作,不用看三省六部的臉色,更有無盡的油水可撈。原以為從此飛黃騰達,置產買房,豈料這個肥缺竟是個保證掉腦袋的坑。眼看鍘刀已懸在頭上,這會兒才來求神仙傳授縮地術為時已晚,李善德只好硬著頭皮先下嶺南看荔枝,然而他萬萬沒想到,自己要面對的不僅僅是荔枝如何保鮮、快馬如何加鞭,竟然還有節度使親兵半途截殺?!至於為了一顆荔枝,跟他這個九品小官過不去嗎?
【讀者好評】
l 全書緊鑼密鼓節奏緊湊,閱讀過程暢快淋漓,以一個小人物的視角窺視了大廈將傾的唐朝盛世。
l 這是一本常讀常新的書,我如今讀第二遍依舊津津有味。
l 雖是第三人稱角度敘事,卻讓我不由得代入主人翁的視角,隨他一起經歷命運浮沉。
l 有價值的歷史小說都是符合史實,能夠深刻反映當時社會面貌的歷史小說。好久沒有看到能讓我沉醉其中忘記時間的書了。
作者簡介
馬伯庸
暢銷作家。
曾榮獲人民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茅盾新人獎。
被譽為沿襲「『五四』以來歷史文學創作的譜系」,致力於對「歷史可能性小說」的探索。
代表作有《長安十二時辰》、《古董局中局》、《三國機密》、《風起隴西》、《顯微鏡下的大明》等。